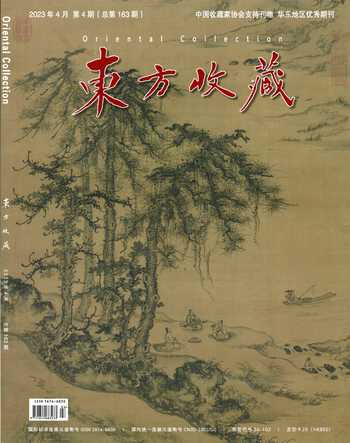传统图像的重构与表达



摘要:武汉博物馆馆藏的碧玉仙人四灵图对碗,其用料为单色碧玉,有黑色点沁,玉质油润,通透晶莹。从用料和制作工艺判断当其为仿痕都斯坦玉器,在图案装饰上保留着我国传统的仙人和“四灵”组合,但又经过了历史的重构,形成了新的表达。这种重构和表达不仅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也体现着一定的地域性和民俗性。
关键词:仙人;四灵;图像;重构
武汉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碧玉仙人四灵图对碗(图1),器型规整,端庄大气,高7、口径18厘米。器壁极薄,侈口,微束腰,矮圈足。口沿和近底足部位各饰一圈阴线纹,中部浅浮雕仙人手持兵器骑乘四灵兽。碗底心有“乾隆年制”四字款(图2)。
这对碧玉碗的制作工艺等争议不大,笔者不再赘述,主要针对玉碗的装饰图案——“四灵”和仙人的组合展开讨论。“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由于图像本身不便区分先后顺序,文中就以“麟、凤、龟、龙”作为“四灵”组合,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中的记载来排序展开叙述。
四幅图像的仙人面相和装束基本一致,初步设定为同一仙人的四种表现。第一幅为仙人骑麒麟(图3),右手握钩,左手握二股叉;第二幅为仙人骑凤(图4),双手舞剑;第三幅为仙人骑龟,左手执戟,右手持拂尘;第四幅为仙人骑龙,双手张弓搭箭。
一、“四靈”图像的演变和重构
“四灵”无论作为个体或整体,在古代整个图案的装饰应用中都比较活跃,常见于画像砖、建筑构件、服饰、壁画和各类器物上,同时在古代的人文观念中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
根据考古物证和史籍记载,古人认为龟能通灵,其预测吉凶的功能在殷商甲骨文中体现无遗,麟、凤、龙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作为各自物种领域的主要代表而确定下来,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的经历和地位的沉浮。总体来说,麟、凤变化不大,一直作为祥瑞和政治身份的象征而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龙的地位因“天人感应”而与皇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这在“四灵”当中是无可比拟的。龟的地位直到唐代还很尊崇,但在元代以后却一落千丈。这就造成了此对玉碗中“四灵”图案的重构,用“龙生九子”之一的赑屃代替了原组合中的龟。这一点,许维莹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有相应的论证。因此,“四灵”图案的组合重构,正是当时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一种重新组合后新的表达,也是清代龟的地位下降的一个实物例证。
二、仙人图像的考疑和推测
在该对碗的纹饰图案中,仙人的女性特征比较明显。纵观中国古代神话信仰体系中出现的女性仙人,常见的有女娲、西王母、后土、九天圣母、碧霞元君、妈祖、斗姆元君、无生老母等,她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地域当中占据着信仰的主流。那么,此对碗纹饰图案中的女仙究竟是谁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重构呢?经笔者综合各类资料信息推测,其当为斗姆(图5)。
斗姆,又称斗姆元君、斗姥、紫光夫人、斗姆摩利攴天等,是北斗众星的母亲。斗姆本身的图像,就经历了本土信仰和佛教经义的互相组合渗透和重构。斗姆信仰脱胎于九皇信仰,而九皇信仰则是继承北斗信仰而来,所以从根源上来说,斗姆是古代星斗信仰的集大成者。据考,斗姆信仰形成于宋代,在元代和佛教的摩利攴天结合在一起,明清时期盛行。
《道法会元·卷八十三·先天雷晶隐书》云:
天母圣相:主法斗母摩利攴天大圣,四头八臂,手擎日、月、弓矢、金枪、金铃、箭牌、宝剑,着天青衣,驾火辇,辇前有七白猪引车,使者立前听令,现大圆光内。
刊于清代的《九皇斗姥戒杀延生真经》也有这样的记载:
九皇斗姥金轮开泰元君,头挽螺髻,身被霞绡,耳坠金环,足登珠舄,左手执拂,右手执杵,乘五龙之车,趺八宝之座会,三登上真于摩利攴天,谈生天生地之道,阐不生不灭之旨。
此外《道藏》中还有记载:
斗母紫光天后摩利攴天大圣,化身四头八臂……两手抵日月,一手执戟,戟上有黄幡,上有金字,云九天雷祖大帝;一手剑,一手印,或曰杵;一手金绳,一手弓,一手箭。坐七猪辇。
据此看来,从装束上,文献中所述“头挽螺髻,身被霞绡”和碗上仙人的穿着表现基本吻合;从法器上,弓矢、拂、宝剑、戟基本吻合;从显像上,碗外壁四面四幅图案表达正好对应了斗姆元君四面八臂的形象,这在民间信仰中则是一个整体图像的另一种表达;从坐骑上,一般是火辇前有七头白猪或是五龙车,而在玉碗中则演变为和传统的“四灵”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图像重构。
三、整体图像重构之成因
在该对玉碗中,斗姆与“四灵”图像的组合在目前现存的图像中较为少见,这种组合与斗姆信仰的兴起演变有着紧密的联系。斗姆的神职,据《道法会元·卷八十五·先天雷晶隐书》云:“(天母默朝急告)凡袪雷、祈祷、杀伐、禳星、避难、释冤憎、救死亡,无施不可,务在专心致意,依法奏告,有求必应。”这种灵应也见诸清代的文人笔记中——
清王嗣槐《桂山堂诗文选》 文选卷一载:
祖母土夏月遘危疾,父景和公远馆于外,先生忧惶不知所为,日夜祷于天,愿以身代,家奉斗姥案前盎水忽结为冰,饮之得汗而疾愈。
清褚人获《坚瓠集》 秘集卷三《斗姆救焚》载:
康熙壬申仲冬二日浑暮,屈驾桥人,见绿衣两人在巷门口坐,以为代役看栅者,转瞬不见,咸诧为奇,随火起桥陌,延烧三十余家。至张君安铺,屋柱焦损,火飞入檐,君安合掌称“斗姆”宝号不辍,火光照耀之间,人见君安屋上有老人策杖巡行,火焰随灭。盖君安奉斗斋多年,极其诚敬,故斗姆垂救及门而止,奉斗之力昭然可信。
清齐学裘《见闻随笔》 卷二《斗姥送保命灯》载:
咸丰纪元中秋前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成池,余病头风将及两月,夜间跌坐,云起楼榻上。童子寿康赤脚踆在榻旁,头而睡。余闭目宴息,闻门有声,见一丫鬟持烛台进房置方桌上,又闻门声,见一老妪珠翠满头,盛装盛服,抱一斗灯上笼碧纱,上踏步床,置斗灯于床头,复以百龄袄挂在帐钩。
以上三则材料中,一则是救火,二则是救命,说明了斗姆在清代神职的进一步扩大,几乎达到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程度。再看下面一则史料,来源于清沈起元的《敬亭诗文》文稿卷九:
今士大夫往往尊奉斗姆,為舞乩、为圆光,其术尤足感人。无论二氏之神鬼,都属不经要,与夫子敬鬼神而远之之训相背。
文中出现了对斗姆信仰的批判,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斗姆信仰在当时的流行。
道教圣地武当山太子坡现存有相当数量的碑刻,从碑刻的考察中能获知,至清末年间,分别经历了大小6次修建。此外,龙虎殿的八字山墙下以及走道两侧的部分碑刻并未嵌入到墙壁中,是可以活动的。虽然有6通碑刻与斗姆阁修建有关,但是在资料中并未提及相关内容。在被提及的内容中,有4通的年代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1通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1通为乾隆五十年(1785)。这些被提及的碑刻总共修建过4次,第一次为1755年—1761年,主要是对太子坡进行了全面修建,包括复真殿的重建、大殿的重点维修;第二次为1771年,重新塑建了斗姆阁救苦楼的神像;第三次为1783年,在斗姆阁中作了彩画油漆;第四次为1850年,主要为太子坡的整体维护。
此外,在武昌城西有斗姥阁。碑刻《重修武昌府斗姥阁碑记》 记载:“斗姥建自前唐,道光九年(1829)毁于大火,道光十四年(1834)重修而成,主要为扼奔流、镇灵怪。”在此,斗姆的神职又转化为镇水害、镇灵怪,这也许就是斗姆的坐骑转化为“四灵”的直接原因。
当然,在上述提到中国传统信仰的女神中,还有一位也与玉碗中的形象比较接近,那就是在黄帝与蚩尤大战中助黄帝战胜蚩尤的九天玄女,《颐道堂集》文钞卷十一载:“元(玄)女授兵钤位尊斗姥。”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传统图像在历史的演变中会发生多种组合、层累和重构。
“出于某种功利心理,他们对神的躬逢其盛也以人们普遍喜爱的物化形式来进行。”这也许就是制造这对玉碗的最初目的。这种重新整合的图像表达,与其说是普通民众信仰意识的错位表现,不如说是将信仰中的不同神灵和谐统一到日常的信仰实践之中,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1]刘固盛,梅莉,胡军等.湖北道教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3][美] 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M].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陈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6]李信军.水陆神全:北京白云观藏历代道教水陆画[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7]姜守诚,张海澜.道教女仙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
[8]张继禹.中华道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刘明哲(1985—),女,汉族,山西左权人。本科学历,艺术设计专业,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器物的图案与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