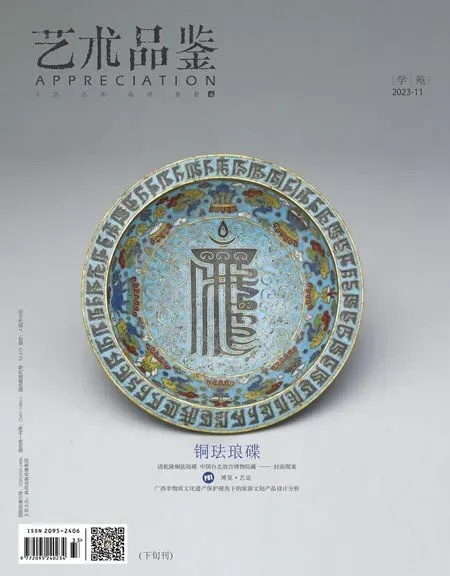“不计工拙”:宋朝尚意书风的转捩
何晓莹(肇庆市高要区黎雄才艺术馆)
宋代的书法在巍峨的唐法面前,面对着难以企及的城墙与如何再造辉煌的难题,宋代文人们以自我角色的转捩为理据,试图在书法中调和唐代“法度”,注入宋代“意蕴”。以欧阳修为始端并亮出的“不计工拙”书法思想的底牌,由此带动了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人士大夫对此思想的翕然从之,体现的皆是以“工拙杂存”的方式,以期创造出不输前代的新的土壤,“尚意”书风风潮亦因此而奠定了自己扎实的地位,迎来了春天。而后代书者在这场尚意风波中,亦受益颇丰。
至唐止,诸多书家的书写多数以“工夫”取胜,讲求书写“工力”之妙谛。如南朝王僧虔《论书·笔意赞》中便有提及“书工”的重要性:“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工之尽矣,可擅时名。”唐朝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亦曾用“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寥寥几语盛赞书圣王羲之书法。至宋代,其书法审美语境与价值判断标准则开始一反常态。以欧阳修为始端,唱出“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的书写论调。此论调在彼时书法语境中产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影响,亦致使后人不断追问:在书法审美与价值判断标准中,“工”与“拙”是相辅相成抑或二元对立的矛盾?如何理解欧阳修提出的“不计工拙”的书写思想?其对后来的宋代尚意书风是否构成联系?由此产生了几多的意义与弊端?此文将依次逐一进行梳理。
一、工拙的内涵及“不计工拙”的提出
(一)工拙的内涵
“工”与“拙”在字面意义上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放至书法情境中,从实用层面言之,则直指书写技能工夫。“工”对应着高层次、赏心悦目的书写形态,其点画、结构与布白皆在书写者的笔下熠熠生辉;“拙”则指代低层次、不甚成熟的书写技能,书写者尚不能胸有成竹地处理字间架构关系。一般而言,由“拙”到“工”是可以通过提升书写者的书写技能而臻以完备。
若从审美层面论之,则沾溉着实用的一面,又涵泳着审美内涵的一面。“工”仍是对应着书写者的工夫弥深,在技法上可得心应手,有“庖丁解牛”之赞誉;而“拙”,除却实用批评层面,还表明了另一层蕴意:用得心应手之技能,使其书法不露痕迹地流露出“拙”的一面,生发出一种信手书写、拙朴自然之妙谛,这层寓意,比实用层面中的“拙”意,内涵更为隽永丰富。
(二)“不计工拙”的提出
纵览从殷商时期至唐的书写,都可明确窥见每一种字体几乎都存在着由“拙”到“工”的书写进程。陈振濂认为,这是由于当书法处于实用层面时,书写者多数是以“工”为最终目的及不竭追求。无论是在书写层面或书法理论层面,皆是如此。以至于到了唐朝,其隶书、楷书、行书的基本笔画之定型、笔法要素之开掘、结构空间之划分定势,已趋于完备,形成精整的旨趣与森严的书写法度。
当然,求“工”不是书写者的唯一旨趣。另有一些有识之士传达出其他的书法审美信号。如孙过庭认为书法应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张怀瓘则认为,品赏书法是“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一语中的地指明求“工”求妍只能居下,尚未能登得高堂,而神采气势则能居上。这些审美风尚都在孕育着另一种书法审美旨趣,表明了除求“工”之外,仍有别样美的存在。
故乎于此,从实用层面分析,宋代面对晋唐这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其矻矻以求的技法,精雕细刻的书写态度,很大程度上阻塞了宋代书法前进的通道。宋人面对这样的困境,亦唯有避正取侧,避骏取跛了。从审美层面分析,既然“工”至极则的唐朝无法跨越,那便只好高扬“新意”的旗帜,带领士大夫们挣脱必然之网,为宋朝书法寻求一丝生机。于是欧阳修便标榜着“不计工拙”的书写思想横空出世,以求通过这不羁心声去弥合书法前进道路中的裂痕。
二、从“意先笔后”到“不计工拙”:尚意的前兆
唐代的“重法”为其朝代滋养了诸多理论典范且荟萃了众多名家。欧阳询《八诀》曾提及,书写时须“意在笔前,文向思后。”韩方明《授笔要说》亦有言道:“意在笔前,笔居心后,皆须存用笔法,想要难书之字,预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笔,自然容与徘徊……”孙过庭《书谱》亦有言,书写时若能做到“意先笔后”则精气神便潇洒闲逸,蔼然自得文人气息。虽说先“意”后“书”是确保书写者规范各种书写技能与章法布白,减少败笔;此用意最后亦为唐代书法树立了森严的法度,将书家禁锢于“法度”之中,为后来宋代打破其天网提供了契机。
欧阳修所提出的“不计工拙”的不羁心声,概括而言,有三个要义,回应了唐代书法应有“法度”之规则。其一,试图将“向外追求”的书写形态拉回到“人生内部”,转向对内部世界的人格、胸次、襟怀的追求与依赖。此处之“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写技能的拙丑之意,它指代了一种用技而不被技拘,无所矫饰、自然天成之美。北宋时期书家仍有崇晋慕王之遗风,大多周折于晋唐书风恬适、疏淡、圆润之窠臼。故此,“不计工拙”思想的提出,是贯以纯熟的“工”之后再求“拙”的迥异审美追求;亦是辅以其勃郁的求新精神开掘书法新领域。
其二,《宣和画谱》中载入了很多二王经典名作,宋代选官制度中很多考生便以此为范本,邯郸学步,不越雷池一步。甚至有“趋时贵书”,考官是何种字体,考生便模拟某种字体,投机取巧获得功名利禄。这两者现象,前者会将书法引向死胡同,形成书法历程的闭环;后者则会断送书法之精髓,让书法的土壤变得浅薄。
其三,欧阳修收藏了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得其所收藏的古代碑文胎息,于缺憾处,不完美之瑕疵处觅得宋代书风新的出路。如张坤山在其《张坤山五体书法研究》中指出,宋人“因为从上古金石中发现了古雅之美,窥看到古代不知名的书家随意下笔,随形结构,大小不一,如百物之状,皆能活动圆备,字字自足,错落有致,美不胜收”,从而滋生了“不计工拙”乃至于“尚意”书风的蔓延。又如欧阳修所言:“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表明阅览古人遗迹,领悟古人之意,方能再造创新。同时,也有对碑文完好无损,可供赏玩收藏研究表示可喜可贺:“汉隶世所难得,幸而在者多残灭不完,独此碑刻画完具,而隶法尤精妙,甚可喜也。”
三、从“不计工拙”到“文士崛起”:尚意的后盾
以工求拙,能在宋代以火苗之势迅速蔓延,亦主要是以整个宋代士大夫阶层为主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宋代士大夫阶层政治地位的提升。据许总主编的《理学文化史纲》一书中指出,宋代文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阶层地位较高,有别于唐代时期的阶层境况。士大夫手持如此政治局面,方促使他们得以高举着“游于艺”的旗帜,涵融着士大夫特有的文史哲美学等各方面的通识,驶往“不事雕琢,一任天机”的书写甬道。
正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篇什中提及:“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事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学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各有相当之素养,鉴赏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切实地表明士大夫之素养足以借助于金石碑文的滋养,而得大施拳脚之平台。
其二,时风激荡下士大夫的情感转场,由外转向内。按理说,宋代士大夫阶层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理应充分发挥“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书法创作与审美层面上亦应是一派向外欣欣向荣的态势,为何会呈现对内部精神世界的矻矻以求局面呢?据秦寰明在《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一篇什中记载道,在仁宗前期,出现了较多具有进取精神的新兴士人队伍,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是在诗歌方面呈现出复古之风气。然而,好景不长,时风激荡下,士人们慢慢转向内省,他们将原本追求精进有为之心态转为追求淡泊,且“逐渐淡化外在的事功追求”。另外,诸多文人士大夫熬熬汲汲于功名利禄,攻于心机,在很多实际问题上坐失空谈,从而令另一批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此熬熬汲汲又驻而不得,徒陷时光,空耗生命,危世难济亦身心俱疲。这样的心态从宏观层面而言,等于消耗掉了文士们对外部世界观照的热情与夙愿,在微观上为其情感外场转向内心场域留下了注脚。
综上论之,在这样莫测的时风中,士大夫秉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已淡化了以“达”通“济”的实质。将以“通达”而乞求“兼济”天下的夙愿斥于次席,从而深入到以追求“穷达”至“独善”的脉理。恰恰是这戏剧性的转换,促使文士们的“独善”,有力地为宋人“不计工拙”且“尚意”书风风潮的建树铺垫下了坦途。
四、尚意之旨趣:游于物外
可以说,欧阳修所提出的“不计工拙”之先声,在某种程度上,为宋代“尚意”书风风潮的蔚然成风导夫先路,遂使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翕然从之,成为这场风潮的主要倡导者,将高扬“新意”的书法姿态得以温习而光大。
由这点火苗,而促使后来者频频以“不计工拙”作为据点,引申出自己对书法创作及书法审美领域中的独到见解。如苏轼言之“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口号,亦与欧阳修的“不计工拙”有异曲同工之处。又如黄庭坚力呈己见:“但现世间万缘如蚁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再如米芾就书法创作中的心得论之:“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在工拙关系的见解上,黄庭坚则道之:“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从而在书法创作形态上,于传统中成功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有如苏轼的“状类石压蛤蟆”的“画字”,黄庭坚“直逼荡桨拨槕”的“描字”,米芾“犹如风樯阵马”的“刷字”,都一一印证了他们作为书家,除了通晓“意在笔前”法度的题中之义,亦把士大夫所特有的萧散闲逸的情怀发挥到极致,遂使书法成为文士们内心世界中独善其身的“乐事”之一。
除此之外,还孵化出了“游于艺”的美学思想。而这,还得从欧阳修的书学思想中发掘其能被后人不断发扬光大的蛛丝马迹。在欧阳修的《试笔·学书为乐》一篇什中论道:“苏子美尝言:窗明净几,笔砚纸墨皆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所好者,又特稀也。”在这段文字中,可提取出书写乃为“人生一乐”,且不因此作为筹码熬汲于功名利禄、为物所役是极为难得珍贵的品质。正所谓“应物而无累于物”(王弼《魏志·钟会传》)。此处欧阳修赞咏苏子美有“人生一乐”,他亦有学书“可以消日”,此外,还有苏轼的“自乐于一时”,米芾的“放笔一戏空”的论调,这些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宋人视书法为内部世界的投射的同时,亦在强调书法艺事“游于艺”之中的“游”的功能,正所谓“自游息焉”。
“游于艺”中的“游”,其能够与艺事发生化学反应的基本要素是“无用”与“中和”,只有当书家把自己的创作活动视为与实用、与外界不相关的境地,方能通过“无用”之用将“游”更好地涵泳自我的内心世界,从而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在此处,我们可以将实用的与外界相关的比作各种高超的技法与森严的法度,在此将用“物”来指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以上的种种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向“游于物外”,即是不为物役,拼命追求高超技法与不可逾越的法度亦有涯,正所谓“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对“物”的追求,理应“寓意于物”而不是为物所役。一言以蔽之,即倒不如在转益多师后,“不计工拙”,摆脱“为绳墨所缚,不得左右”的困局,随遇而安,随物而乐。如此,苏轼找到了“无意于佳乃佳尔”之妙谛;黄庭坚觅见“心意闲淡乃入微”之本质;米芾悟得了“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学书须得趣”“无刻意做作乃佳”之脉理。林林总总,皆是“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之“神与物游”的境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五、余论
此文从“不计工拙”作为切入点,并随之引申出后来者的种种独到心印。那么,很值得说明的一点是,不管是“自出新意”或是“总而成之”,他们都循着书法发展的轨迹,坚贞不渝地践行自己的风格取向,并凝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将书写技巧的森严法度拉下神坛,成功解放了审美的宽容度,更加注视个体的主体性情,力图以有限通往无限,完成对书法无形虚空主体意绪的重塑。西方也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当完美的尺度无法逾越,便会努力从法度完备的罅隙中,另辟蹊径,寻求全新的价值意义,安放本时代的艺术。
宋代“尚意”风潮行至今日,对其评价好坏参半。主要原因在于“尚意”在整个史论构架中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有人言:“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呈现出来了”。这样的观点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以个人精神追求为旨归的艺术常“带有虚幻性”,换言之,就是只为能达到一种“渺茫的无限”,自己说服自己的“满足”,并且常用这种“虚幻性”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棘手的现实问题。
此外,还对南宋的书法发展轨迹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有学者认为,正是北宋这场轰轰烈烈地对书法法度的解体,导致了南宋书法嬗递过程中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用一句话概括并作为结语最为合适:“东方美学中,艺术对现实中任何感性事物的描写,其最终的意义都不在于单纯认知这感性事物自身,而在于从这感性事物中显示出比感性事物更深邃、更高、更重大的精神意义。”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