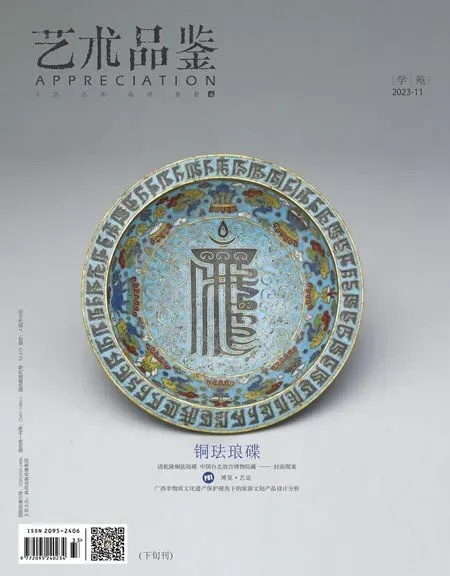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装饰艺术分析*
张靖怡 孟春荣(内蒙古工业大学)
蒙古汗国时期,诸汗在“大宫帐”,“金帐”内举行各种典礼,蒙古语称这种宫帐为“斡尔朵”(ordo)。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未设固定的都城,分布四处的斡尔朵便是他的指挥中心。“鄂尔多斯”(Ordos)蒙古语意为众多的宫殿,其地名承载历史文化信息,侧面反映特殊的地域文化。历史上的蒙古族皇室贵族对鄂尔多斯地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过对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如今的鄂尔多斯蒙古包从形制、装饰等方面也呈现出与其他地区蒙古包迥别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装饰艺术风格。
一、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装饰文化源流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装饰文化是基于鄂尔多斯多元的文化背景而形成。在历史文化进程里,游牧民族、黄金家族、汉民族的文化在此相互交融、相通并存,从而构成独具风格的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装饰文化。
(一)北方游牧民族装饰文化的传承
鄂尔多斯自古就是北方游牧部族的活动基地。在北方游牧文化中,流动是核心价值,帐幕类的建筑适应迁徙的生活方式,“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游牧民族以木杆为主要支撑材料,穹顶圆壁,用毛毡等做覆盖,畜牧转移时可立即拆卸装载。游牧民族有着崇尚自由的价值观和热爱大自然的秉性,随性奔放、豁达开朗的性情塑造了他们纯真、朴拙的审美心理,牛羊毛的围毡和木制杆件传递着亲切的自然气息和粗犷的审美风格。随北方游牧部族的兴衰交替,帐幕类建筑逐渐成熟并多样化,蒙古包也由此而生。鄂尔多斯蒙古包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传承而来,文化基因决定了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最基本的可装卸三段式框架,在此基础上发展、诞生出具有民族风格、地域特色的装饰文化。
(二)黄金家族帝王装饰文化的传入
黄金家族对鄂尔多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历史久远的。公元1205 年至1227 年,成吉思汗先后六次对西夏用兵,这期间他的人马在鄂尔多斯过冬休整,留下阿尔寨石窟、百眼泉、苏里格敖包等历史遗迹。在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中,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张,多种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 “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欧亚其他古国的名贵材料、先进技术与工匠大量涌入蒙古高原,草原王公贵族的帐幕类建筑从构造、材料、装饰、规模等方面焕然一新。元朝时,鄂尔多斯在沟通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区、防御西部外来势力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作为元皇室的牧场和军马基地,并在今鄂尔多斯乌审旗、鄂托克旗西部、杭锦旗南部、伊金霍洛旗南部、东胜区一带建行宫察罕脑儿,属皇室封地。明朝天顺四年,与黄金家族关系密切的鄂尔多斯部与达尔扈特部开始定居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部首领世代享受济农的称号,济农阶层用蒙古包奢华的装饰彰显地位和身份的尊贵。黄金家族帝王文化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深刻影响了鄂尔多斯的地域文化。
(三)汉民族装饰文化的融合
鄂尔多斯地处于黄河几字弯,与中原汉地长期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往来。漠南蒙古地区施行盟旗制度后,清朝廷对济农、朝贡者的赏赐数目庞大,覆盖范围广,赏赐人数多,且频繁。所赏之物以工艺品、丝绸居多,有利于中原皇家装饰纹样大规模地在蒙古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康熙、雍正两朝都极重视蒙古地区的农垦,破产农民向今鄂尔多斯地区流动,蒙古王公的奢侈生活,也需要招民开垦以开辟财源,今鄂尔多斯境内几近黄河、长城处,就都有了汉族农民的足迹。播种时来、收割后走,很多汉族农民开始“游农”的活动,蒙、汉两族文化逐渐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中原地区与蒙古族地区的工艺美术和制造技艺也相互借鉴和学习。中原的绘画题材也开始出现在蒙古包家具的装饰中,例如,石榴、琴棋书画还有象征至高统治地位的龙图案等。当时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王公贵族所使用的大蒙古包和经堂蒙古包也普遍借鉴汉式建筑的重檐歇山顶和门廊的元素与结构(图1),彰显其有别于普通毡包的独特属性,也使蒙古包的装饰更加丰富及多样化。

图1 带重檐歇山顶和门廊的蒙古包(图片来源:额尔德木图.蒙古包建筑史:13至20世纪中叶)
二、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装饰手法
(一)雕刻
在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装饰中,雕刻手法会运用于木材和金属,较能体现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审美风格。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木构架装饰多运用雕刻的手法,在其套脑、乌尼、哈纳之间的连接柱以及木门上都有雕刻吉祥图案。在对木构架进行选材时,也会考虑材料是否利于雕刻,一般会选用柏木,木材颜色鲜艳、味道清香、可塑性较强。然后将要雕刻的内容绘制于木材上进行雕刻,雕刻完毕后依据木材的粗细、纹路等进行打磨,最后将雕刻的图样着色作修整和修光。
蒙古贵族多喜爱贵金属,多年来不断出土的蒙元时期的墓葬中展现的金银器皿,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在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装饰上,常见金、银等金属饰片,在这些饰片上也常运用雕刻的手法。据《元典章》记载,蒙元时代,蒙古族银器的纹样制作工艺就十分高超,包括錾刻、模压、错金等多种工艺,其中錾刻就指金属雕刻工艺,是常用的金属纹样制作方法。利用金属材料的延展性,在设计好图案和形状后,将其固定在胶板上。通过用锤子敲击錾子,使其在工件上移动,从而创造出多姿的线条和留白。然后,从正反两面反复进行采或抬的操作,打造出浮雕层次。按照绘画的构思展现轮廓,先完成浮雕再在正面进行精细雕刻。中间需要经历数十道工艺流程,包括抬、落、串、点、压、采、勾和丝等步骤。这些工艺使得图案纹样在金属表面呈现出立体的层次和纹饰。制作完成的金属饰片常装饰于套脑底部与乌尼杆的头、尾部(图2),伴随乌尼杆伞形排列结构具有和谐、韵律和向心的装饰效果,经金属饰片的装点,使蒙古包具有华丽、精致的气质。

图2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中的金属饰片(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二)彩绘
包内装饰中,彩绘常与雕刻结合,在哈纳与哈纳间的柱子、套脑底部以及木门上均有采用。彩绘较雕刻更具有视觉冲击力,使蒙古包的装饰具有更浓郁的装饰艺术性,打造出富丽堂皇空间效果。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彩绘用料采用天然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制成。矿物质颜料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常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松石、孔雀石、朱砂等珍贵矿石制作,原料采集后,需经过研磨或凿舂,又经水沉淀、过滤、晒干后成为各色粉末颜料。不同颜色的矿物颜料,研磨、制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由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能够保证木架构上的图案长时间色彩艳丽。相比天然矿物质颜料,植物颜料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其是由草本植物在沸水中煎煮后提炼而成。传统的彩绘材料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可以保护蒙古包木构件,减缓木材的腐蚀速度,延长使用寿命。彩绘题材涉及动物、植物、吉祥图样等,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彩绘内容多为龙凤、瑞兽以及八宝纹样,象征着权力、威严以及美好生活。
(三)毡绣
毛毡对于蒙古族的重要意义不只是生活的必需品,更是民族的标志。毡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种,在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苫毡及其内饰毡中常用到毡绣工艺,此工艺主要为平面型毛毡的多层加固。鄂尔多斯蒙古族制作的毛毡先用绵羊毛、山羊纤毛、驼毛和驼鬣来纺织,然后用毛线编织,再进行裁剪、缝合最后用纤毛线、鬣毛线锁边,毛毡密实、坚牢、平整,如图3,十分适合毡绣。使用的绣线来自骆驼、牛、马、羊的毛,手工搓成不同粗细的毛绳,用于毡绣的各个部位,与白色的毛毡搭配,色彩和谐,且结实耐用。

图3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中的毡绣挂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毡绣的基本工艺有绗缝,贴花,盘绳等。绗缝即单针沿着毡子的两个面的一个方向进行缝制,一般由2-3 层毡拼接而成。用缝针时针鼻不能太大,否则毛毡致密性受到破坏。手工搓成驼毛缝线不超过1 米,两头细,中间厚,较薄的部位可通过针鼻并回绕固定,以保证缝制时针线不会分离。绗缝的出发点是非常有讲究的,会将花纹中间部位缝纫到边缘,以保证针吃量均匀和缝纫后毡面光滑。贴花是指将各种布料或皮革剪裁粘贴于布底或者毡底,然后缝缀,锁边而形成的刺绣装饰方式。毡绣所用贴花比较简洁,一般用在毛毡边缘、角隅处,造型多为直线型,大方、古朴自然。盘绳即把绳子缠绕于毡面上,一般盘绳是整幅毡绣的最后一个环节,多用于图案边缘与角隅处,既可直接盘绳饰于毡面上,又可盘绳饰于绗缝后的毡面上,以加强边界和丰富视觉效果。在盘缝时既要使绳子顺直、无结块,还要保证缝制时毡子表面光滑。用牛毛或驼毛做成的盘绳色彩比较暗,和白色毛毡产生强烈反差,既有装饰效果也有保护边缘效用。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中的毡绣多用组合图案,构图方法与普通地毯相似,有中心纹,边缘纹,角隅纹,底纹等多种形式,以中心图案为关键(图3),常使用含义清晰的吉祥图案,其他部分的图案表现出平衡、对称的审美取向。
三、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装饰特色
鄂托克旗蒙古秘史博物馆里陈列的《蒙古秘史》系列油画展示了蒙古汗国时期,汗王使用的蒙古包的外观形态及色彩,可以看出现今的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与之是相继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又吸纳、涵化汉民族的装饰文化,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装饰特色。
(一)包体色彩
蒙古族有尚白习俗,认为白色是最为高洁、吉祥的颜色。仪式中洒向四方的马奶酒,可汗登基时坐的白毛毡,都象征了白色的神圣地位。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外观以白色为主,从色彩搭配来看,白色因其包容性,与棕色的绳索、以红蓝二色为主的包边和贴布装饰所搭配都毫无违和感(图4)。

图4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包体色彩(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鄂尔多斯蒙古包的毛毡制作十分精细,要剔除杂色的羊毛,然后边用木杆弹打边撒鲜奶,做出的毛毡洁白耐用,在蒙古包表面形成细腻、圣洁的效果。此外,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苫毡还包括天窗毡即额如和,具有较为鲜明的身份标示性。在清代时,高僧活佛使用红色或黄色饰顶毡,王公贵族用蓝色饰顶毡。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天窗毡以红、蓝两种颜色较为常见。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外部色彩简洁中蕴含标识信息,有比较鲜艳、醒目的色彩用于顶饰毡及苫毡边缘的装饰,较多采用蓝、红和黄色,木门与套脑多为木色或红色,整体大部为白色毛毡。色彩上具有华丽的装饰效果,与建筑形成完美的统一。
(二)包体构造
为彰示使用者身份地位的尊贵,在构造方面,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规格与配件有与普通蒙古包有明显的区分。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延续了大斡尔朵的形制,建筑形体较大,具有雄伟华丽之感,凸显宫廷帐幕的威严。关于蒙古汗国可汗的斡尔朵之建筑形制,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记述了窝阔台汗的金帐,“山中为他修造了一座契丹帐殿,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作昔刺斡尔朵”。南宋书记官徐霆至蒙古时,称“其制即是草地中大毡帐,上下用毡为衣,中可容数百人”。因容积较大,需要更多的支撑,宫廷式蒙古包普遍有巴根柱,两到四根不等。
除有巴根柱外,双扇门、有颈套脑和双重天窗都是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标志性构件。双扇门是汲取汉式建筑元素,与大的包体相得益彰的。有颈套脑是用一定厚度的木条做成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在小圆圈的下面、大圆圈的上面打孔,再用多条长短粗细一致的木棍竖着将大小圈穿在一起,变成一个等腰梯形的桶状框架。下方的大圆圈的侧面留孔,用来插挂乌尼。双重天窗延续了有颈套脑的大致形态,区别是双重天窗是在传统插孔式套脑的基础上,加高一个圆顶或攒尖顶的方格玻璃罩。有颈套脑的使用历史较深远,双重天窗是从清开始产生并使用的。
(三)包体布局
宫廷式蒙古包一般用作宴客、会议、仪式等用途,所以其内部的布局及陈设与普通蒙古包有所区别。
传统蒙古包包内布局分三大圈,香火圈、铺垫圈和家具圈。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布局因其使用功能的不同有所差异,但共同点是均有灶火区。在蒙古族的传统中,守炉灶者即家庭的继承者,鄂尔多斯部的首领阶层是成吉思汗“守炉灶者”的传承者,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会更加重视灶火。灶火位于包的正中心,主要放置一个铁质火撑,其上坐一面铜锅。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内的火撑较为豪华,常为四脚八柱,饰以卷草纹或者云纹铁艺图案。正北是主位,放置屏风、宝座等,东、西两面对称分布摆放矮桌、坐毯等器具,会根据人数的多寡在最外围增减桌凳。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的坐毯下铺有传统的蒙古毛毡和牛羊皮,另外还铺设手工榆林、银川地毯,一般都是三蓝的,也是使用者身份尊贵的标志。
四、结语
鄂尔多斯宫廷式蒙古包体现了地区历史、社会、文化等印记,形式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创造出了内蒙古地区独特的蒙古包建筑形态与建筑装饰文化。其建筑装饰在多种因素的汇聚、衔接、碰撞下,产生了彼此的强调、淡化、调和直至融合,体现了一种一脉相承、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装饰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