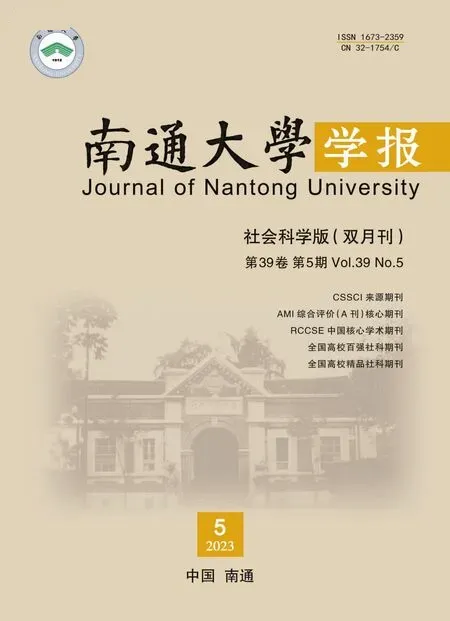论黄蓓佳小说抒情艺术的嬗变
吴学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黄蓓佳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是当代鲜见的成功跨界作家。她的小说侧重于演绎和探讨家庭亲情、人生困境与人性伦理,而“情”自然而然就成为其叙事的着眼点和推动力,因而抒情在小说里占据着重要地位。学界习惯于分开研究黄蓓佳的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而容易割裂她小说创作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忽视了其小说抒情艺术的嬗变与升华。如费振钟认为她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就结束了“抒情诗时代”[1]。实际上,黄蓓佳小说揖别青春梦幻与浪漫风格,而增强社会现实叙事,但并未抛弃青年男女情感纠葛这类题材,更没有让抒情陷入萎缩或停顿状态,而是转变了抒情策略。那么黄蓓佳小说的抒情策略具体是如何转变的?这种策略转变是否丰富了抒情内涵?又使得抒情提升到了怎样的境界?本文将着眼黄蓓佳小说创作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探讨其抒情艺术的嬗变和意义。
一、从浪漫外现到美感内化
20 世纪前期,中国小说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这主要离不开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吸收归化和西方小说技巧的借鉴移植。然而,中国小说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如其中就继承转化了“史传”“诗骚”等中国文学传统。五四时期,作家们急切地要进行思想启蒙和个人情感表达,先天性地看重“诗骚”传统,即中国抒情传统。陈平原认为:“‘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结构上引大量诗词入小说。”[2]212这种引“诗骚”入小说的艺术尝试便创造出了现代抒情体小说,当然同时融合了西方浪漫主义。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文学再次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青年知识分子充满着激情与浪漫、光荣与梦想,积极推动小说实验和变革,浪漫主义迎来了崭新的契机。对黄蓓佳来说,80 年代是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她没有了家庭出身的牵连,上大学、写文章、谈恋爱、爱跳舞、迷音乐,虽有酸甜苦辣,但还是度过了“美好时光”[3]106。时代文化和浪漫氛围影响着她小说的抒情方式和风格。黄蓓佳说:“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写作上经过一段‘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过程。那时候的我有点像一张宣纸,苍白而敏感,稍稍粘上一点墨汁,马上洇出黑黑的一片,雨一般雾一般地在心头缭绕不去,弄出许多惆怅许多忧伤。”[4]1查建英认为:“20 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5]3因为市场经济与科技革命大潮很快席卷而来,实用主义与功利倾向大行其道,文学随之迅速边缘化,而浪漫主义“更多是存在于艺术精神、忧患意识、启蒙立场与英雄气质之中,而出于‘现实’、归于‘现代’的理解方式,又使其很难走出一种历史与观念的‘限制’,这样,所谓‘变革’过程中的‘浪漫’的理解就很容易止步于外部的表象”[6]。所以,浪漫主义抒情很难展示出轻松怡然的姿态,常常为其他文学手法或风格所涵纳或淹没。20 世纪80 年代末,黄蓓佳的社会观、人生观发生了转变,“热情的充满梦幻的黄蓓佳变成了冷静的现实的黄蓓佳。她把她的笔触伸向了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人生”[7],小说书写由“意识内容向具象内容转化”[8],“浪漫的理想逐渐隐没,代之以沉重的人生价值的思索”[1]。
然而,黄蓓佳小说叙事风格转变是否标志着黄蓓佳抒情时代的结束?丁帆先生以黄蓓佳几十年老朋友的身份表示:“我并不认为她的浪漫主义元素就在现实生活描写中消逝了,被瓦解和遮蔽了,相反,她用成熟的哲思剔除了青春期冲动的浪漫激情,转而植入了冷静的浪漫描写,带着‘忧伤的浪漫’进入主题的深层模式表达之中。”[9]他认为黄蓓佳小说里的浪漫主义元素始终存在,只是浪漫模式与抒情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艺术既有西方浪漫主义元素,还赓续着中国抒情传统的基因,只不过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小说里表现的力度、方式及效果可能不一。换句话说,不能把中国语境下的抒情完全等同于西方浪漫主义。西方抒情文学真正发展是在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也偏于直抒胸臆型,敢于直接表达个人的主观思想与情感”[10]。20 世纪80 年代,黄蓓佳小说抒情最显在的表征就是耽于人物内心感受的陈述或精神心理的思辨。随便翻开她那时期的任何一本小说集,都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丰沛细腻的青春情感与黏稠绵密的忧郁情绪。1980 年发表的《阿兔》属于叙事者的回忆,全篇渲染着悲情与伤感,以至于丁玲阅读该篇小说“好像罩在一重悲伤的雾霭中,不觉得在心上压了一块石头”[11]2。小说集《这一瞬间如此辉煌》完全是一本青春漫溢、幻梦忧伤的情绪之书。其中《请与我同行》主体就是修莎的生活回忆及几段情感的心理感受和反思;《雨巷》写的就是情感追求不能实现而来的惆怅失望、遗憾哀伤的情绪;《这一瞬间如此辉煌》《我们去摘秋天的果实》《秋色宜人》讲述的是大学毕业生在人生道路上探索的忧郁与追求的微苦。黄蓓佳自己都评价这些小说“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自我,太狭窄,在空中飘着”[12]。普实克对中西抒情文学传统作了比较后指出,西方浪漫主义具有“夸张的个人主义、悲剧色彩和厌世情绪”[13]4。据此以揆黄蓓佳小说,其直抒“青春期冲动的浪漫激情”,以及对青年的惆怅、迷惘与失意的大量书写,主要表现为西方浪漫主义风格特质。因此可以说,80 年代末黄蓓佳小说书写转变是浪漫主义抒情时代的结束,但是她同时开启了对中国抒情传统的传承转化。
20 世纪70 年代,陈世骧发掘出了与西方叙事传统相颉颃的中国抒情传统,但主要是从材料考据的实证主义层面出发。高友工则从哲学思辨的本体论高度,构筑出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体系和理论观念,梳理出一套中国抒情美学的理想架构,即抒情美典。抒情美典是以主体美感经验为文艺作品的本体或内容,保存这个经验的方法就是“内化(internalization)”和“象意(symbolization)”[14]93。所谓内化是把外在材料转化为记忆或心象等的审美活动;而象意(符号化)是把美感经验转化为符号形式的物化活动。黄蓓佳小说转向后的抒情策略契合了高友工阐述的抒情美典。首先,她很少直接表现情感倾向,更多将外在对象或刺激内化为记忆或心象等美感经验。《目光一样透明》写的是特殊年代江心洲里的男女情感,很少沉浸于心思辨析。女主人公小芽出场:“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天空蓝得透明。满岛子的芦苇花开得有些败了,白色的花絮漫天里飞飞扬扬,屋顶上、门前晒着的蓝印花棉被上、人们的发梢睫毛胡须上,哪儿哪儿沾得都是,腻腻歪歪,躲又不行,拂又不行,挠心得很。”[15]1这既映衬了小芽澄明柔和的形象,又暗示着少女的烦忧心绪和心灵苏醒,隐喻了洲上缠绕纠葛的恩怨情仇,为混乱纷扰的时代作了注释。黄蓓佳在风景描写里注入了个人生命体验,将之内化为时代心象和集体记忆,实现了事与人、情与境、物与我的统一融合。其次,她通过建构符号化系统保存美感经验。《野蜂飞舞》里,《野蜂飞舞》是钢琴曲名,是黄橙子与沈天路的爱情媒介,还是故事线索,形成了符号体系,承载了黄橙子与沈天路的情感历程和内涵。《太平洋,大西洋》里,“荆棘鸟”“多来米”、小号、号嘴等,构建出了人与物、今与昔交织的符号系统,谱写出一首有关历史、信仰与友谊的“悲怆奏鸣曲”。黄蓓佳已然跨越听觉与视觉嗅觉的沟堑,构建出色、香、味齐全的符号体系,真实立体地抒写出人物的情感流动与美感经验。
每种文化里都有抒情传统,还有与之平行对立的叙事传统。高友工认为,叙事美学“目的是‘外构’(proiection)而成为一种‘外现’(display)在欣赏者面前陈现,它的手段是‘代表’(representation)和‘模仿’(mimesis),故是一个外向的美典(extroversive,centrifugal),以求陈现一个可以为人共知共感的外在世界”[14]147。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在不同文化里有不同形貌,但分别在中、西方文化里更能突显各自优势特色,故而西方强大的叙事传统制约着浪漫主义的抒情表达。黄蓓佳在早期小说里乐于抒写个人的青春情感和蓬勃思考,使得小说叙事者常常沉浸于内心独白和见解发表的状态。如小说集《这一瞬间如此辉煌》里都是青年人的婚恋、事业的故事,但更多展现为这些年轻男女的所思所想,导致小说故事性、情节性弱化而散文化倾向突出,但是这些作品“得到了很多同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呼应,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我的小说,因为作品和他们的思想同步,比较浪漫、华美、小资”[12]。可以说,80 年代,黄蓓佳小说的浪漫主义抒情受到西方叙事美学的影响限制,有着显著的陈述“外现”意图,更多体现为“模仿”和“代表”青春情感,创造出了当时年轻人能够“共知共感的外在世界”。进入90 年代后,她书写了大量的社会现实,但明显冷静沉稳下来,且努力借助内化与符号化手段,以求达到内省自我与反思时代的境界,而这正是中国抒情传统重要的艺术策略。
二、从抒情化自我到主体间个体
陈世骧认为,初民之“兴”是中国文学之本、抒情精神之本。高友工的抒情美典把美感经验作为研究中心,既重视创作者的文艺创作过程,又不忘文学欣赏中的“主体再经验”,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个人主体性。普实克同样注意到中国“‘抒情’传统关注的是作家的主观感受和情绪、色彩与想象力的再现”[13]2。他指出清代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私密性和个人主义色彩”[13]107,对五四文学形成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的作用深远。以上诸家论述折射出以下事实:首先在抒情传统的论述里,“主体”“个体”及“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内涵有所重叠或相近或互补,基本可以混同或替换;其次抒情文学创作或文学里的抒情表达皆需要主体,且至少应包含作者与文学人物两个层面。实际上,就“主体”与“个体”来说,两者属于历史性概念,内涵并不一一对应。人作为主体是自笛卡尔赋予人类以理性开始,至康德以先验自我作为认识和构造万物的根基而完成,自此“主体”明确涵纳了自我、理性、意识等意义。当人的中心地位确立之后,个体的独立性、生命独特性与个性自由得以展现和高扬。然而,拉康的主体性理论解构了现代理性“主体”的幻象。他把主体存在分为想象(The Imaginary)、象征(The Symbolic)和真实(The Real)三个界域。想象域对应镜像阶段,可以理解为自我对某个对象(“小他者”)的想象认同与模仿内化;象征域是语言符号场所(“大他者”),人的主体“我”在这里被召唤建构;真实域是“象征结构所创造和环绕的空隙和空无”,处于此域的是无意识主体“它”[16]25-26。据此可以说,人的“自我”是想象认同的构成,“主体”是由语言符号赋予。主体建构就是对某个“小他者”想象认同与模仿内化,而后分离转向接受一个“大他者”质询召唤的循环替代历程。抒情美学本来就讨论主体对外在对象的内化和符号化,所以不需太过强调拉康理论的解构性,反倒可以借鉴它来透视和讨论文学如何建构人物主体并抒情。
在面临着民族危机的中国近现代,救亡图存成为个体想象(“小他者”)和民族国家期望(“大他者”)高度一致的目标,表现在现代文学讨论场域,就是“个体”“自我”与“主体”大都被等同使用。如郁达夫的《沉沦》属于“自述传”的抒情,有学者指出其“最终生成的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自我和主体。郁达夫在无意识中与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达成了吻合。或者说,郁达夫的主体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质询’的结果”,“‘总体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召唤,使个体变成自己所需要的主体”[17]。当然,中国现代文学里的感时忧国之情,传承转化了中国抒情传统社会性与道德性。80 年代,国家没有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召唤着个体的主体建构,但不再是单极化的要求,个体获得了广阔多元的主体空间。黄蓓佳“1978 年初进入北京大学,改革开放同时开始”,“大量接触到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对过去的创作有了彻底反思和否定,但是却不知道新文学道路怎么走,很徬徨。也多次下河试水,但老是走不通”[12]。她此时在小说创作方面仍未形成明确方向,造成小说人物主体常常处于分裂状态,即一方面是有着丰富内心活动的抒情化自我,另一方面不忘呼应意识形态或宏大目标的召唤。比如在《请与我同行》里,女大学生修莎有着浪漫的校园生活和丰富的个人情感,不断找寻合适的男朋友,目的就是能共同到荒凉郊外修复宋代建筑遗迹朗润园,从而实现她始终怀有的复兴民族建筑的远大梦想。黄蓓佳这个阶段的小说主要想塑造抒情化个体形象,又胆怯于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于是常常以宏大目标或主流价值(“大他者”)来约束自我想象(“小他者”),因而个体与主体很难整合但充满张力,使得小说太理想化却很浪漫化。
进入90 年代,黄蓓佳告别了迷惘青春和浪漫年华,转变为陪伴女儿成长的母亲。随着女儿进入紧张的小升初阶段,她对教育状况和儿童成长有很多切身感受和感慨。此时黄蓓佳兼有矛盾和张力的思维模式先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收获了成功,因为儿童文学创作毕竟有所约束和局限,需要用宏大或正向目标来召唤儿童成长和主体建构。《我要做好孩子》里,金玲活泼好动、性格直率、悲天悯人,但就是学习马虎、成绩平平,不是家长与老师认可的“好孩子”。金玲只能按照社会主流意识认可的“好孩子”标准(“大他者”)建构主体,放弃了不少自我特性(“小他者”),一波三折后还算成功。然而,金玲的成功并不具有可推广性。首先她得到了退隐名师孙淑云的喜爱和辅导,这种偶然巧遇近乎神迹。另外,假如金玲成绩没有提升,那就很难算作主流意识认同的成功。黄蓓佳觉察到了这些问题,随后的《今天我是升旗手》继续讨论孩子成长问题。肖晓梦想做一名升旗手,那就必须成为品学皆优的“好学生”(“大他者”),而他成绩不突出,曾被迫把到手的机会让给“学习尖子”。尽管如此,肖晓没有完全接受“大他者”的质询,而是努力保持自我本色,努力磨砺优良品质(“小他者”)。最后,学校不再以成绩优异作为升旗手的充分条件,那么“大他者”召唤的标准发生了调整,肖晓的个体和主体从而保持一致,成功当选升旗手。相比金玲,肖晓的成功更有普遍意义和引领价值。两部小说充分展现了儿童个体需求同主体建构之间的距离、矛盾与磨合,为诸多情感的释放和表达创造了宽广的空间,其中蕴含着学生个性被规训的苦恼与丧气,家长对孩子成长的关切、同情、焦虑和期待等复杂感情,群众对评价孩子标准的忧虑及对其转变的期冀。
黄蓓佳透过儿童成长书写,意在强调主流意识召唤主体建构不能简单地单向输出,而应该尊重个体的主动性和特殊性。儿童文学有着教育引领功能的制约,需要尽量统一自我主体建构需求与国家民族发展号召,而成人文学里的主体就有了多元面向的选择,更能体现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女性作家,黄蓓佳自然关注女性的现代主体建构,特别是当远离青春岁月,对女性的观察和思考会更加冷静而深刻。《所有的》《家人们》是她在新世纪创作的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所有的》主要讲述双胞胎姐妹艾早、艾晚爱上了同一个男人陈清风的故事。艾早是个率性自由的女性,也是她认同的形象(“小他者”);妹妹艾晚自幼把姐姐作为羡慕的对象(“小他者”);陈清风则是召唤她们主体的共同“大他者”。艾早始终没有得到陈清风的爱,在精神崩溃之际,还因给陈清风私生子牟取巨款而落入监狱,是为接受“大他者”的召唤而牺牲自我。艾晚最后放任情感出轨,看似主体建构的突破,实际上只是将率性自由的姐姐从“小他者”转换成“大他者”。双胞胎主体建构路径相似,但毕竟是不同主体,注定了二人矛盾和悲剧的结局。《家人们》选择近似母女的杨云和乔麦子作为讨论对象。就杨云来说,乔六月是召唤她一生言行的“大他者”,工作只算是“小他者”。实际上,她早已被乔六月背叛,最终在崇拜“大他者”的幻想里离世。养女乔麦子相反,始终将事业作为“大他者”,而罗想农只是“小他者”。她与罗想农保持着主体间关系,具有自我独立性,最后迎来了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黄蓓佳有鲜明的“为女人而写”的意识,但不追求排他性的女权主义,“至今还没有觉察到有为女权主义而呐喊的必要”[18]。她描绘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主体建构困境,充分表明男女关系应属于主体间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更不能是“大他者”对主体的质询召唤关系,否则女性就无法摆脱受制于男性的宿命。
抒情艺术必须进入创作经验来讨论,而不是仅靠审美活动的解释。黄蓓佳逐步从浪漫自我转向冷静主体,在小说创作方面逐步找准了方向和风格。主体“具有能动力和责任能力”,但“在许多方面受限于其时代和文化可能性,虽然它具有一些力量去改变并发展那些可能性”[19]3。所以主体建构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具有流动性,主体之间就有了繁复多变的情感组合。黄蓓佳小说由刻画迷茫的自我抒情形象转向了对主体间个体的塑造,呈现出了蓬勃丰富的情感类型,以及细碎饱满的日常生活。她透过儿童和女性成长,描绘出主体经过模仿、内化、压抑、矛盾、突破等等路径而被确认为本质存在这个过程里的喜怒哀乐,同时强调人只有统一个体需求与主体召唤,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成功。
三、境界:抒情的多重内涵与意义
中国文学追求意境美,讲究境界营造,中国的抒情性文学更是如此。王国维认为论述诗歌特性,“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人间词话》九)。叶嘉莹就之阐释:“静安之所谓‘境界’,则似偏重在所引发之感受在作品中具体之呈现。”[20]248叶嘉莹强调“境界”是以主体感觉经验为特质,作者要能鲜明真切地表现所感知的“境界”。换言之,中国文学特性就在于透过语言文字,表现主体的生命深化和心灵升华,以达到一定的“境界”。正如宗白华所概括的“艺术境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21]287高友工进一步阐述:“客观现象最后可能完全与自我价值融为一体。我们可以视之为外物‘人化’(personification),或‘主观化’以与自我人格交流,表现深入的情感。也可以视为自我人格体现于外在现象中,这则是一种‘物化’(objectivazation),或‘客观化’。但二者都做到一种‘价值’与‘现象’合一的中文所谓的‘境界’。”[14]36高友工在宗白华观点基础上,突出艺术境界里的“价值”“人格”等元素,丰富了抒情主体美感经验的层次,扩大了“境界”的范围和内涵。他由此指出中国抒情传统“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14]83。那么,中国抒情传统就不是简单地以语言表达个人愿望的观念,而是“以艺术媒介整体地表现个人的心境和人格”的美学理论。由此推衍,“‘抒情’可以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类型,一种情怀,也可以是一种表征体系、知识系统,甚至可以是一种由情感、历史驱动的意识形态”[22]426。因此,文学抒情营造的境界除了容纳个人的生命价值、理想、心境与人格等内容,还展现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识形态。
叶嘉莹基于“境界”说,认为抒情传统“本质上就是一条感觉与感情的系带,它系连了个人与社会,并扩充到自然界。而当这种浑然一体之情,从时间上纵的延展下来,就产生了连绵不断的历史意识”[23]109。因而历史“有情”,主体通过抒情表达能“反思历史的危机与转机,群与己的关系,艺术与诗学的诸多形式”[22]3。黄蓓佳是位有着历史意识的作家,早期《阿兔》《月光》《朋友》《请与我同行》等诸多小说都有对特殊时代的反映和反思,但主要顺应着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题和风格,或多或少存在着简单化、模式化倾向。《阿兔》里,“我”和阿兔在特殊时代从亲密朋友变成对立面,“我”受到时代狂潮影响而丧失了理性,后者被时代主流排挤而磨灭了感性和理想。随着进入新时期,“我”和阿兔身上的本性和理想逐渐复苏。小说批判了特殊时代对人性的扭曲,把两人都作为受害者来讨论,而缺乏对“我”伤害阿兔言行的深刻检讨和反思。《请与我同行》将主人公修莎父母离婚、母亲去世、姐姐牺牲都放到特殊时代,在制造压抑悲痛氛围的同时,将个人不幸遭遇都归咎为历史原因。这些小说书写大都通过今昔对比,批判特殊时代的戕害,渲染个人悲情,但还缺少历史深度的掘进与复杂人性的辩证。90 年代之后,黄蓓佳小说的历史书写不再汲汲于简单的批判或赞扬,而是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讨论人性与民族性。首先,探寻特定时代的人格与人性。《目光一样透明》的历史背景仍然是特殊时代,但没有时代的混乱无序和人们的精神扭曲。小说虽然书写了悲伤的情感和不幸的人生,但突出的是人物的坚强性格与温暖人性。如温医生跟随妻子下放,但始终保持儒雅澄澈的性格,追求生活品质和艺术;欧阳老师受丈夫政治牵连,但是性格坚韧又重情重义,独自照顾孤儿黄滔,并将之培养成才。江心洲上的各色人等由于时代原因萍聚,但没有狂热、愚昧与险恶,而是各安其心、和谐相处,洋溢着细腻温婉、自然优美的人性美。其次,能够跨越不同时代,纵深考察历史天空下的个体与群体。《世纪恋情》以晚清到抗战为历史背景,描绘了启明、秋明与刘仁、林眉两对青年的人生选择和情路历程。两对夫妻的政治、事业方向均异,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都不畏艰险积极投身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小说没有以政治色彩来判定人物善恶,而是注重通过人物不同的选择和姿态,展现时代风云之下个体生动饱满的情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坚强的民族气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抒情境界的内涵与抒情主体的见识、人格、修养、情怀等息息相关。宗白华指出,境界美的创造“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21]290。黄蓓佳出身书香之家,既富有历史情怀,还具有不俗的文化品位。她在早期小说里经常用文化内容来推动氛围营造和抒情表达。小说《请与我同行》题目出自惠特曼的诗《大路之歌》,文本内容除了大段引用现代诗歌,还涉及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文化书写,让本就浪漫的大学恋情更富有诗情画意。值得注意的是,黄蓓佳此时已经流露出书写和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偏爱。《请与我同行》里,修莎传承了姨夫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热爱和深情,树立了修复建筑遗迹的远大理想,并与和自己在中西建筑文化认知方面有分歧的男友分手。修莎表达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自信:“中国的建筑并不都是宫殿,还有举世闻名的优美园林,有恬静的乡村居室,有世俗性很浓的庙堂钟楼,中国有自己的人本主义的文化意识,表现在建筑上,便是浪漫情操和诗情画意。”[24]64-65黄蓓佳早期小说关于文化的理解和思考,主要是直接嫁接在人物的言行之上,有些是为抒情而抒情,难免会显得突兀和僵硬,而随后的文化书写就逐渐变得自然婉转且质地雄健。《世纪恋情》里,启明在留学过程里经由对比中美建筑,真切感受到中国建筑文化底蕴的深厚:“美国之梦?美国人的梦想?那么,中国人又在梦想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之梦?中国的四合院,中国的骑街楼,中国的瓦檐翘脊,那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梦幻的结晶,它们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呀。”[25]265启明夫妻正是在立足于民族高度的不断思考里,自发担负起保护和传承中国建筑文化的使命,毅然从美国回到兵荒马乱的中国,跋山涉水到各地勘访测绘古建筑。小说把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孺慕之情融入启明夫妻的生命历程,催化其爱情由浪漫向深沉质变,诠释出了中华儿女历久弥坚的文化自信与爱国热情。
黄蓓佳小说里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并非割裂,而且只有当两者融合才能更好地表达深刻的思想意识,创造出宏大崇高的情感境界。《世纪恋情》就展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不同路径,解释了中华大地历经劫难仍斯文在兹、文脉绵延的原因。实际上,黄蓓佳所特别关注的教育和女性问题只有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讨论,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宏的美学境界。如《野蜂飞舞》书写了抗战烽火岁月里中华教育弦歌不辍的故事。内迁的金陵大学教授们无惧艰苦危难环境,仍然无私奉献,正是在他们的熏陶引领下,沈天路和黄家大哥、大姐都选择奔赴抗日前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主角黄橙子在与兄姐的相处过程中,受到影响并不断成长。小说是老年黄橙子的回忆,可以说她一生都在兄姐的精神感召下成长,而这种成长显然是民族精神的赓续。所以,有学者评论《野蜂飞舞》:“超越了儿童文学中大多数战争题材作品的园囿,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中战争文学领域的一个翘楚,以文学的细腻经纬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担当和文化使命。”[26]9
中国抒情传统注重生命价值、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的蕴藏和融入。文学作品必须让人们感觉与反省之后,在生命上获得“由日常的向审美的、低级的向高级的、物质的向精神的攀升超越”[27],才能实现融美感与真理、道德于一体的境界。黄蓓佳在小说里始终内化着自己的生命体验、文化涵养与美感经验,融入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有情观照和理解,建构出多重层次的抒情内涵,不仅有对喜怒哀乐之情的诗意诠释,还有对生命态度、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家国情怀的宏大演绎,从而创造了富有人性温度、历史深度、文化高度与思想力度的抒情境界。
四、结语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不少人将现代情境里的抒情艺术等同于浪漫主义技巧。实际上,中国抒情传统源远流长,在现代文学体系里经过传承转化,仍然生生不息、光彩焕发。黄蓓佳小说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抒情主要表现为对浪漫主义的模仿和外现,而后来的书写转型最显在体现就是抒情策略的嬗变。首先,她告别了青春的梦幻与伤感,积极转向繁复深厚的社会现实,其小说不再示人以浓稠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是通过中国传统抒情的内化和符号化的手法来保存美感、隐喻情感与注释时代。其次,她在由浪漫多情走向冷静深沉的过程里,逐步意识到人的主体建构既主动也被动,而引领主体建构的意识形态即使宏大而正确,还是应该尽量尊重个体的主动性和特殊性,否则可能会造成主体的内在分裂与不幸命运。所以,她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逐步从耽溺于抒情表达的自我转变为主体间性突出的个体,有意突出融合统一主体召唤(“大他者”)和个体需求(“小他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契合了中国抒情传统所强调的社会性与道德性。黄蓓佳是位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的作家,既能站在民族和国家高度观照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又能从历史与文化的层面审视儿童、女性及知识分子的生命成长和价值追求。她小说的抒情策略经由嬗变转化,扩大了抒情可以表达的边界和内涵,既能诗性抒发个人层面的情感体验、理想追求,又创造出了展现时代脉搏、民族风骨与文化自信等价值意识的宏阔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