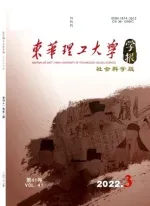女性写作的挣扎与困顿——论王安忆长篇新作《天香》
邓 婕, 毕文君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如果在当代文学版图中划分领地,上海这座城市当归属于王安忆的名下。尽管王安忆否认她对上海的亲近与喜爱,也并不认同大众冠以她“上海代言人”的身份,但必须承认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中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脉搏和精神地理把握得最为准确、深刻、细腻的一位女作家。自《长恨歌》将她推至“海派传人”的位置之后,她开始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视角进一步挖掘上海这座城市。特别是近些年的作品,从《富萍》到《遍地枭雄》,从《启蒙时代》到《月色撩人》,虽然地理背景仍然都是定于上海,但几乎每部作品都在寻求新意。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乐于看到一个作家推陈出新,但是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特别是对一位女作家而言,面对单一到多元这一艺术哲学的永恒矛盾,作家想要寻求突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与自我意识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是在面对陌生的写作素材时在把握上气力稍显不足。《天香》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王安忆对以往写作套路的一次颠覆,也是她作品中将这种写作的困顿与挣扎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部。
1 地方性知识的介入与日常生活的疏离
王安忆在做《天香》访谈时曾谈到:“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接近小说这门艺术。小说其实是描写生活的,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有兴趣。”[1]事实亦是如此,她本身就是一位擅长书写日常生活的女作家。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对王安忆就曾有过一段十分精妙到位的分析:“王安忆是只写日常小事的作家。从最初开始。她也并不排除超越了每日生活范围的深刻事件及离奇事情。在她的想法之外,有一种调节深刻性和离奇性,使之变成令人感到很亲近的,非常牢固的日常感的东西。可以说,这一方面是她的弱点,一方面也是她的强项。在巧妙地容纳了威胁每日亲近和睦状态的冲击部分的空间中,原本保守性的日常生活显示出了卓越的深度。”[2]而这一次,《天香》的问世似乎是王安忆在试图推翻对她只写日常小事的定论。
小说《天香》的故事背景被作家安放在了晚明时期的上海,讲述了从明嘉靖三十八年到清康熙六年这百余年间申氏家族由盛及衰的际遇,以此串起一段关于“天香园绣”这一刺绣工艺从产生到流转到回归的传奇。面对这一历史题材,作者很自然地告别了以往写世俗小事的类型化叙述方式。从曾经写世俗到如今写古雅,王安忆的方式是直接的。雅便雅得彻底,不留一点余地。于是知识在小说中的地位便凸显了。可以看到,作品涉及了天文、五行、食货、诗画、器物、管制、民俗等众多门类。不仅如此,还将当时的朝廷权争、海上倭扰、土木之兴的历史史实以及张居正、董其昌、徐光启等名流史传也都掺杂了进去,俨然像一部上海的地方志小说。这种唯物性的知识考古型叙述方式也的确可以算是作者新的写作尝试,但这样的尝试对于擅写日常小事的女作家而言,不可不谓一种冒险。如何把这种冰冷如器物般的知识融入作品的精神基调,而不只是作用于作品的叙述基调中,这对女作家是一件难事。作家努力想通过知识表现作品古雅的精神气质,但仅靠堆砌知识而来的古雅反而显得有些许生硬与做作,远不如《长恨歌》里的俗艳来得畅快有生气。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知识性很可能会降低作品的故事性,影响阅读的兴致。但这正是女性写作的瓶颈所在,知识似乎是女性经验中几乎不曾观照过的对象,也是女性作家很难把握和感受的对象,这样一个物种又如何能去融入进作品的精神气质呢?
从另一个方面看,作家似乎试图在摆脱自己原来擅长且趋于定型的自我和风格化的叙述腔调。对于王安忆来说,她不在自己擅长的女性情感心理和微妙的人物关系上着墨,转而尝试用一种客观化的笔调讲述一个物件的来龙去脉,这样的转型很难有所突破。作者曾在《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的信中谈道:“我努力地要摆脱一个东西,一个自己的视点。这样做下去,会有两个结果,乐观的话,那么最终会获得一个宏大得多的,而又更为‘自我’的观点;可是,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结果,全是徒劳,因为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3,4]从对日常小事的书写到宏大的考古性叙事,女作家如何表现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该不该脱离个人经验去表现,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王安忆写作的一个困惑所在。
2 历史的展开轨迹与故事的处理方式:女性意识的刻意淡化
遵循唯物主义原则的写作若是仅仅摆脱个人写作经验的束缚而利用客观化的叙事腔调显然是不够的。要端起一个宏大的历史题材,除了用大量的考古性知识和史实材料堆砌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还必须摒弃作家自己的当代意识进而去融入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让所有的人物特性都符合具体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必然要求。
小说《天香》虽然讲述的是刺绣工艺的传承,但传承必然要以人物为轴心,才能牵扯出工艺的发展和演变,由之拎出故事的主线。我们可以清晰抓住《天香》内三个主要的人物:小绸、希昭与蕙兰。正是这三位核心人物的不同命运才有了天香绣从民间产生,经由贵族阶级的提升,又回归民间的整个大的故事脉络,同时三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又构成了三个小的叙事单元。这样的故事结构,按照作者以往惯常的笔墨,三位女性悲欢离合的人生将构成整部小说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会是凸显作品的灵魂所在。而这一次,作家却轻描淡写地将人物的重要地位削弱了。作者刻意塑造了小绸的倔强、希昭的高卓与蕙兰的纯真,但人物的性格刻画却没有伸向更广更深更复杂的维度,只是变成了一种脸谱化的描摹,在把她们的命运托付给天香园绣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慧手兰心、内心笃定的单一式性格原型。尤其是沈希昭,这个承担传达作品精神要旨的关键角色,在这个历史故事中本该风云际会、谁主沉浮,作者却用笔过轻。杭州城由一位道姑引出的神秘化出场让沈希昭这位人物一开始就被渲染得有些传奇意味,而从南宋遗珠到武陵女史,俨然更有可能成就一位充满个性、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但是故事在进入上海之后整个人物形象立即变得黯然失色。希昭高卓是高卓,却像隐士般深居简出,即使面对阿潜的出走和归来,除偶露点点焦灼与痛心外,仍是一副气定神闲、不问世事的世外高人模样,看起来缺少一点人性的光彩与可爱,所以作品对这一人物的处理使本该鲜活的形象变得些许做作和呆板,显然也无从承载作品在精神层面那些深高和更为多维的历史向度的展开。
对于王安忆这样一位能够触摸一座城市精神脉搏的作家而言,这样草率地安置她的小说人物一定有她的用意或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方。一位女作家,她的当代意识最为关键的部位便是她的女性意识,而面对晚明这样一个时间拐点和历史叙述面影,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又要求她必须还原历史的真实感,但这种在当时的历史朝代必被冠以离经叛道的女性意识根本很难被安插进历史叙述之中,更无法让这种意识合法化与合理化。那么如何让这个虚构的历史故事顺理成章,作者除了添加更多的历史素材去营造或证明一个天工开物且具有开放思维的社会存在,似乎别无它法。另一方面,作者却不得不淡化人物的存在感,通过单面呈现她们的思想性格并尽可能让她们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方式将人物、故事笼统交付给所谓的民间社会,似乎不如此就无法回避作者自身当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相冲撞与矛盾的地方。不得不说,这也是王安忆为这样一个历史素材而潜心思考之处。如何把当代意识融入历史素材,对王安忆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与挑战,尽管在处理上有些笔墨失衡之处,但也由此可以看到作家的努力与用心。
3 由“去人心而写物性”向“圆融女儿心”的回归之难
无论是用大量的考古性知识去营造或烘托起客观化的作品氛围与叙事基调,还是作者刻意淡化对人物的塑造以回避自己的当代意识,作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去人心而写物性”。摆脱自己的观点去客观描述一个物件的存在,这原本就是一个悖论,如她所言:“事情一开始就是徒劳,因为一个人是永远无法离开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3]于是我们看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又从物性写回了人心。
小说的前两卷所刻意营造的远离世俗、古雅高妙的境界,在第三卷受到了一股来自现实的强大冲击。在将天香园绣导向了生计之后,作者又写回自己擅长的世俗生活,故事叙述也在这一部分才显得从容而富有张力。前两卷中过多生硬知识的杂烩其中及那些淡化了故事感的戏剧冲突,可以说使整个叙述更趋向于明清世情小说客观蓦写世态的基调。而在重新回归自己擅长的领域后,作家的笔墨游走顺畅而婉转自如,读者也能再次感受到王安忆笔下熟悉的那“圆融女儿心”:这些人就像路边田间那类没有姓名的稗草,婶婶方才说的,浑然不自知,但其实,也有她们的心事[5]。
再如:婶婶你看那些野花,无论多么的小或者贱,不过半日,变又化进地里作了泥,可也有薄如蝉翼的瓣,纤长细致的蕊,顶着一丁点儿的蜜,供蜂们去采集,那就是它们的心事吧!这些心事或都是粗俗的,免不了爹死娘嫁人,或者缺衣少食一类的苦楚,可也是心事一桩,到底是女儿家,未出阁的,干干净净,就能将那些苦楚打磨成女儿心[5]!
小说结尾希昭与蕙兰一段关于天香园绣总结性的对话,一方面从希昭的口述中暗含了王安忆自己的诗学自忖,即:“希昭所言的技要工(要走大道而不是偏锋,过与不及同不可取),以及心要超越(不读书者不得绣,绣以诗书画做底)与王安忆所强调的作家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教养,是同声相应。”[6]另一方面,从蕙兰的对答中则不免读出了王安忆的一番写作感悟。蕙兰所言不过“人心”两字,那是:“无论天涯海角,总是在人世间”[5]。王安忆想摆脱“女儿心”,不写那世俗而写大境界,不写小人心而写纯物性,尽管我们看到作家的勤勉与用功,看到她尝试一切可能去超越自己,并试图为我们讲述一个不是她讲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不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有看见。”[3]但追求绝对客观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小说原本就是虚构之本事。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安排、不同的叙述方式,全都深深从小说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扩张着小说家自己的血液,写作从本质上而言是个人化的事情,否则也就只能陷入左拉式的写作怪圈,直至走向自我纠结的死胡同。
或许小说第三部分的回归正在此角度暗示了作者唯物主义写作的矛盾与困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王安忆在向上追求一种更为开阔的思想境界,这是她写作生涯三十年的过程中以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姿态完成她从青涩到成熟的人生蜕变。这里不仅指个人的人生阅历也是指向其作为一位写作者的人生圆融之途,她不再追求喧哗虚无的尘世,而更向往一份平和宁静的内心,所以这里也不再会有舞厅里浮艳旖旎的王琦瑶,而有了当下《天香》里内心笃定、埋首绣工的织女们。只是作家还未参透那份圆融女儿心的根蒂所在,因而才使作品在境界把握上显得过犹不及。但无论如何,落尽繁华,锦心犹在,《天香》这部作品在作家的小说创作谱系中也一定会成为值得我们长久谈论的一次写作实践。
[1]谭旭峰.王安忆:故纸堆里出《天香》[EB/OL](2011-07-25).http://www.eeo.com.cn/2011/0725/207071.shtml.
[2]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88.
[3]王安忆.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N].光明日报,1985-08-15.
[4]毕文君.谱系·图景·想象——当代女性家族叙事的主题形态与精神内涵[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2):140-143.
[5]王安忆.天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96-398.
[6]胡晓.写回去与写上来——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N].文学报,2011-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