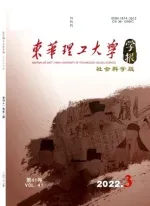重新审视沈从文的“生命观”
唐东堰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生命”是沈从文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代的是人的理想生命状态,也即“完全生命形式”。沈从文常用“如焚如烧”来形容它。与它相对的是“生活”,即残缺的“不完全生命形式”,沈从文常用“如牛粪一样无热无光”来形容这种不完全的生命形态。“生命观”就是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理解和看法。一般地说来,生命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生命”是什么的内容,二是生命应该怎么样的内容。前者关注的是事实,后者涉及的是价值。下面,笔者就从这两个方面对沈从文的“生命观”进行全面的审视。
1 “生命”的实质与特性
“生命”一词,沈从文虽然在文本中多次提到,但是很少对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做出正面的、确切的回答。沈从文第一次从其生命观的意义上提到“生命”一词大概是在1934年初写给张兆和的信中。他说:
这里的一切颜色,一切声音,以至于由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调子,如何能够一下子全部提来让你望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且计算着一切,我叹息了。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看着水流所感到的一样。我好像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我方明白我在一切作品上用各种赞美言语装饰到这条河流时,所说的话如何蠢笨。……人类的言语太贫乏了[1]212-213。单就写出来的文字看,上面这段文字只不过是一段普通的写景而已,然而如果注意到这些文字背后隐藏的“言说”,就会发现,上面的文字并不是普通的写景,它们当中还蕴藏着很多无法著于文字的东西,如“由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调子”等等。这个现象表明沈从文当时所欲传达的并不单单是“河”的客观外形,而是他在静观汤汤流水时产生的一种丰富的、主客交融的体验或者境界。这种体验是现实与“神秘”的界线,语言不到的极限,故沈从文感叹“人类的言语太贫乏了”。然而正是在这种难以言喻的“浑然一体”感中,沈从文“感到生存或生命”,并悟彻了“智慧”。这样的例子在沈从文的《湘行书简》中还有很多,例如:
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1]188。
这段文字中出现了“悟”、“智慧”、“透明烛照”等词语。在汉语中,这些词语都是与中国古老思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思想方式相关联的——“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发生的,而“智慧”也不是通过普通的认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得来的,而是一种心灵的“明悟”。虽然沈从文并没有在文中直接点明当时是一种“物我交融合一”状态,但是这些独特的用语却表明沈从文并不是在冷静地观察那一条河,而是把自己融入到了“河”之中,进入到了主客互渗的迷狂(沉迷)状态中去了。正如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认为的那样,这种“浑然一体”的体验是一种带有形而上意义的澈悟。它给我们“敞开一个与理念概念全然不同的世界,让我们领悟到不同于逻辑抽象所把握的另一种人生意蕴”,并“通过生命意识认识了自己,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2]47。沈从文所说的生命正是日常状态把握不到的“另一种人生意蕴”,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感悟”,即上文中所说的“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
除了从汤汤流水中明悟到“生命”外,沈从文也常常在对小生物(如,花草虫鸟)的痴迷、凝视中感受到“生命”或“生命最完整形式”。这种现象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也是大量存在的,例如:
一个小小金甲虫落在我的手背上,捉住了它看看时,只见六只小脚全缩敛到带金属光泽的甲壳下面。从这小虫生命完整处,见出自然之巧和生命形式的多方。……我想这个泛神倾向若用之与自然对面,很可给我对现世光色有更多理解机会[3]108-109……
能欣赏仙人掌神奇的人怕不多。这东西从表面看来,平平无奇,可是开花时也有个神性在生命发展中存在,而且完完整整!在这一点上,我倒有点艺术家的自信,从理解入手,于是居然发现了神[4]309。
马斯洛曾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些现象做过认真地剖析。他说,当人“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眼前”之物时,“他们能付出一切,更多地脱离他人,较少地意识到自己,较少畏惧、防卫和抑制,以无所求的、不干预的、道家的方式来承受一切”,因而“与当前的事物融为一体”即进入到物我交融的“浑然一体”状态。
问题是,为什么沈从文所说“生命”总是与“浑然一体”的状态相联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浑然一体”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忘我的潜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与客、内与外、我与非我是统一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主客、内外的分别,因而这种状态是与“天地精神的那种状态”相一致的状态。而“自觉的意识状态则是一种人为的状态,不是精神的本来状态,和天地精神状态不一致”[5]23,在日常的意识状态中,主与客、我与非我、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日常状态中的生命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它“总是追求一些具体的目标,总是受利害好恶的欲望所左右”[5]23。故道家哲学认为,“只有摈弃意识活动、摈弃自我意识,在潜意识的精神状态下,才能摆脱人生的各种负累,从而获得‘逍遥游’式的精神自由,进入至美至乐的精神境界”[5]23。沈从文所体验到的“浑然一体”的体验正是一种类似于“逍遥游”的状态。只不过老庄是通过“坐忘”、“心斋”的功夫一步步“丧失自我意识”,“最后进入潜意识状态”抵达生命的极致[5]23。沈从文则是通过对“美”的迷狂、沉迷来消弭主客、内外的界限,进入到“浑然一体”的状态中,感受到生命的极致。殊途同归,他们最终都步入到了生命的极端自由、谐和状态。对于这个现象,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做过精彩的解释。他认为人在日常现实中存在着很多二歧式、两极化的冲突,如体验我(实际我)与观察我(理想我)、理智与情欲、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的冲突。这些冲突到了“浑然一体”的体验中都被超越了或者说被融合了。各种身心的机能在整体统辖下和谐地运作,“成为一个融合的统一体”,因而生命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6]83。
事实上,把这种超越主客、内外界限的“浑然一体”体验(境界)视为生命极致状态的并不只是沈从文一人。如果把沈从文所说的“生命”放到世界文化背景下观照,我们发现,沈从文关于生命终极形态的设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佛教的涅槃境界、基督教的“与上帝同在”体验、尼采哲学的“酒神的迷狂”等等都是相通的。生命的最高点都归于一种忘乎所以、全心投入、自由畅快……总之最完美的境界(体验)。尽管不同文化、不同的人种在生命的具体形态上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描述人性发展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时,在设想生命的最高点时,都容易趋于相同。
既然“生命”是不可分析、不可言说的,那么沈从文作品中出现的那些关于“生命”的具体言说显然都不是从本体意义上言说生命的。因而沈从文文本中的关于“生命”的言说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例如:
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3]32。
这里的“生命”指的是那种对于“美”倾心的内在本性。在沈从文看来,追求金钱、道德、名誉等由人和社会制定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体现。“名誉、金钱,或爱情”在沈从文看来都不算什么,生命的内在本性在于对“美”的倾心,而“美”与“神”近,即与“人”远。因此“生命”实际上就是人追求超越性的本性的体现。
总之,沈从文所说的“生命”一方面是指主体在“浑然一体”状态中感受到的“透明烛照”、“毫无什么渣滓”的心灵状态,另一方面又指主体在“浑然一体”的状态获得的对于生命(人生)的觉悟。最后还指主体追求“爱”、“美”、“神”等高级精神需要的超越性本能。
2 “生命”的形式与内在本性的实现
按照人内在本性的实现程度,沈从文把“生命”分为“完全生命形式”和“不完全生命形式”两种。前者是生命的极致状态,沈从文有时直接称之为“生命”,有时称之为“生命最完整形式”,不管怎么称呼,它们都是指“生命”的最完美状态。沈从文常用“生命的疯狂燃烧”或“如烧如焚”来喻指它。后者是生命的不充分、不完美状态,沈从文常用“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来比喻它[7]237。在《美与爱》中,沈从文对两者做了详细地辨析: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蚀,已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逐渐都变成庸俗呆笨,了无趣味。这些人对于一切美物,美事,美行为,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毫无反应……这种人大都富于常识,会打小算盘,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蚤,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事。这些人所需要的既只是“生活”,并非对“生命”具有何等特殊理解,故亦从不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义[7]360。
显然,区分“完全生命形式”和“不完全生命形式”的依据是人心对于“美”的倾心程度。能够用泛神情感去接近“美”,并从中见出精巧处和完整处的就是最完全生命形式,反之只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的就是“不完全生命形式”。处于不完全生命形式的人爱名誉,爱“道德”,虚伪做作,装腔作势,看起来四平八稳,实际上“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凡事敷衍,无理想,亦无实现欲望的能力,他们“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3]33。而处于最完全生命形式中的人往往是那种对“美特具敏感”的“痴汉”。他们对于“美”的感受如同遭遇到神奇的“山灵”一样,一见倾心,忘乎所以,“失其所信所守”。在沈从文看来,生命“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3]94。沈从文的作品存在着大量的关于生命最完全形式的描写,例如: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3]43。
在沈从文的“生命观”里,“生命”的顶点和神圣意味不是某个外在的目标而是人心的自由、高潮、完美状态。人们在这种境界中可以“得到永生快乐的”。虽然寻求生命的永生也是各类宗教的共同目标,但是其他宗教大多有压制人的本性的倾向。沈从文恰恰相反,他所说的生命最高形态则是本性(尤其是那种追求“美”的超越性本性)的完美实现。这个观念在《看虹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关于《看虹录》的写作目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视之为恋爱小说的、也有视之为色情小说的。沈从文本人却认为这部小说是为了展示几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他在《水云》中也说,所谓看虹、摘星,采摘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即在女性美丽的肉体面前,他“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过去的研究由于没有意识到在沈从文那里对于“美”的痴迷正是生命最高意义的体现,因此他们无法把《看虹录》中“我”对于女性身体的心醉神迷与“生命”的最高形式结合起来。事实上,“色情”和“性欲”属于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它并不能激发生命向上,“向上即接近天堂”[8]141,更不能抵达沈从文所说的“生命”——一种谐和、澄澈的浑然一体感。故沈从文坚持认为:
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说毫无情欲……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认识了神与美[3]117。
《看虹录》中的女性身体并不是作为性欲的对象,而是作为“美”——一种高级的超越性需求而存在的。这种观点后来又在《莲花》中得到体现,沈从文说从“两条长长的腿子”和“猪耳莲”中“我看到的只是个人生命中/一点蓝色的火”[8]142,即在对“美”的痴迷中,作者“看到”的是最完全生命形式。然而,社会上的一般人总以为“美”与欲相连,对于那些对美特别敏感的人总是极力打击、迫害。沈从文认为这些观念都是不健康的。生命的本性本身(哪怕是性欲)应该是善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它就是道德立法准则,外在的规范不能压制它,相反还得受它检验。合理的社会和文化应该是充分肯定人对于“美”的追求的。因此,《看虹录》并不是爱情小说,也不是色情小说,而是以展示生命的“最完全形式”和新道德为目的的小说。
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约瑟夫·L·汉德森、约瑟夫·坎贝尔等人研究也发现,生命存在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满足“饮食男女”等孤立的本能或者目的性机制,而是心灵内核的完美表现。对于个体来说,超越性机能实现的最高目标就是“个体潜意识自我的潜能的圆满实现”[9]125。这个目标只有当“意识自我融入到潜意识自我时”才会实现[9]125。沈从文所说的生命最完全形式正是对于心灵内核的完美表现。他所说的“生命”不是指人的外在文化、道德生命,而是指人内在的追求美、爱和一切更高尚原则的超越性本性(机能)。生命的最高形式就是内在超越性机能的完全实现。正因为如此,沈从文才如此珍重对于美的迷狂(沉迷)体验,并视之为生命的最高意义。
3 “生命”与“乡下人”的道德重构
所谓‘乡下人’,特点或弱点也正在此。见事少,反应强。孩心与稚气与沉默自然对面时,如从自然领受许多无言的教训,调整到生命,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3]87。
类似的表述在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存在。例如在《主妇》中,沈从文说道:
和自己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市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举凡另外一时另外一处热情与幻想结合产生的艺术,都能占有我的生命。尤其是阳光下生长那个完美的生物。美既随阳光所在而存在,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复如云如水毫无凝滞。可是一种遇事忘我的情形[4]316-317。
概括地讲,“乡下人特点”就是指“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生命”的极致形式正是这个特点的完全体现。在沈从文看来,对“美”的入迷体验正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所在。他说,“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名誉、金钱,或爱情”在沈从文看来都不算什么,“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3]32。然而,都市文化以追求金钱和名誉为目的,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不光如此,还对那种“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美特具敏感”的人总是严厉打击[3]32。这种生存境遇让沈从文感到自己的“乡下人”本性被严重扭曲,他在《烛虚》中写道:
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天空中鸟也不再在这原野上飞过投个影子。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3]23。
远离“美”的城市生活形式抽空了沈从文的生命意义,活着只是时间无意义地延续。那么,如何重新获得“意义感”的生命呢?沈从文认为,只有在“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时,生命之火才可重新燃烧——“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感情恢复哀乐弹性[3]24。此时,人才算是活人。正是立足于自身“乡下人”本性的实现,沈从文才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
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外在的社会文化、时代因素在沈从文“生命观”形成中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都是外在的,沈从文“生命观”形成的内在因素是那个由种族记忆遗传、文化积淀和个人生活经历共同构成的“乡下人”的独特心理结构。外在的社会因素只能加速或者催发其“生命观”的形成。正如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所说的那样,真正的人是要完美地实现自己的本性。“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叫做自我实现。”[10]168同样的,沈从文只有在实现自己身上“乡下人特点”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完满实现。而他的“生命观”既是对这种实现的肯定,也是这种实现的成果。
与生命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叫“乡下人的尺子”。“乡下人的尺子”是沈从文独特价值体系的总称。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生命观”也应当包括在这个体系里面。沈从文虽然多次提到“乡下人的尺子”,但是很少对之做正面的解释。综合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创作来看,“乡下人的尺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1)肯定人追求“爱”和“美”的本性。(2)反对对于世俗道德观念的盲目顺从,反对以“道”制欲,要求人们超越世俗的观念,对于生命有较深的认识。(3)肯定人类对于理想的追求热情,要求人们超越“物的沉沦”,为人类更高尚的原则和理想受苦。(4)从现实层面来看,“乡下人的尺子”要求人们为人类远景凝眸,超越小我之私,把个人的力量粘附到人类、民族进步向上的事业当中去。这四个方面是沈从文衡量自己生命意义和评价一切外在事物的标准。沈从文说:
小厂还不错,环境好,有花有草的,东西排放得整齐,洗手间都飘着淡淡的清香。这大概就是女老板的特点了。大发厂的洗手间永远都是臭烘烘的,林老板从来都不会过问。
……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3]94。
在沈从文看来,“‘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和“一般标准”都是对于“生命力”的否定,这些标准、规范是不健康的。合理的规范不是对于“生命”的压抑和否定,而应是对于生命的肯定。这样一来,沈从文与马斯洛在思想建构上达成了一个重大的共识——理想的社会价值体系应该建立在对于健康人性的肯定之上的。他们所提倡的价值标准都有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基石,在马斯洛那里是人的某种“似本能”(一种积极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在精神上自我实现的本性)[11],在沈从文那里是“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马斯洛所说的那种“似本能”是从美国最优秀、心理最健康的人(即社会精英)身上研究归纳出来的。他发现“一切基本需要,个体所有天生的智慧和天才,都可以归入人本性内部的、生物学的、似本能的核心”(这与以往心理学家总是研究病态的人大不一样)[6]161。沈从文的“乡下人特点”是从自身或者湘西半原始乡下人那里总结出的,沈从文认为这种人才是心理最健康的人。“似本能”和“乡下人的特点”两个概念都是作为健康人性的意义提出来的。
以马斯洛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目标就是要以这种健康的人性为基础建立起一套从“人自己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以此来回答那些古老的哲学难题——“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怎样才能把人教育成期望和喜欢过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道德高尚的成人等?”[6]133这一套新价值观念是顺应人的本性产生的,而不是“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演绎出来的。沈从文则以“乡下人”为基础,建立了一套从“乡下人的特点”生发出来的价值观念——“乡下人的尺子”。这一套价值观念同样是顺应人的内在本性产生的,而不是接受了现成的“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一些道德、规范和标准。沈从文多次强调,自己不相信一切只相信“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也不是指外在的文化、道德生命,而是指人内在的,追求美、爱和一切更高尚原则的超越性本性(本能)。因此“乡下人的尺子”到底是对于内在“生命”的维护。在《水云》中,沈从文说道:
……不过度量这一切,自然用的是我从乡下随身带来的尺和秤。若由一般社会所习惯的权衡来度量我的弱点和我的坦白,则我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早已失去了[3]118。
以“乡下人的尺子”来度量,生命追求“美”(不论是美丽的自然还是美丽的女性)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命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对于“美”的完全投入[3]94。“乡下人的尺子”就是要求人们忠诚于人的健康本性。人按照“乡下人特点(本性)”发展,就是善,就是美(尽管这么做在现实生活层面会产生不便,但它并不产生恶和丑)。可见,尽管沈从文生命观的最初动机是个体生命意义的重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对外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负责任。事实上,只要现实了“生命”,世界就容易变得合理、美好,也就实现了更大的事功。从实践层面上看,沈从文的生命观是一种建立新道德、新价值的尝试。
这种改造社会的思路与马斯洛是一样的。马斯洛认为,尽管这些生物学的、似本能核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应尽的义务”或“道德的规范”,但是它们是“固有价值的赤裸裸的原基或雏形”[6]161。最理想的价值体系应该是从这些本性中“流淌”出来的。社会的规范不应该扼杀“生命”,相反一切规范都应该从“生命”中生发出来。“生命”应该成为新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它是“最终决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最高上诉法院”[6]3。沈从文的“生命观”最终沟通了个人与社会,实现了自我建构与外在文化建构的合一。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孙文宪.文学言说的意指与境界[J].民族艺术研究.2002(6).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刘文英.道家的精神哲学与现代的潜意识概念[J].文史哲,2002(1).
[6]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李文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荣格,等.潜意识与心灵成长[M].张月,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10]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1]郭永玉.马斯洛晚年的超越性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影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2):19.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