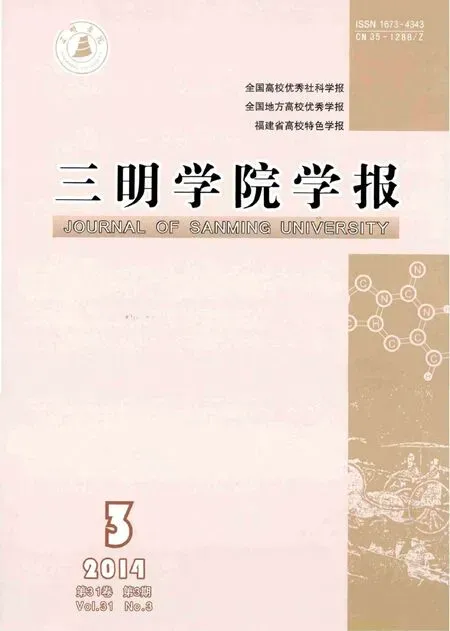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
林阳华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
林阳华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出现五世十人登科的盛况,并非偶然现象,这与苏氏家族非常重视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和学习方法的科举教育不可分离。文学和天文历法学作为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苏氏家族重视培养文学创作能力的文学教育,与对科学的热爱所采取的科技教育关系密切。而安邦匡朝、忠君爱民与父母在世尽职赡养、父母过世则尽丧礼的道德教育,对苏氏家族忠、孝家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家族教育,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传统
一、家族科举教育与五世十人登科之科举世家
元丰二年(1079年),当苏颂出知濠州时,他的儿子苏駉时彦榜登科,被赐予进士出身。《魏公谭训》卷十记载:“盖自天禧至是,盖四世九人登科矣。”[1](P1174)四世九人登科的盛况,使当时负罪在外的苏颂感到万分喜悦,他在《谢男駉赐进士出身》中说道:“报自胪传,庆丛私室”,“闻命兢惶,举宗荣惧”[1](P574)。然而喜悦和荣耀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元祐六年(1091年),苏颂之孙苏象先马涓榜蒙恩赐第,至此达到了五世十人登科的局面,为此宾客纷纷登门庆贺,其中刘彦的和诗云:“五世登科只一家。”虽然苏氏之后,尚有晁氏、韩氏皆五世登科,但能达到十人登科荣耀的,在宋代屈指可数,所谓“本朝五世登科者,唯衰族尔”[1](P1130),真实地透露了苏颂为家族所取得的优良科举成绩而骄傲。
宋代同安苏氏家族能够顺应科举时代发展的要求,形成了五世十人登科的家族文化传统,科举教育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同安苏氏家族在宋代所进行的科举教育世代延续,而且颇为严格。苏颂祖父苏仲昌的严格教诲使得苏颂在七十余岁时,仍旧记忆犹新,在梦中也为此而惊醒。苏颂父亲教导苏颂也非常严格,苏颂曾回忆说:“我昔就学初,髫同齿未龀。严亲年痴狂,小艺诱愚钝。”[1](P51)在很小的时候,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科考环境,苏绅为苏颂选择了一些可以相互切磋、相互促进的好友一同学习。《魏公谭训》卷三多次记载,苏颂回忆起早年与华直温、刘颁、刘敞、吕夏卿等好友,一同学习的往事。[1](P1136)苏颂在与他们一同学习中,学业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试想,如果没有苏绅的安排,年幼的苏颂为了应对科举的生活,将会是多么的寂寥、辛苦和无趣。由此,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苏绅在苏颂的科举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苏绅除了为苏颂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以便相互促进之外,还培养其科考写作能力。苏仲昌在苏绅年幼时,就非常重视培养苏绅的文学创作能力。《魏公谭训》卷九说道:“曾祖十岁时,有一道士自云善相。高祖令相曾祖,云:‘必达,当以文章显。’高祖令赠之诗,执笔立成……”[1](P1169)苏绅承续其父的教育方式,也特别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苏颂的写作能力。苏颂曾说道:“始时授章句,次第教篇韵。”在诗句下的自注中谈到,苏绅在苏颂五岁时除了教授儒家经典外,已经开始传授古今诗赋和声律。[1](P51)并且苏绅还让他同诸位叔父一起学习、相互切磋,共同培养和提升文学创作水平。《魏公谭训》卷三亦记载了苏绅在苏颂十六岁时,命其作《夏正建寅赋》,称赏其博学之事[1](P1135-1136),苏颂在日后的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被欧阳修等考官大为褒奖,称赏其博学多才,与苏绅的用心良苦显然不可分离。苏绅的几位兄弟,如苏绎“博学能文”[1](P1160),苏缄以“文学知名”[1](P1161),苏绅之子苏衮能够传承乃父之文,故苏绅称“衮得吾之文”[1](P1139),这跟苏绅的教育关系甚大。苏颂也特别重视培养子孙的文学创作能力,以应对科举考试。《魏公谭训》共十卷,卷四名为“文学、诗什”,即为记载苏颂向子孙讲述文学创作之事和创作之法而设。除此之外,在另外九卷中,相关论述还占有不少的比例。
苏仲昌、苏绅等先辈虽然对苏颂的科举教育极其严格,但也善于采用鼓励的方式教育之。踏上仕途从政,是宋代同安苏氏家族的美好愿望,除了科举考试之外,门荫等途径也可以实现。苏仲昌、苏绅尽管对苏颂等人抱着殷切的期望,然而在严峻的科举考试中,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看到子孙登科。因此,借用门荫使子孙走上官场,也成为了他们的另一种选择。《魏公谭训》卷二记载苏绅欲借用乾元节可推举子孙的机会,使之为官,在科举与门荫的较量中,苏颂毅然选择了科举,苏绅虽然屡次劝导,但最终只好作罢,转而鼓励苏颂继续努力,争取登科。尽管之后两位弟弟皆因门荫得官,而苏颂自己没有依靠门荫得官,但他并不后悔。[1](P1130)这一方面体现了苏颂励志科举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苏绅在严格的教育中,也能灵活地以鼓励的方式教导之。在科考即将到来之时,苏绅经常会以登科的重要性来鼓励子孙。《魏公谭训》卷三记载,苏绅勉励苏颂等人以高中状元为目标[1](P1136-1137),为同安争光之事,可以看出苏绅所寄予的厚望。
苏颂秉承了祖父、父亲的科考教育方式,将严厉和鼓励的方式灵活加以运用。苏颂虽然平时政务非常繁忙,但在闲暇之时,即会召集子孙,与之谈论诗文,并告诫他们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此,苏颂常常借用《柳氏训序》的例子作为教导的材料,所谓“太保每以猪胆和黄连为丸,令子弟含化,使读书不至困寐,故皆笃学有闻”[1](P1145)。努习学习是成功中举的重要因素,勤奋也至关重要。所谓“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1](P1162)。非学何以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除了勤奋、努力学习外,还需要掌握科学方法,才能够在科考过程中少走弯路。对此,苏颂通过令子孙抄写类书的方式,来扩大阅读范围。《魏公谭训》卷三云:“祖父取平日钞节,分门类令子孙辈传写二百册,古今类书莫及焉。”[1](P1139)可见子孙所抄写的范围是多么广,因此同安苏氏家族以博学著称,在科考中才能够得心应手。
苏颂同苏绅一样,特别在科考来临之际,也善于以鼓励的方式教育子弟。《魏公谭训》卷十记载,苏绅庆历初身任翰林学士时,仁宗曾赐予金带,之后苏颂为侍郎、尚书和翰林学士时,以佩戴此金带为荣耀。晚年又加以修治,并告诫子孙以后为官者可佩戴之。[1](P1179)这种行为如同苏颂所谓的“传衣钵”。当苏象先即将赴廷试时,苏颂对他说道:“唐人与主司名第同者,谓之传衣钵。先内翰第一甲,得职官;吾第三甲,亦得职官。尔若得职官,亦谓传衣钵也。”[1](P1129)此时的勉励,势必为苏象先参加廷试增加了信心。
宋代同安苏氏家族出现五世十人登科的盛况,并非偶然的现象,这与家族长辈含辛茹苦的科举教育显然是不可分离的。如果缺少了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和学习方法的科举教育,同安苏氏家族是很难在宋代的科举浪潮中,成为绚丽而耀眼的进士世家,也不可能在仕途中有辉煌的成绩。当然并非所有受到家族教育的苏氏成员,都有幸登科,甚至有放弃科考者,如苏绎就是其中一个。
在橡胶粉掺量比例10%以内时,抗压强度离散性有所提高,而后基本保持稳定。这可能是由于橡胶粉的掺入增加基体本身的内部缺陷且减弱了水泥浆与骨料接触带来的粘结。掺量不超过10%时复合材料的抗压强度能达到40MPa,满足一般工程上的要求。
二、家族文学、科技教育与文学、天文历法学兼举之家学
宋代同安苏氏家族中出现了多位以博学著称者,诸如苏绅、苏颂、苏绎。苏颂的博学尤其引人注意。苏颂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举凡地理学、药物学、化学、矿物学、生物学、水利学、天文历法学、文学、民俗学、历史文献学等,皆创获颇多。同安苏氏家族虽然出现了苏颂这样的博学之士,但并非每个家族成员都能如他一样,在以上所列举的诸多学科中皆能有所成就。能够代表同安苏氏家族家学的,应当属于文学和天文历法学。
文学之所以成为宋代同安苏氏家学中的一部分,一方面离不开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男性成员所做的文学教育 (在家族科举教育中已谈到)。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为了写作能力等目的,对女性成员所做的文学教育 (女性不参与科举考试)。
同安苏氏家族中出现了数位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擅长翰墨的女作家。苏颂曾记载其长妹年少时就能诵章句和承礼义之训[1](P951),早期的教育为其日后诗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次中之妻为苏颂之妹,亦以能文著称。苏颂之妹中最擅长翰墨的,当属延安夫人,现存四首词,分别为 《临江仙·立春寄季顺妹》《更漏子·寄季玉妹》《踏莎行·寄姐妹》和《鹊桥仙·寄季顺妹》,为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清代朱彝尊《词综》收录。这四首词的艺术成就颇高,我们从词题目中还可以得知这样的信息:延安夫人尚有季顺、季玉等姐妹也是精通词作的,否则延安夫人将词寄予诸位姐妹,有如对牛弹琴。在中国古代,女子一般不入学堂读书和应举,她们的诗文创作能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文学教育,同安苏氏家族中出现了数位能诗擅文的女性,这跟苏绅的家族文学教育有较大的关系。
如果说,家族文学教育为同安苏氏家族的文学成为家学提供了可能的话,那么作为家族教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家族科技教育,则为天文历法学成为苏氏家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宋代同安苏氏家族中的苏绅、苏绎、苏颂,是精通天文历法学的三位博学之士。
上文曾引用苏绅在担任扬州通判时,曾让时为十六岁的苏颂作《夏正建寅赋》,苏绅称赏苏颂之后当以博学知名。苏颂在十六岁时,就能作出令苏绅大为赞叹的天文历法之文,一方面说明了苏颂对天文历法知识的涉猎颇多,且善于运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苏绅精通天文历法学。苏颂还作有《斗为天之喉舌赋》《历者天地之大纪赋》等有关天文历法学的作品,为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盛度称赏。如果说,以上三篇赋作可代表苏颂天文历法学成就的早期之作的话,那么举世闻名的《新仪象法要》则是他天文历法学成就的成熟之作,“正是水运仪象台与 《新仪象法要》,为苏颂争得了五项世界第一”[2](P73)。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认为苏颂 “精通天文学技术和历法科学”“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3](P158)。苏颂的天文历法学研究,由于不得不依附于政治,所以出现了一些错误[6](P110),但本着热爱科学和重视科学规律的精神,苏颂并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使天文历法学研究停滞不前。苏颂在天文历法学上的成就,“反映了我国宋代对天文观测、天象演示、报时等方面的先进科学水平,对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4](P68)。 所论颇为中肯。
苏颂的叔父苏绎早期致力于科举考试,后来由于手臂出现毛病无法应举,遂断绝科举道路。此后,苏绎“专精文史、阴阳、星历、占筮、术数,百家之言,靡不精造。喜推考人生年月日时,以五行星数参验休咎,合若符要。”[1](P946)专心于研究天文历法学,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虽然在宋代放宽了人才选拔的门槛,“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都可‘自求’、‘他荐’,参加考试,成绩合格,便可在司天监求学、任职”[5](P172),但苏绎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并非为了参加考试,他所取得的成绩与其长期对天文历法学的爱好和精研,是分不开的。苏颂从小与苏绎一起学习,受苏绎科技教育的影响不小,所谓“宜乎为宗族之矜式而士大夫所以推挹也”[1](P949)就是很好的证明,以苏绎淡泊名利而学通精微的人格为宗族学习的榜样和推崇的对象。
在苏绅、苏绎的影响下,苏颂也十分重视对子孙的科技教育。苏象先在《魏公谭训》卷三中,回忆苏颂 “仰瞻星宿躔度,常于小子首背上提之,使知星命。谓子孙曰:‘悬象昭然如此,汝不虔奉,乃欲求之杳冥乎?’”[1](P1138)苏颂经常利用月朗星空,为子孙讲解天文历法知识,使他们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星象,这正是苏颂的有意为之。这从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同安苏氏家族的天文历法学教育,跟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不无关系。
如果说,文学是同安苏氏家族人文社科领域的骄傲的话,那么天文历法学则是其自然科学领域的自豪。作为同安苏氏家族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和天文历法学兼举的特点是其区别于宋代其他家族的一个体现,而两者的形成与家族文学和科技教育不可分离。
三、家族道德教育与忠孝兼备之家风
同安苏氏家族自入宋以来至苏颂时,历经七世,士大夫以其为名门望族。对此,苏颂常常告诫子孙应当谨守家法。[1](P1129)在苏颂看来,构成宋代同安苏氏家族家风的“忠、孝、文、行”四者中,忠孝需要特别重视,它们是宋代同安苏氏家族的典型家风。
明代刘定之指出,君子至少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即“言有章也,行有则也,孝于家也,忠于国也”,而且“子官继父非孝也,德业足显扬斯谓之孝,相位承主非忠也,进退关盛衰斯谓之忠”[7](P2)。在刘定之看来,苏颂是兼备忠、孝、言、行四者的君子。所谓“进退关盛衰斯谓之忠”,可以理解成为政期间能够安邦匡朝,忠君爱民,但又不仅仅是一般的忠君爱民,戴海东在《苏颂的道德风尚刍议》中指出苏颂的“忠君爱民不是绝对的‘惟君命是从’,而是要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疾苦与承受能力”[6](P159)。苏颂能够从大局入手,而不是“愚忠”,他“从国家的利益考虑,从百姓的生活考虑,对君王不盲从,敢于凭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8](P55)。他坚守法度,以法治国,反对神宗任意升迁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五次上书,而遭受神宗的贬谪。苏绅的《以灾异言政事疏》《经制安化叛蛮奏》《陈便宜八事疏》《论西北兵事疏》《久旱言政事疏》等,对关乎国家盛衰的内忧外患,皆能够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提出宝贵的建议。苏缄因为在知邕州时与蛮贼作战,守城失败,为了不动摇军心,而手刃家中妻子男女孙婢妾三十六人,后自刎而享誉古今,神宗为其壮举哀悼,并赐予“忠义”之名,以激励世人。他的行为被记载于《宋史·苏缄传》中。苏绅、苏缄、苏颂并称“芦山三苏”,我们或许可以以他们在忠君爱民上的举措作为一个重要的凭证。
“芦山三苏”的忠君爱民,离不开苏氏的道德教育。以上所引《魏公谭训》卷二有关苏氏家族的“忠孝”家风到苏颂时已经七世传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同安苏氏在道德教育上的成功之处。当我们对苏缄为何要以手刃家中妻子男女孙婢妾三十六人,来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往往会将其归纳为内外因素。这内外因素中的家族道德教育是特别需要提及的。苏缄所受到的家族道德教育,来自于家族先辈。并且他的忠义之举,也深刻地影响着苏颂,起着无形的、深入人心的教育功能。当苏颂追忆苏缄的伟大事迹时,曾在宋神宗赐予苏缄以“忠义”殊荣之后,做了说明。《魏公谭训》卷六记载苏颂之弟在苏绅的墓地上,所写的诗句 “近年忠义心如铁,不负平生教育恩”[1](P1161),体现的正是苏绅的忠义教育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而苏颂为苏象先等子孙讲述苏缄的壮举,以及其弟受苏绅的感染,显然也是为了让他们知晓忠义的重要性,进而多行忠义之事。
刘定之对何为“孝”也有独到的见解。[7](P2)在刘定之看来,苏颂之所以为孝,在于他能够显扬苏绅,如同宗的苏颋、苏轼在德业上显扬苏瓌、苏洵一样。客观地说,苏颂在功业、道德、学问等方面,都比苏绅更胜一筹,刘定之以此称之为孝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把刘定之的标准,用于衡量宋代同安苏氏家族的话,则能够进入孝范畴的,恐怕非苏颂、苏绅莫属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9](P3295)我们认为刘定之所言之孝,当为孝之大者。有孝之大者,亦有孝之小者。宋代同安苏氏家族家风之孝,更多的是孝之小者,即:父母在世时,尽职赡养;父母过世时,则尽丧礼。
五代末任漳州刺史的苏光诲,即以至孝著称。《魏公谭训》卷二记载苏光诲为使祖母、母亲享受快乐,嘘寒问暖,事必躬亲,寝食难安,可谓用心良苦,为此也受到了邻郡的追慕。[1](P1128)苏佑图秉承其父苏光诲的忠孝之风,平生也尽心孝养其母。入宋之后的同安苏氏家族将苏光诲、苏佑图的孝养之风,发扬光大,并成为他们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苏绅颇有苏光诲的至孝品格。他的母亲代国夫人张氏为泉州一带的名门望族,年老之后,喜欢乡谈。《魏公谭训》卷二记载,苏绅为了让张夫人安享晚年,告诫子孙仿效南音以博得张夫人快乐。[1](P1130)这对培养苏颂的孝养品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苏绅多次放弃了御史中丞的官职。当时的石介、曾巩屡次劝解,但因父亲苏仲昌年老多病之故,均被苏绅委婉拒绝。[1](P1160)
在先辈的耳濡目染之下,苏颂也颇有至孝品格。《魏公谭训》卷三记载,苏颂在科考来临之际,本该专心读书,然而为了解决父亲的难题,却不辞劳苦地奔波于两地之间。[1](P1139)母亲陈夫人去世之后,苏颂尽按丧礼办理。苏颂的门生陆佃有挽诗云:“贰卿头已白,儿慕不胜悲。”[1](P1131)可见苏颂在此期间的心情极为悲伤。连宋神宗都为之心疼,送礼物慰问[1](P1133),并命令州县认真筹办丧事。
苏颂也常常教育子孙应当形成孝养品格。苏颂告诫子孙:“勿远亲庭而淹泊妻室也。”[1](P1162)在苏颂看来,父母比妻子更为重要,父母不可远离,而当亲自照顾,方可尽孝养之礼。苏颂也常引孝养之例以教导子孙。《魏公谭训》卷四记载,王文考承颜顺色,为其父作《鲁灵光殿赋》之事[1](P1145),向子弟说明承颜顺色是孝养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安苏氏家族自入宋以来,秉承忠孝家风而在士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苏颂采用多种方式,向子孙讲述先辈的忠孝之行,并践行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设想,在苏绅、苏颂等人的教育下,宋代同安苏氏家族的忠孝家风不仅仅被七世秉承,而且将跨越时空,得到一代代的传播和发扬。
对于任何一个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原因,往往可以从内外因素加以考察。内外因素如何?或许又可以粗略概括为社会时代环境、周围环境、家族环境三个成分。为了便于区分,不妨将社会时代环境称为“大环境”,将家族环境称为“小环境”,那么周围环境则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中环境”。这三个环境,包含自然、人文、经济等人文生态因素,也涉及深厚的家学渊源、文化积淀等家族文化建设因素[10](P89),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也离不开以上三种环境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小环境”在“大环境”、“中环境”的作用下,具有自身的特点。进而言之,在社会时代环境、周围环境的作用下,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教育最终具备了自身特色。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家族教育,即家族科举教育、文学教育、科技教育、道德教育的作用下,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并与其他家族文化传统有所区别。以上是有关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论述,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宋]苏颂.苏魏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曾纪鑫.科技宰相苏颂[J].书屋,2013(11).
[3]颜中其,管成学.中国宋代科学家苏颂[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4]周日升.苏颂与北宋科学[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6).
[5]胡静宜.略论宋代天文学人才的培养与任用[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2).
[6]杨效雷.《新仪象法要》再研究[C]//周济,管成学.苏颂研究论文新编.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
[7][明]刘定之.重建苏丞相祠堂碑[C]//鲠夫.正简流风.同安:同安县纪念苏颂筹备会,1988.
[8]林爱枝.官员苏颂[J].文史纵横,2011(11).
[9][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9.
[10]金文凯.清代海宁查氏家族的文化特质及成因——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责任编辑:刘建朝)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Cultural Tradition of Sushi clan in Tong'an County of Fujian in Song Dynasty
LIN Yang-hua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China)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are ten people for five generations who have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Sushi clan in Tong'an County is not accidental.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strict and supportive imperial education,which Sushi clan attach importance great importance to provide a good imperial examination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method.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amily education,literature and astronomy calendar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at Sushi clan pay importance to foster literary writing ability of literature education,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ardently love to science.Moral education of discipline and stability of country,loyalty to country,cherishing people,supporting parents and observing mourning for parents plays important role to the formation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of family trait.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 of Sushi clan in Tong'an County can not separated from family education,which is a factor can not be ignored.
Song dynasty;Tong'an County of Fujian;Sushi clan;family education;family cultural tradition
K244.07
A
1673-4343(2014)03-0034-06
2014-02-11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C111)
林阳华,男,福建漳州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福建区域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