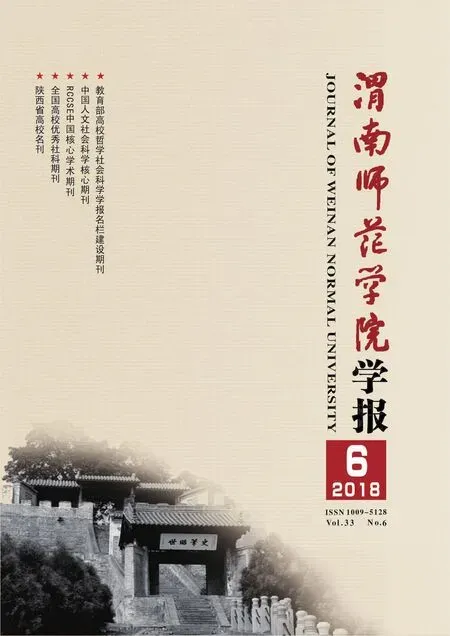“文气”说的“一体三相”研究
马 也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文气”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便是对“文气”的解读。夏静在《文气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中特别提出:“目前学界流行的看法,认为就作者方面而言,指他的气质、个性、语气;就作品方面而言,指作品的风格。论气质、才性者,如陈钟凡、朱东润、方孝岳等先生;论才气、语气者,如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论才气、风格者,如刘大杰等先生。这样的理解就相当简单化、狭义化了。”[1]这与侯文宜《文气说辨——从郭绍虞〈文气的辨析〉的局限说起》一文中对郭绍虞《文气的辨析》及相关“文气”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是一致的,两者可作参证。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两位学者的看法,即不能将“文气”仅仅等同于“才气”、行文的气势等等,我们要在“个性说”“风格说”等种种遮蔽“文气”的迷雾中,看到更广阔的哲学美学内涵,从而一改“焦点式”的研究思路,试图从多条理路上打开“文气”的生命空间。由此,笔者梳理了学界目前出现的两大类研究思路,并将跟随夏静的脚步做以尝试,采用“体用”的视角,对“文气”说的内涵做出“一体三相”的解读。
一、学界目前对“文气”的解读
学界对“文气”的解读,笔者经过分类整理后认为可大致分为两类,即以郭绍虞先生的研究为代表的“焦点式”和与结合传统哲学思想的“综合式”理路。两大类之下又有众多小类,笔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划分在层出不穷的研究面前也许仍十分有限,但还是将以此为基础做出笔者在研究思路上的选择。
(一)以郭绍虞先生的研究为代表的“焦点式”研究理路
笔者在上文中特别提到的夏静和侯文宜的两篇论文中看到了他们对郭绍虞先生关于“文气”论所做研究的评价,认同侯文宜对于该类脱离思想史的研究所称的“焦点式”研究的说法,并看到了很多在这条理路上的追随者,现在只列举一部分有代表性的。
郭绍虞先生对“文气”的研究局限在“文本”范围之内,其于1928 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文气的辨析》,并做了“文气”的直接论述,“文气之说,不过指行文之气势言耳”。郭绍虞先生对“文气”说做了简单化处理,将“文气”主要落点在文本上,即行文文体的语气、气势特点上。侯文宜在论文中这样论述,“郭绍虞没有考虑气之生命本体特性”[2]。在与之可做相互参证的夏静的论文中,她这样说道,这种剥离的做法,充分体现了第一代研究者的研究路数,即将文论话语从整体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确立言说范围、学科边界,同时这个疆界的确立,也是受制于本人的学术兴趣、知识储备以及社会形势的需求,就郭氏本人而言,兴趣显然在传统的诗文创作价值而非我们今天的理论眼光,他写批评史的目的在于印证文学史。经过这样层层的剥离与建构,此后的研究大都从既有的文学概论结论出发,缺乏学科构成方式和运作模式上的反思,从而导致此一领域的研究方式贫乏,研究氛围极为沉闷。[2]
在笔者看来,这条理路的追随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将“文气”主要视作美学范畴,另一方面则如郭绍虞先生将考察的视角不同程度地聚焦向了“文本”“作者”等维度。一方面,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文气”做了解读,将“文气”看作美学概念。如毛慧玉和白少玉的《古代散文理论中“文气”说的风格美指向》中这样论述,“文气这一范畴本身就指向阳刚美的境界”,“论古代散文风格,突出推崇阳刚之美”。体现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诸如陈果安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洪珉的《文气的实质》、白少玉的《“文气”:范畴的结构机制与内蕴》等等。另一方面,学者们做了类似于郭绍虞先生研究的“文本”或“作者”或是二者结合后的简单化处理,仅仅从文学观念的理路考察“文气”说的内涵,将“文气”局限于“文本”或“作者”等视域之内。如胡家祥的《中国古代文气论的再体认》一文,“气用于文艺活动,已失去质料的含义,其可贵之处在于兼指力与象,所以气力与气象是它的两个最基本的意涵,气力是全线贯通的,气象则专指其外在表现”。此外,还有畅广元的《文气论的当代价值》,将“文气”视作“为文之气”与“文之气”,宋扬在《辞盈乎气:修辞在文气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及意义》一文中提出,“慎辞”是文气论的基本命题,许家竹的《文气论视野中的作家生命形态》中将“作家之气”视作“文气最根本的形态”。
(二)结合传统哲学思想的“综合式”理路
如果说上述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的“焦点式”研究,所采取的原则和理论取向是“疏离气论哲学”[3]的话,那么这种结合传统哲学思想的“综合式”理路则回到了所谓的“气论宇宙观”和“生命本体论”。笔者赞同侯文宜文章中的观点:文气说的正宗发展在刘勰的《文心雕龙》。[4]这是因为,在侯文宜的视角中,刘勰的文气说包含了宇宙生命之气、作者体性之气、作品文势之气等等丰富内容。由此,在论及传统“气论”与“生命”时,他这样论述,“回到当时的哲学文化语境,不能不看到它是一个源自先秦到汉魏的元气自然论宇宙观、生命观的概念,其所含的‘天人同构’之理和生命气化的‘任气’意识是显在的。中国文气说的哲学美学蕴含和内在结构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气本源论和气化论,是涵盖了自然生命的大宇宙性、个体生命的差异性、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追求的”。此外,刘勰不仅做到了结合“生命本体”,同时对“文气”的考察是在多个维度展开的。这样一来,这种“综合式”理路在观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哲学思想的传统,对“文气”说内涵的考察便更完整丰富了。
在这条理路上做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例如,姜小青的《文气论》一文,指出“文气”的哲学基础乃古代万物之源的“气”,“文气”是“气”之生命性在文学观念中的体现。同时,对“文气”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分析,既着重于创作与本文两个层面,也顾及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气”的文学意义作了论述。万奇的《中国古代“文气论”探》,其认为“文气论”有三个组成部分:着眼于作者的“养气说”、关乎创制的“行气说”和立足文本的“神气说”。万奇在结合“气论”哲学思想的同时,对于作家、创作、文本、风貌等维度亦做了理论关照。张海青的《文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整体论》,明确了“天、人、文”三位一体的视角。陈学广的《古代文论中“文气”辨识》,其认为“文气”说以“气”论文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论述了“气”从哲学范畴到文论范畴的演变,并从创作主体、创作功能和创作风格三个方面对“文气”说进行了辨析。此外,这条理路上也有一些有代表的研究将“文气”视作特殊的美学范畴,不同于上文中提到的此类美学范畴论者,这类研究结合了“气论”传统,并且对“文气”进行了多维度考察,不仅只局限于上述论文的“风格”“修辞”等角度。例如,顾明栋的《文气论的现代诠释与美学重构》,其将“文气论”视作一个理论系统,认为“文气论”所面对的对象是“三个相互交织的空间内的创作活动及其美学原理”。李岩的《“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其认为“文气论”是中国美学理论的独特理论,在 “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这条理路上,学界考察了“气”之生命本体特性,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气”说丰富的哲学美学内涵。但是除了在结合传统哲学思想方面做得很一致之外,在“综合”眼光方面学界依旧纷繁复杂,对于“文气”说的不同面相所做的归纳也不统一。这种情形一方面与“文气说”本身的复杂性相关,一方面也与其视角有关。这条理路与笔者即将采用的“一体三相”研究视角看起来颇为相似,不仅联系到了传统气论与生命本体观,同时也在“文气”的内涵上持多元态度。但笔者的视角在此基础上仍往前迈了一步,从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视角出发,对“文气”体用义展开解读的视角,将“内在之气”与“外显之文”和“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文章气象”看作互为体用之关系。
二、以“体用”为研究“文气”的话语方法
相较于笔者上述所梳理的两大类思路,夏静在“文气”内涵上的研究思路,不仅体系完整,而且方法论也更合理,这不仅在笔者上述引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其专著《文气话语形态》中的论述则更详尽清晰。由此,笔者将跟随夏静的脚步,在方法论上采用“体用”视角去考察,在内容辨析方面也沿用其所提出的“一体三相”之说。夏静认为,从文气之体用义来看,作者之气乃是体,文本之气、文章气象乃是用,也即内在之气为体,而外显之文为用。此外,对于“文气话语结构形态”,在夏静看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气说,综合了历代以来学者关于气学思想的见解,主要呈现为“一体三相”的特征:一是先天命定之气质禀赋、后天养成之心性道德,两者融合成为作者之气,包括作者之情、性、才、胆、识、力等;一是语言法则之体势声调、字句章法,这构成文本之气,包括文本之辞、字、句、音、韵、声、调等;一是作者之气和文本之气共同熔铸的作品整体性的生命形相(气势、情韵、意境、风格等),这就构成了传统文气思想的三个面向。[5]258
在夏静的著作中,明确阐述了“体用”的特点与内涵。“体用”概括了华夏民族思考宇宙存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最能表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一个范畴,深刻体现了古代哲人的智慧,蕴含了极强的文化衍生性和解释力。体用思想的渊源在先秦,是指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体在用中,用以显体。作为观念形态的体,往往隐微难察,唯一的认知途径就是其显露之用,因此,用不仅是指体的功能或属性,而且是体自身的显现,离用也就无所谓体了。[5]61“文”与“气”之间,本身处于一种分而不分、不分而分的特殊张力之中。所谓张力,乃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平衡,两者均能单独成体,各自为用,又能合二为一,相互渗透,相互阐释,合之则为美,离之则两伤。正因为文气之间的这种特殊张力,故而在谈论此一类文论元范畴时,以体用加以言说,较之实体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两分法,更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内涵与形态,也更能以言尽意。[5]251
笔者认为,在“文气”说中有两个交互存在的话语结构,一层是“文”与“气”之体用关系,另一层是文气结构中的作者与文本、文章整体的体用关系。这两层体用关系在“文气”话语之“体用”义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且,往往在具体的批评话语中交织出现,不能将之分割来看。本文中,为了使研究更加清晰,使我们在面对“文气”话语时有更清晰的思路和判断意识,我们暂且将二者分离开来,在两个维度中探寻“文气”说的内涵。
(一)“才气为体,文辞为用”
从整体上来说,所谓的“文章”是一个整体,“文”与“气”是有机统一的,两者不偏一隅。如果“文”多而“气”少,那就是有用无体、以“文”害意,如果“气”多“文”少,那就是有体无用、“气”盛“文”不足。
其次,就体用义而言,文气源自于“气”,显之于“文”,“气”决定“文”,“气”为体,“文”为用。[5]251这一层意思,从曹丕谓“文以气为主”开始就很显明了。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6]158
从曹丕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便能得出“气”决定“文”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气之清浊”决定了“文之清浊”,另一方面,“气”为不可力强而致之物,贯通于作者之中,属于作者的先天禀赋。前者“清浊之气”乃由此作者之“气”而决定,外显于“文”时又成为文本之“气”。相对于“辞”“体”等要素,“气”才是最重要的。由此,我们会发现用传统的“体用”义来解释“文气”确实好过于当下种种“决定”之类的文辞。二者虽为“决定”关系,又为统一的整体,“体用”一词将两者关系阐释得更准确清晰。通观古代文论史,“才气为体,文辞为用”大抵是古代文论家的一致看法。如唐代刘禹锡认为,“文”与“气”乃“枝”与“干”的关系,“气为干,文为枝”。[5]252刘申叔《论文章有生死之别》中论述得更加显露:
文章有生死之别,不可不知。有活跃之气者为生,无活跃之气者为死。
盖文有劲气,犹花有条干。条干既立,则枝叶扶疏;劲气贯中,则风骨自显。如无劲气贯串全篇,则文章散漫,犹如落树之花,纵有佳句,亦不足为此篇出色也。[5]253
“无劲气”之文,“犹如落树之花”,不足为“有劲气”之文出色。虽然刘申叔没有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这样的论断,但其倾向明显见之于字里行间。“条干”与“枝叶”二者互不相离,但“枝干”的确为前提,同时“枝干”之态又见之于“枝叶”。
除了像桐城派等少数现象,“才气”与“文辞”之体用关系成为中国“文气”论的主流,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文论与文学传统,也在“东方诗话圈”中很大程度上给予古代朝鲜文人深刻的影响。在高丽诗话中,这一维度的体用关系同样外显于其批评话语的字里行间。
(二)“作者之气”为体,“文本之气”与“文章气象”为用
“文气”的两层体用关系在“文气”话语之“体用”义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气”话语中“才气”与“文辞”之体用关系呈现的是“文气”话语的总体倾向,而“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文章气象”的“体用”义则是更具体的话语结构。在这层更具体更显露的话语结构中,不仅将“才气”与“文辞”之“体用”义印证得更明显有力,同时也在更具体的视角中给予了阐释。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体性》一文中,有这样的经典论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义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7]189
在这段论述中,“才”“气”“学”“习”与“辞理”“风趣”“事义”“体式”为“体用”之关系,“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便是最好的自证。若用笔者“一体三相”的视角去解读,“辞理”“事义”“风趣”“体式”等范畴大抵归之于“文本之气”“文章气象”的维度,而“才”“气”“学”“习”则在“作者之气”的维度。刘勰论述话语中的“作者之气”维度,不仅有如曹丕所“不可强力而致”的先天之“气”,亦有后天学得之“习”,其共同构成了作家个人之“气”,并在具体创作中影响到了各个方面,而且每个人“其异如面”。因此,在文气结构中,“作者之气”“文本之气”“文章气象”虽然相互区分,并有决定于外显之关系,但又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绝对分梳。
沿着刘勰的这套“文气话语”,后代文论在这条理路上的发展蔚为壮观。就“文本之气”而言,有“辞根于气”“气形于言”“气畅辞达”“气盛言宜”“随物赋形”“气殊各异”“阴阳刚柔”诸说法;就文章气象而言,有气脉、气势、气骨、气象、气韵、风骨等,论及作品艺术生命力与整体精神风貌,构成蔚为壮观的文气话语景观。[5]301在这些具体的范畴与观点中,虽然没有具体论及作家主体,但我们仍旧能见到“作者之气”为“体”的影子。
三、“文气”话语结构的“一体三相”
夏静在《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中提到了现代史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即经典诠释中的“隧道效应”问题。[5]256这种理论认为,随着时代的不同,经典思想的要素在不同的诠释者那里,由于关注的焦点不同,会出现复杂化和简单化两种趋势,如此便形成两种“隧道历史谬误”。“气”范畴具有不同的层级意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和不同文本语境中含有参差不齐的意素结构,既有固定的物质属性的基源意义,又有后来附加的次级衍生意义。[5]279
回观“文气”说发展历程,自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后,随着文学地位的独立,文学意义上的“文气”说逐渐演变为作者之气、文本之气、文章之气三个密不可分的面向。[5]259
基于上述“隧道效应”的理论,我们今天从“三个面向”出发来阐释“文气”说的基本内涵,是综合了历代文论家的不同见解,借鉴了现代学者的不同维度的阐发而确定下来的视角。此外,具体到三个面向中所具体呈现的特征时,不同时代的文论家和学者对此的阐发也尽显不同,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有确定之义。有鉴于此,笔者在下文对不同面相所具体划分的内涵做了一定意义上的概括和取舍。因此,一定会有种种疏漏和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作者之气
“作者之气”,可以理解为创作主体以天赋的生命力为基础,加之后天的学养及心性道德所共同融合而成之气。[5]258因此,主要包括创作主体的气、志、学、情等。
1.“气”与“学”
“气”与“学”是一对对立的范畴。“气”即创作主体的先天禀赋,“不可力强而致”的先天之气。这一点,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论述为典型代表。在朝鲜高丽朝,李奎报在《白云小说》中有相关的直接论述:“气本乎天,不可学得”。[5]58这一派文论家将先天禀赋视作决定作者之气的关键因素,并且影响到了创作过程与文本风格等方方面面。“学”即后天之学养而成的心性道德及文学修养。将先天之“气”与后天之“学”结合起来看的典型代表为刘勰,他不仅吸收了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不可移”的思想,同时也在“作者之气”的维度上融入了后天之“学”。如《体性》中的“才有天资,学慎始习”[7]189便是例证。
2.“志”与“情”
“志”在我国“文气”论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范畴。这一点上,必须要提到的便是孟子论气之例。“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此“志”即心志,是一种由理智、意志、动机而构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5]268
“情”与“志”共同构成了创作主体精神力量的维度。“情”是触物之感发,相比于“志”作为稳定的意志和心理状态,其更关乎作者的生命情态。在《岁寒堂诗话》中,有这样的说法:“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在此尚且不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的“言志卫道”倾向,其在论述中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志”与“情”在“作者之气”的维度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上述“气”与“学”只是构成“作者之气”并影响作家创作的基础范畴,其决定了一个创作者的基本素质。而一个作者的“情”与“志”才是直接影响作者之创作力的重要因素,并最终影响作品形相。
(二)文本之气
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互为表里,作者之气为文本之气的决定性要素,文本之气为主体生命性情之形迹。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既不可能离开主体之形神、性情而论文气,也不可能离开文本之言辞、声调、气势而论文气。[5]333因此,在“文本之气”的维度上,“文气”便落到了具象的角度,主要包含“声气”“辞气”这两个方面。如果说辞气是偏于诉诸视觉的书面语言表达,那么,声气就是偏于诉诸听觉的口头语言表达,故而同样被古人视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有机环节。[5]313
1.辞气
辞气的含义大体包含文学作品中的言辞、文势等特征。言辞是在字句,章法等角度上来说的,而文势则包括语气、文辞风格等义。如《马氏文通》所论之“辞气”便是通过言辞声气来认知句法语义。还有像《春秋榖梁传》中便出现了“急辞”“缓辞”之分。这是从语气轻重缓急上所做出的分类。在高丽朝李奎报的《白云小说》中也有对辞气的间接论述:“故气之劣者,以雕文为工,未尝以意为先也,盖雕镂其文,丹青其句,信丽矣”。[5]58在李奎报眼中,“雕镂其文,丹青其句”而所得之“丽”气乃是“气之劣者”为之。这里能看到其对文章中语言文辞之地位的主张。
2.声气
声气与文气的关系非常紧密,声律和谐,文气便自然顺畅。故而论“文气”之中的“声气”,通常包括声律、音韵等义。在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这样的论述:“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5]307这一判断是否合适暂且不论,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声气在“文气”中的重要性。例如《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关于音律的论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如果说在声气中声律属于声音高低切响是否和谐的维度,那么音韵便是在声音切响的基础上对于“声气”音乐感与美感的追求。宗白华先生有这样的说法:“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5]313《文心雕龙·声律》:“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7]222在这一点上,高丽朝诗话中有大量的批评实践之例,例如在崔滋《补闲集》便有这样的例子:“此诗韵强,凡作者颇艰于和。观君之作辞意绝妙,虽使李杜作之,无以附加也。”[5]92
(三)文章气象
文章之气象,体现在“气”与“象”两个方面。“气”更偏向的是作家的主体精神所体现在文章中的特质,而“象”偏向于作品中“文气”所表现出的整体的一面。
1.“气”
在古代文论家眼里,作者总体性的生命特征与人生追求可以通过诗之气象直接体现出来,所谓文如其人,作家的生命气质铸造着作品的个性特质,《艺概·诗概》谓“诗无气象,则精神无所寄托矣”,两者是相互印证的关系。这便是从创作主体之精神风貌为出发点所体现出的作品生命形态。
2.“象”
“象”源于先民的“尚象”意识,作为构建古代思想系统的文化符号,成为我国古代一套传统的思维与言说方式。“象”综合融合了主观与具象因素,在文学中的“文气”领域中,其与“意境”“味”“韵”等显现整体风貌的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意蕴丰富,层次复杂。它统摄了风格审美、艺术境界乃至文学的总体精神。
“气”与“象”是相互对待的关系。[5]344两者从不同角度共同构筑成了文章的整体风貌,并对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算是做了总体的把握。例如《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这样评价李白:“太白纯以气象胜。”高丽朝崔滋《补闲集》中亦能看到这样的论述之例:“杜子美诗虽五字中,尚有气吞象外。李春卿走笔长篇,亦象外得知,是谓逸气。”[5]99“象外之气”被崔滋称之为“逸气”,这一文论范畴作为品评文章整体风貌的视角,对“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兼有把握,是与二者共同紧密相连的作品生命形态。
[1] 夏静.文气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文艺理论研究,2009(4):124-130.
[2] 侯文宜.文气说辨——从郭绍虞《文气的辨析》的局限说起[J].文学评论,2010(5):114-117.
[3] 侯文宜.从批评话语到理论研究:20世纪文气论之变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2-37.
[4] 蔡镇楚.诗话之学与古代文论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32-37.
[5] 夏静.文气话语形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 郭绍虞.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陈果安.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J].江汉论坛,1984(4):54-57.
[9] 洪珉.文气的实质[J].殷都学刊,1985(2):29-35.
[10] 白少玉.“文气”:范畴的结构机制与内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5):31-38.
[11] 胡家祥.中国古代文气论的再体认[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61-166.
[12] 畅广元.文气论的当代价值[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59-69.
[13] 许家竹.文气论视野中的作家生命形态[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62-66.
[14] 万奇.中国古代“文气论”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32-40.
[15] 张海青.文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整体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10-17.
[16] 陈学广.古代文论中“文气说”辨识[J].扬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21-26.
[17] 顾明栋.文气论的现代诠释与美学重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74-85.
[18] 李岩.“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J].北方论丛,2015(4):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