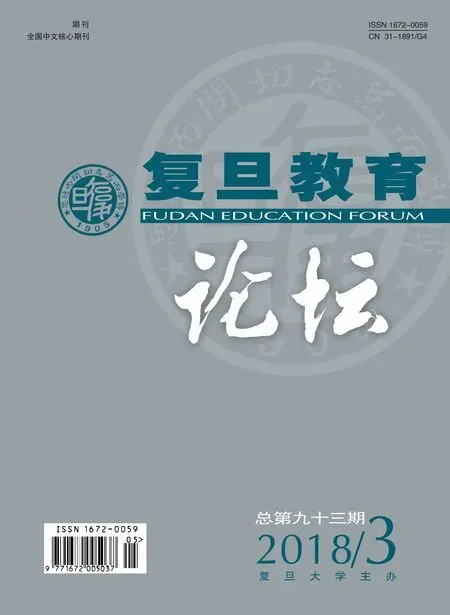教育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古典
吴元发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7)
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古典”一词,英文为“classics”。据朱光潜先生考证,这个词源于拉丁文“classici”,最初是指“第一等的有资产的公民”,后来引申为“有价值有地位的作者”[1]391。近代大学产生以后,像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古典研究,由专指研究古希腊拉丁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发展为专指研究模范作品。若古典专指第一流的模范作品,则当然不限于古希腊,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优秀作品产生。此时,“古典”的含义实指“经典”。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代表了智慧的高峰,其作品对人性思考没有任何时代能够超越。若认同这个假设,则可以把西方学术中所说的“古典”界定为,专指古希腊时期的优秀作品。进而可以说,“古典”是指那些研究人的本质并主张灵魂净化[2],处于人类“轴心”时代的“第一流的作家或作品”,而且它“不分古今中外”[1]392。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古典研究受到诸多批评,日益被边缘化。在当今科技力量进一步被自我证成的时代,古典研究更加遭受不公正待遇,遭遇各种先入为主式的冷嘲热讽。然而,古典恰恰是现代的根基。教育哲学只有通过研究古典,还原古典的现代意义,现代人才能深层次地理解现代,才能摆脱日趋低下、狭隘的眼界,从而获得和接续古典所传达的高贵德性。
一、“为什么要研究古典”何以成了问题
“知今”须“鉴古”。“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精神上的先辈一无所知,就不能被视为受过教育的人。”[3]这些道理似乎很简单,而“教育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古典”,又何以成了一个问题?
(一)从“崇古”到“反古”:教育的古今之变
古希腊衰亡之后,罗马人认为古希腊的智慧高峰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是最好的办法。这种研究古典的节制而审慎的态度一直保持到中世纪,最终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复兴”其实就是指古典研究的重生。正是这种向古人学习、向古典传统要思路的教育传承,使得高贵的希腊文明教化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近代自然科学和工商业产生以后,这种崇古观念被打破。与此观念相匹配的现代大学产生后,教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古今之变。教育开始更多地被理解为提供基本生存技能的国民教育。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认为,关于人类精神性探讨的古典学问,“不过是诡辩,除不正确的、暧昧的日常说法外,没有其他根据”,而且这些古典教育只是花架子,“不能对有常识的人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根本无法使人带来金钱上的利益[4]337。因此,斯密认为,把这种让人“得知极少”“只能产出狡智和诡辩”的古典学问与让人“得知极多”“有用”的物理学放在对等的位置,在重视程度上是颠倒的[4]338。因此,他认为应该由“未开化社会”的古典教育,转变为“文明社会”的现代教育。教育上出现了从“信古”“崇古”到“疑古”“反古”的古今之变。
(二)“德性”与“欲望”:教育的古今之争
斯密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新观念的代表。面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商业化时代的来临,古典教育所追寻的德性教养因显得无用而遭到贬低,或被认为是少数人的学习内容。这些古典教育所追寻的德性,在文明的商业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利己心”这个追求欲望的商业手段来实现。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人们在满足欲望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5]。换言之,古典教育努力想让人性通过攀爬“理性的阶梯”才能达致的德性与高贵,在现代人那里通过日常经济行为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在这样的新旧观念的纠缠与激荡中,欧洲产生了一场关于教育内容与目标的争论,即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爆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古今之争”,产生了“崇古派”和“崇今派”[6]。在法国巴黎,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1688年发表《古人与今人对比》,首先开始向古典宣战。在英国伦敦,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在1690年发表了《论古今学问》,对崇今派进行反击。坦普尔的秘书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后来继续为抵抗崇今派而战,先后发表了《木桶的故事》《书籍之战》等寓言体作品。这场运动延续到19世纪的英国大学,其争论的主要焦点是: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到底何者更为重要,更为时代所需[7]。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在中西的教育古今之争中,崇今派占了上风。
然而,这种评判本身是不公正的,因为作为评判者的现代人本身浸淫于现代科学理性之中。对于胸无大志、习惯了张扬欲望和权利的现代人来说,已经部分丧失了对古典理性的评判能力。因此说古今之争“陷入了某种僵局”[8],也许更加符合事实。古典节制人的欲望,而现代挑拨人的欲望,古今之争背后的实质是德性与欲望之争。也许欲望是“对我们而言第一的事情(what is first for us)”,但是德性却是“依本性而言第一的事件(what is first by nature)”[9]。古典研究的目的在于关切文明传统,守护传统教育的德性品质。只有通过古典研究,进而反思现代学术与教育现状的偏颇,才能意识到古典对于现代人意味着什么。研究古典才能带着古典的乡愁寻找教育的精神故乡,才能引领教育走向高贵与美好。
二、尊重教育研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脉络
教育哲学研究古典,源于教育哲学的文化“根性”。它要求现代人在时代“迷雾”和人的精神歧路中时刻做好正本清源工作。教育哲学研究要尊重基本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脉络。
(一)阅读经典即学术训练
教育哲学有别于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它关涉的是教育的根本价值和根本目的的探究[10]。教育哲学的探究力主要来自前人,包括古人的理性或经验性的思考。经典作品之中的古人思考成果是经过深思熟虑并被人类历史担保过的。因此,现代人对教育方向性的思考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阅读古典来获取。
1.经典即教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涵养学生的心性,维护其心灵秩序,让学生明白何为“人之为人”。而要做到这点,必然要有正义而正派的教师。然而这种具有伟大心灵的教师,在现实当中即使不能说不存在,至少也是很难找,而且常人很难辨别真伪[11]。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告诫说,人的灵魂不能轻易地托付给别人[12]。所以在当下最好的做法是去阅读历经岁月沧桑而不朽的伟大古典著作,以经典为师。这些经典著作之中内嵌着伟大思想。只有这些伟大的经典才能承担培育和照料人的心灵(cultivate human mind)的重担[11]。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靠的教师,循其路径而行可助现代人抵抗学术的庸俗化。经典给人以厚重之遗风而免于落入流俗之言。古典作品遗留的教诲不可轻易抛弃,对古典教育要有基本的敬畏,有耐心地倾听伟大心灵写下的伟大之书的伟大教诲。若抛弃古人的思想则会丧失眼界的高度,使现代人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深度与严肃性。
2.阅读即训练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中“永恒问题”的探究。只有透过历史上最严肃的古典作品,现代教育的关切才可以被理解。古典作品中的那些经典,并非只是处理它们那个时代中的特殊问题,而是指向人类教育的永恒问题。作为教育研究者,不能忽略古人的思考而闭门造车。教育问题可以来自当下实践,然而实际上诸多问题更早地存在于古典作品之中。这些教育问题已经得到古人审慎、系统而深刻地思考并固化于文字之中。这些思考已经超越了其时代性和历史特殊性,而成为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根本问题。因此,阅读古典就是一种学术训练。阅读即训练,阅读即研究。通过这种训练可以获得研究教育的学术脉络、思想传统和理解教育的基本素养。研究者最忌讳的是:以为今人比古人聪明。这是一种在人文性学术上缺乏教养和无知的表现。
(二)探寻教育问题的原初
教育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教育根本上是要处理人的内在灵魂秩序,其根本问题是“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古典作品中有非常深入的探讨,并且相较于现代而言是相对洁净的原初理解。
1.朝向古典本身
自然科学不关心古典,是因为它着眼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正如自然科学的每项进步,并不一定要回顾之前的每一次失败。然而教育哲学研究,不关心古典,则颇有些令人费解。国内教育学术界,近两年来教育实证主义研究风气强势崛起。这种潮流实际上是延续着近代西方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延续。作为研究方法之一种,无可厚非,但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显然是夸大其词[13]。数据确实可以揭露或展现活生生的现实,但它并不能告诉人类的未来在哪里。何为人类的美好生活作为一个核心话题存在于古典作品之中。遗弃古典,就是只顾眼前的一抹功利而放弃长远的未来。教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教育学而言,毕竟不能说坐着高铁的现代人,比坐着牛车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先进。现代学术研究往往存在“修辞学的转向”[14],不断地制造与滥用各种新概念,并不断地挑起争论,然而实际上要么只是用着现代性术语谈论着古老的论题,要么是由于概念的理解不尊重思想传统与学术脉络而导致虚假争论。由此,教育研究从内容上,应超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狭隘功用视野,而应审慎冷静地朝向古典本身。对中西教育的古典,应辨其源委,挹其旨趣。
2.超越新老“陈词滥调”
朝向古典,向古人要“经验”,则会避免诸多的新式和老式的“陈词滥调”。首先,警惕现代各种昙花一现式的“主义”。现代学术工业表面兴盛,实质上往往是虚假繁荣。“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15]研究者往往身陷各种“主义”与只有新形式而没有新内容的泡沫化概念之中而不能自醒。然而,当以古典为师,则可以从根本上质疑和摆脱现代各种盲目的“主义”。如果研究者不能经由古典而把握真正的教育根本性问题,则不能清醒地坚守研究志向,不能使自己避免陷入各种主义的追逐之中。其次,应尽量避免教科书式的陈词滥调。教科书列出的条条框框可以给初学者或普通大众了解思想地图的一个梗概。然而作为研究者,如果不能直接阅读古典著作,或没有直接研讨古典原著的经验,则很难冷静地超脱世俗的追逐。当时髦的研究成为主导,古典所确立的教育志向却被遮蔽,被这种教育所化之人也就会成为心灵枯竭之人。此时正需要通过古典作品中的经典来实现价值逆转,即把当下时髦而流行的“噪音”调成背景轻音[16]。
三、探寻古典传统的教育“大问题”
深入思考现代教育问题,必先深入理解古典教育传统。而要理解古典教育传统,就必须从教育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对古典传统的理解也不停留于表面,而有必要领悟其背后的基本问题。教育哲学研究首先要抵制各种功利性的诱惑,坚守教育中最为根本的要义,最终期待通过教育教化出不被时代末流所误的、能在古今之间平衡的“明白人”。
(一)现代性教育的“器”象
现代性教育始终着重在“器物”的层面上思考问题,从而略显“小器”。它根本上基于一种技术崇拜,即往往把复杂的教育问题简化成技术问题。人正是在这种技术的崇拜与宰制中,丧失了对诸如“人应该如何生活”等人的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问题的追问能力。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景象掩盖了人类教育的根本危机与堕落。
1.教育的技术化
现代性教育突显其工具性价值。工具理性最终又要依靠科学-技术来支撑。由此,教育问题在现代性的学术视野中被简化为技术问题。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人在这种技术“座架”中,“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17]。换言之,人在技术崇拜中,获得丰富的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使技术成为没有主体的主体性,从而陷入被技术操控的命运。在此种际遇中,最终必然导致人对精神的贬低与曲解:往往把精神曲解为“智能”,即工具性的算计理性;或者把精神当作获取其他事物的工具和手段。科学技术也许是追求工具理性的最佳方式,却不是追求价值理性的最好途径。科学主义如果只是停留于技术崇拜而没有价值引导,从而导致目的迷失,那它“也不过是一种泥足巨人”[18]313。教育如果只基于工具主义理性,从而导致人的精神萎靡而不返回到德性生活的精神教化上,现代人也只是个“瞎了眼的巨人”[18]311。
2.教育学的专业切割
教育哲学探寻美好生活与好的教育[19],着眼于学生灵魂的整全性发展。由此,教育学研究需要有更为广阔的眼界和从容的心态,有必要摘下现代“学科之眼”。只有突破学科门户之见,才可能整体性地把握教育实践,进而把握教育的“大问题”。然而产生于近代的学科分化,使得学术繁荣的同时,把学术研究和真理碎片化了。其一,现代人津津乐道于固守“瞎子摸象”式的片面学术之中。它表面上是切割学科,实质上是切割真理与真实。专业化包括两种:学科分化式切割与教育学内部专业的切割。这两种切割都限制着现代人对教育与人性作全局式的理解[20]。其二,教育学以“专业”的名义拒绝整全宏大的思想探索,使研究者心胸日益狭隘封闭。这种切割与拒绝的背后,实质上是放弃了对教育根本问题的探寻,转而专注于教育的社会功利或个人欲望满足。
(二)古典传统的“大问题”意识
现代性教育基于对科学与技术的自信,信心满满地急于要为现代人的幸福效力。其途径是通过为现代人提供技术与实利性知识,以获取有利于现实生活的外在条件。而古典教育传统指向一种灵魂的教化,它旨在使人的灵魂向上。
1.探寻超个人超时代的“大问题”
中西古典传统的教育,主张有国家情怀与天下关怀精神。古典旨在思考教育大问题和关切教育根本性问题,诸如“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等。它的根本着眼点不是对时代的琐碎的特殊问题的回应。古代人胸怀追寻德性之大志,从而不会被一些耀眼的半途风景迷误了双眼。而现代生活使人善于一些琐屑思考,并“有着过分蔓延的危险,它使那些让灵魂高度紧张的深刻问题变得平淡无奇”[21]288-289。然而最致命的是,以科学理性为代表的现代理性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何为美好生活”,唯一要做的是选择达到美好生活的手段和途径。换言之,现代人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作一个有确定答案的事件来办。最终把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定位于技术手段,从而最终导致欲望与技术的互为对象化。欲望化的“好生活”与技术相互证成,成为手拉着手的一对孪生兄弟。它最终导致两个根本性的悖论:我们追求美好生活,却生活得并不美好;我们追求幸福,却并不幸福。教育哲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出于有关个人生活理想的关怀或个人命运的救赎,那么又何以保证对所有人有效?因此,唯有着眼于“大问题”,才可能抓住教育的根本性问题。
2.永葆苦恼意识与苦难精神
古典教育“大问题意识”之大,在于其始终盯着完美目标,最终使人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产生各种焦灼的苦恼感与苦难感。首先,古典教育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有一种质疑并不断追问的精神。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些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教育哲学就是要不断去探寻这些问题。其次,古典教育传统往往关注的是对永恒真理的探求和对自己灵魂的照看。它试图表明人类要想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成为好人需要“机运”[22]35。所以人需要不断地对恶保持警惕的态度。亚里士多德说,“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事”[23]。而现代人认为只要科技足够发达,人类完全可能达至一个完美的均质社会。因此现代人不试图区分善恶与好坏[22]33。再次,古典教育中把政治或政制问题提升为教育的背景或底色来理解。教育永远绕不开政制问题。最佳政制与好的教育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现实的教育永远存在一种提升的空间。然而现代教育研究者,鼓吹和放大客观性、无价值判断的“大数据”与实证研究的有效性,从而绕开或隐匿了政制。现代性教育最终使人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与“快乐主义”。
四、回到“教育”本身
身陷现代性迷雾中的教育,已经被各种强力逻辑所裹挟从而遮蔽了自身独特的逻辑。在这种际遇中,应该回到“教育”本身来看待教育。其基本途径是回到前现代、前科学化时代对教育的“原初”理解,以返回到其单纯化的源头状态以观其妙。
(一)现代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恢复传统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道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似乎一直在试图摧毁传统,仿佛传统是现代性的死敌。然而古典传统恰恰可以成为现代性教育的解毒剂、平衡剂或润滑剂。中国当下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恢复优秀古典传统。
1.现代性教育的演绎化
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口号响彻全球,进而在教育理念中,诸如教育自由、教育民主与教育平等提法则简单地、轻易地进入教育学的话语之中。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陷入一种机械而单薄化地演绎“怪圈”之中。比如功利主义认为个人生活的整体功利的计算(比如人被打时会抱住头部,因为头部比四肢对于生命更重要)可以运用于社会群体之中。在中西古典传统教育之中,并不存在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它们更强调并张扬权威的存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忧心忡忡地说:“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正处于一个不知权威为何物的时代。”[24]权威源于人的优秀与卓越,强调的是真理的内在强力,因此在教育上强调德性教化。否定教育中的权威无异于取消教育。甚至有人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亲子之间也应该像现代政治一样保持民主平等协商原则。现代性教育成为现代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思潮与教条的一个演绎场[25],最终使得现代人所理解的教育只是现代观念推理和简单演绎中的教育想象而失真,最终丧失批判与反思现实的能力。
2.现代性教育的“精神分裂症”
现代性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现代性思潮激起的“浪花”。这种受制于时代羁绊的教育样态,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其一,现代教育研究者把教育学研究当作一门职业来对待,把教育学知识完全客观化与对象化。研究者可就教育学知识在理论上达成共识,但却不去践行甚至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其二,与上述情形相对应,受教育者往往把知识当作实利、实用的技术性知识来学习。特别是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本逻辑占据并主导整个社会价值,知识与行动出现严重分裂,人们完全丧失了庄子“道行之而成”[26]的古典教诲。现代性教育的精神分裂症不是现代性不足或迷失的结果,而恰恰是在现代性规划之中。现代性教育化育出来的人,最终必定是“没有精神或远见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11]。因此,要缓解与治愈这种分裂症需寻找“旁观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教育。
(二)回到教育的“原初”理解
现代教育哲学的各种理论、主义更迭迅猛,很容易使人迷失于纷繁错杂的文化森林中,从而使人遗忘了教育“原初”的单纯与高贵。教育哲学研究古典,并非拄笏看山,而是着意于对“真善美”的关怀。因此,教育哲学有必要在文化的源头处获得滋养,最终有望使现代人逃离物质厚实却又精神空虚的生活,从而严肃地对待“美好生活”。
1.教育即德性教育
教育哲学研究,应该最终落实并服务于一种培养或成就人的技艺中来。其最终指向的目标是成为好人或好公民的技艺。一方面,教育是一种整全性的活动。具体而言,它关涉三个整全:整全的社会、整全的教育与整全的人。古典传统中,教育指向的是从人的整体性出发关照人的整全性的“好”的生活方式,是从更大的整体上来理解教育。基于这种整全的理解,教育就不会被当作一种外在实利技术性的活动,而强调人的内在灵魂和谐。另一方面,教育的根本主题是“好”的生活方式的探讨与人的内在德性的涵养[27]。教育有外在与内在功用,但最根本的在于净化人的内在灵魂,因为“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21]1。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的人的区别被表述为是否实现“灵魂转向”。《大学》中强调知识要转化为对人的内心的充实与更新,即正心、诚意、修身。简言之,教育哲学通过研究古典,可以使现代人转向追问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成为有德性、高贵之人,从而“严肃”地对待更高的生活。
2.古今教育之平衡
教育哲学研究古典并不是出于思古之幽情,而在于着眼于当下问题的解决。首先,古典会以“不合时宜”的方式作用于当下。教育哲学的古典视野,往往并非直接以肯定性角度作用于当下,而往往是以相反的方式。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它称之为“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不合时宜是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其意在作用于更为长远的未来[28]。其次,西方古典为中国教育学研究提供一种典范。中国教育学不可能直接照搬西方。中西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西方古典的研究对中国只是照亮一种可能性,提供一种参考。再次,中国古典传统对现代中国教育也不是机械地回归。通过研究古典而超脱教育的现代性偏见以求对教育的重新理解,使国人对中国教育传统重拾普遍的尊重。概言之,当下中国教育必须直面现代性的状况,采现代实用取向的同时,兼取古典德性涵养,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古今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与平衡。通过研究古典,展现现代性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最终让人重新思考:在历史主义强调的“偶在”的生命之外,还有古典探寻的“永恒”的美好生活。
五、结语
所有的传统都不可能被驳倒与扼杀,它只是暂时地被处于现代性“洪流”中的现代人所嘲讽与遗忘而已。古典蕴涵着未来,未来有求于传统。只有在传统土壤中生长出的教育,才是最具根基、最温和、最有效的教育样态。不管是中国古典还是西方古典,都有助于教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融合。文化的多样性与真理的唯一性并不矛盾。古典教育的中西之别,并不是真理的冲突,而是真理在不同文化中的绽放。强调对古典的研究,就是要把中西古典教育思想重新置于现代背景之中,严肃地加以对待。在深化中国教育问题意识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古典,超越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争,而不被一些昙花一现的时新的“主义”所累。放弃古典就是戳瞎现代人自己的双眼。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在今日中国大数据崇拜的教育实证主义背景下,为教育哲学研究古典申辩,欲求从“欲望”返回“德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9]。
[1]朱光潜.什么是classics?[M]//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2]VOEGELIN E.On Classical Studies[M]//VOEGELIN E.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12).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256.
[3][英]利文斯通.保卫古典教育[M].邵威,徐枫,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41.
[4][英]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3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英]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1卷):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2.
[6]刘小枫.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M]//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67-156.
[7]单中惠.试析十九世纪英国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的论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91-96.
[8][意]列维尼.维柯与古今之争[M]//刘小枫,陈少明.维柯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07.
[9]STRAUSSL.The Cityand Man[M].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64:240.
[10]金生鈜.教育哲学的内在精神[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4):27-31,36.
[11]刘小枫,陈少明.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
[12][古希腊]柏拉图.普罗塔戈拉[M]//刘小枫,编译.柏拉图四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48.
[13]袁振国.实证研究的三个核心词[EB/OL].(2015-10-23)[2017-08-24].http://www.ed.ecnu.edu.cn/?p=2782.
[14]俞吾金.重建思想的维度[N].社会科学报,2012-08-30(001).
[15]甘阳.文明·国家·大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34.
[16][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
[17][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307.
[18][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M].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9]金生鈜.保卫教育的公共性[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80.
[20]王坤庆.试析教育学科分化的内部矛盾[J].中国教育学刊,1999(1):10-13,20.
[21][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2][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演讲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5.
24]ARENDT 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M]. San Diego, NewYork,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465.
[25]吴元发.教育哲学研究中“古典”失落的现实、原因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5(18):8-14,59.
[2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5.
[27]李长伟.古典公民教育透析——一个目的论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5(4):129-135.
[28][德]弗里德里希·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M].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6.
[2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