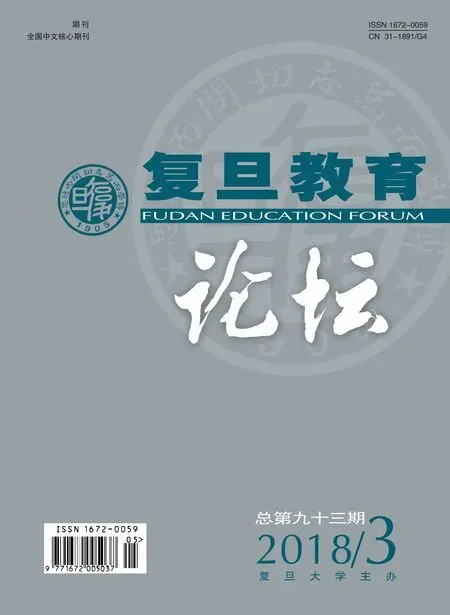美国教育法的司法执行力
——基于“萝莉案”的法学分析
杨克瑞,李双双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210038;2.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依法治教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中国教育的法制化取得了很大进展,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基本法的教育部门法律体系。然而,法制不等于法治,现行教育法的司法实践,并不能令人满意,出现了很多有关教育法是“软法”(soft law)的非议或责难[1]。换句话说,教育法的制度文本建设,仅仅是法治的起点,真正的依法治教的实现,更需要教育法的司法支持。所谓司法(Justice),即法的运用。无论是将其理解为“对法律的适用,是特定机构运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一种专门活动”[2],还是认为它是“法院或者法庭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或争议”[3],实际上其意义都在表明,司法即执行或行使法律,是指立法条文得到法院等审判机构的援引采纳。法律条文的执行程度及其效果,也就体现了司法执行力。毫无疑问,法律的价值就在于执行,即司法。从法制建设到司法实践的完善,这必将是推进中国教育法治的重要取向。探讨美国教育法的司法执行特征,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教育法执行的理念,推进我国教育司法的进步历程。
一、美国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萝莉案”
美国教育法的司法特征,是美国法律文化的产物。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若从法律渊源而言,这种说法并不为错,因为判例法的确是英美法系的重要特征,而且美国的法律制度,最初就是移植于英国。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法制文明的进程,美国的成文法日益丰富,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准确地说,美国是判例法与成文法并重的国家。二者的相辅相成,恰恰构成了美国司法的最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判例法的经验积累促进了成文法的成熟,而法官对于成文法的权威解释造就了判例法的经典。美国的教育类法律之所以有较强的司法执行力,与这一司法特征有着重要关系。
判例法对于美国教育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一些重要政策的历史转变,往往是由判例所开启的,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法院系统又分为联邦与地方两大系统。二者没有从属关系,只有管辖权上的不同划分。联邦系统法院由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三级构成,可以依次上诉。地方州法院系统同样为三级体系,即州初审法院、州上诉法院与州最高法院。
相对而言,美国教育类制定法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作为联邦制国家,其教育事务管理归属各州的地方权力。联邦政府对于教育问题的立法,在“二战”以前的很长时间内都是很谨慎的。虽然其早期有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赠地法案》(Land Grant Act)、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史密斯-休斯法》(Smith-Hughes Act of 1917),以及著名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等法案,但从这些法律的名称中也不难看出,它们并非纯粹的教育法,只能被视为有关教育的法案,是通过相关内容来带动教育问题解决的法律。从立法策略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路径。直到“二战”后的60年代,特别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以及“民权运动”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的态度才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积极涉足教育、民生等传统意义上的地方事务范围。当然,这种涉足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更多的是以经费配套的方式来加以鼓励与引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教育领域的立法也进入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法》(1963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1965年)、《高等教育法》(1965年)等相继颁布。
与“萝莉案”相关的《残障儿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PL94-142),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75年颁布的。该法案不仅是美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特殊教育类法律之一。它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资助法案。各州为了能够享受到联邦政府的这项经济资助,必须为所有存在身心障碍的儿童提供“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4]221。特别是该法案中所确立的特殊教育六大基本原则,成了美国各类学校进行全纳教育所必须遵守的基本理念,也是每一位教师所应当熟悉的教育规范。这六项原则就是:(1)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FAPE);(2)最少限制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LRE);(3)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IEP);(4)正当程序保护;(5)非歧视评估;(6)父母参与。这些原则看似通俗易懂,但能否真正依照立法精神而被遵守执行,现实情况却远非法律条文这么简单。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法律文化更是这样一种现象。立法之后的司法运用,才真正让法律鲜活起来,从而赋予其真正的法律生命力。此后出现的“萝莉案”真正印证了这部法案的时代价值与深远影响。
二、“萝莉案”的司法过程分析
该案件的主角艾米·萝莉(Amy Rowley)是一位听觉障碍学生,仅有微弱的残余听力,但却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智商高达122。1978-1979学年,她到了纽约州某郡的亨德里克·哈德逊中心学区(Hendrick Hudson Central School District)的某小学就读一年级。学校接收到该名学生后,首先基于《残障儿童教育法》的规定,与其家长共同制订了个别化教育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1)基于最少限制环境而将萝莉安置在普通班学习;(2)为其学习提供助听设备;(3)派语言治疗师每星期为其提供3小时的语言治疗;(4)派聋生指导员每天对其提供1小时的个别教学。上述这些安排措施,家长都表示同意。此外,家长还要求,学区能够在学术性课程上为孩子提供手语翻译服务。
关于手语翻译的服务项目,学区方面经过多方面考虑后拒绝了。学区方面主要是基于以下情况所做出的判断:首先,曾为萝莉在幼儿园期间担任过手语翻译的人员,认为其在普通班学习是可以不需要翻译的;其次,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学区身心障碍委员会的调查所支持。但是,萝莉的家长则坚持认为,孩子的听力障碍直接影响到她对于学术性课程的学习,学区只有提供手语翻译,才能达到《残障儿童教育法》所规定的“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要求。显然,对于手语翻译服务是否为法律所规定的“适当”情节,双方存在分歧而无法达成一致,漫长的司法程序也由此展开。双方经历了多次拉锯式的行政救济与司法过程,从学区基层的听证会直至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形成了美国教育史上著名的经典判例,即“哈德逊学区诉萝莉案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Hendrick Hudson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v.Rowley,U.S.,1982,以下简称“萝莉案”)。
(一)听证会裁决
根据《残障儿童教育法》的规定,地方学区应当为残障儿童提供“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学生家长若对学区的教育安排不满意且不能达成一致时,首先可以选择的公正的正当程序是听证会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教育听证会的组成方式,各州不完全一致,主要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间教育部门或州教育机构来主持。萝莉的家长首先向地方学区申请了听证会正当程序。地方学区听证会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与证词后,认同地方学区为萝莉所提供的个别化教育方案,否决了萝莉家长的手语翻译要求。其基本判断理由在于:“萝莉的教育水平、学业成就,以及与班上同学的社会互动情况,在没有手语翻译服务的帮助依然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平。”[5]87
(二)行政申诉
对于听证会的调解结果,萝莉家长显然不能满意,他们又寻求了进一步的救济途径——行政申诉。根据《残障儿童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学生家长或教育部门如果对听证会的裁决结果不服从,可以向州教育机关提出申诉。州教育机关应当对于听证会裁决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无偏性审查(an impartial review),并做出独立的裁定。萝莉的家长由于不能接受地方学区教育机关的听证会裁决意见,因而向纽约州教育厅直接提出行政申诉。结果,纽约州教育厅厅长在审查听证会有关材料记录及其相关证据后,依然支持听证会裁决,同样裁定地方学区不必为萝莉提供手语翻译服务。
(三)联邦地区法院判决
萝莉家长在行政申诉依然败诉后,更是将维权之路坚定地走了下去,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司法诉讼。其诉讼理由根据是:地方学区拒绝向萝莉提供手语翻译服务,这违反了《残障儿童教育法》中的“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似乎发现了新的证据材料。其调查表明,尽管萝莉在普通班的适应表现不错,而且学业成就比一般同学的表现更好,能够顺利升级。然而,她在普通班上的确无法了解全部的课业内容。萝莉家长的律师指出,孩子的智商高达122,即便佩戴助听器,也只能理解教师授课内容的59%。换句话说,她如果配备了手语翻译,学业成就将会更加优越。基于这种调查判断,联邦地区法院认为,萝莉的潜能与已有学业成绩之间的确存在差距,据此可以判定,萝莉没有能够享受到“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地方学区拒绝提供手语翻译的行为是违法的,必须更正。
(四)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结果,使得故事情节发生了急剧转折,地方学区陷入了较为被动的境地。他们感到无法接受,同样依据法律程序提出了上诉。由于该案件是在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地方学区将此上诉到了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结果却是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支持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联邦地区法院的事实认定是清楚的,地方学区的行为违法。
(五)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判决
地方学区对于上诉的结果感到遗憾,他们继而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能够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不仅案件棘手,而且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萝莉案”是联邦最高法院自《残障儿童教育法》1975年颁布以来首次接触到的相关案件。联邦大法官首先分析了“萝莉案”的实质,即梳理清楚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残障儿童教育法》中有关“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其立法精神是什么?第二,各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在审理教育类案件时,应扮演什么角色?大法官们在对司法审查时发现,虽然法案本身对于相关名词都有定义规范,但这些定义往往属于功能性定义(functional definition),尚不能提供明确的操作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探求立法者的真实意义,回顾了当时国会议员的立法报告书。从立法者的立法精神来看,该法案的实质在于,让残障儿童能够公平地享受公共教育,这也就是说,公平教育是立法的中心思想,而并不是如何促进残障儿童潜能的最大发展。据此,联邦最高法院的威廉·伦奎特(William H.Rehnqusit)等大法官做出了如下判决:“如果地方学区对身心障碍儿童提供人性化的教学,同时也提供充分的支援性服务……则表示该儿童已经接受了免费且合适的公立教育。”[5]93至于各级法官的角色定位问题,联邦大法官给出的忠告是,各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在审理教育类案件时,“必须谨慎地避免将自己喜欢的教育方法”强加给学校,因为法官可能缺乏解决教育政策问题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经验[4]227。
三、美国教育法的司法特征分析
从1978年开始至1982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宣判,历时四年的“萝莉案”终于有了最终的法律结论。案件故事本身跌宕起伏,《残障儿童教育法》也得到了司法界的实践检验。关于一位普通残障学生的公平教育权之争的案件能够经过层层司法环节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生动诠释了教育法治的精神。该案件在美国教育司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确立了美国特殊教育的“萝莉标准”,即为“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做出了最具法理性的司法解释。此案件也足以表明,只有将立法付诸司法实践,才能真正彰显法律的价值。美国法学重视判例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判例法,同时也是实践并验证成文法。以案例为突出特征的美国教育法学,恰恰是其司法制度整体发展成熟的结果,即教育法的司法化。其教育法之所以能够被司法实践运用,与其立法中的权利精神、权利救济中的正当程序、执法中的法理精神等是分不开的。
首先,教育立法的权利本位。教育司法的前提在于立法,立法质量也就直接决定着教育法的价值实现。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教育法作为一项事业部类的法律,它既具有通常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性与强制力特征,更具有事业相关人的权利保护特征。“法律秩序的任务是,调和在任何社会中迫切要求认可的权益,并且决定其中哪些应被确认为通过法律加以推行的权利。”[6]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教育法的理解,即“为了对全美4690万名中小学生负责,美国公立教育的设立与管理必须以法律为准绳”[7]。因此,权利关怀应是教育立法的重要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教育法首先是一部面向师生的“权利法案”,而不是立足于教育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行政法。因此,师生权利得以充分保障的法律,才是真正有质量的教育法;也只有赋予其深切的权利关怀,教育法才可能真正实现其“教育”的意义。
其次,权利救济的正当程序。回顾“萝莉案”的一波三折,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不仅在于结果的扣人心弦,还在于司法过程的严谨与权利救济程序的完善。法治社会的突出特征就在于,人们对于社会纠纷的处理,不依靠个人武力,也不是依赖人情关系,而是依据法律而寻求解决的正当程序。从听证会到行政申诉,再依次进行法院上诉,萝莉家长与地方学区都依靠法律手段,通过法律正当程序解决。显然,完善的法律救济,正是人们对法律充满期待的重要制度力量,也是构成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法律情怀及其法律信仰的重要制度保障。
再次,教育司法的法理观念。教育法是基于教育教学活动的法律规范,其既体现了教育学的专业知识,同样也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对于教育法而言,其法律条文的规范,往往是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因此,对于教育法的理解与运用,应是教育专业与法律专业的充分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所做出的司法判例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判例,不仅仅在于他们本身的“最高法院”地位,更在于他们专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专业的法律精神。他们对于一些争议性条文的理解,能够坚持从立法精神的角度来解读,从原有的立法报告书中寻求法律的真实含义,从而形成更为权威的司法解释。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不仅仅是对于法律的遵守,更体现为一种法律的信仰。因此,教育司法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规定的执行,更是教育情怀与法律精神的体现,是对法律价值的弘扬。
四、提升我国教育司法执行力的思考
增强教育法的司法执行能力,这是教育法治的应有之义,也必将随着我国教育法制的完善而逐渐得以重视。在教育法治化的历程中,法律文本的建设仅仅是法治的起点,真正的生命活力在于教育法律的司法执行。美国教育法案的司法实践证明,教育法在学校教育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是必须遵守的工作规范,其价值与使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对于提升我国教育法的司法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教育法的法律定位与司法执行力。教育法的准确定位,直接决定着教育法的立法质量,而提高立法质量正是提升教育司法执行力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教育法本身是否具有较强的执行条件无疑是提高其司法执行能力的基本前提。然而,我国教育法的法律定位模糊,恰恰成了直接影响其执行力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当前的教育立法存在两方面的定位模糊或者“漂移”:一是潜在的公立学校意识;二是行政部门法导向。由于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关于我国教育法的法律地位,“主流观点还是认为教育法应归属于行政法”[8]。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现行教育立法中对相关行为人的权利保护不足。以公立学校为潜在的教育立法对象,以学校工作改进为教育立法目标,这都导致了教育立法的事业规划倾向,从而忽视或淡化了教育活动中的师生个人权利的保护,从根本上导致了在学校的冲突事件中,教师和学生无法从教育类法律中获得充分的权利保护。例如,近些年教育领域所出现的择校问题、留守儿童等社会所普遍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都涉及基本的个人教育权。然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内的基本教育法律,对个体教育权利的司法救济都不够明确,无法成为依据法律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司法精神。相反,我国依靠“人大”立法部门的执法检查或上级政府部门督导的教育法执行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行政化工作模式,恰恰让法律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教育法应有的司法执行力。
第二,教育法的功能定位与司法执行力。当前中国的教育类法律,在现有法律门类中不仅地位模糊,而且价值使命也不够清晰。作为一项事业部门法,根本使命应当在于推动本事业的发展,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应当成为基本的立法精神。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以公办学校为主体,现行的教育类法律有意无意地侧重于行政管理的行为规范,从而带有更多的行政法色彩。这种法律定位偏差的一个后果就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立法重视。权利保护不足,受益人对象不明,这成了教育类法律“宏大叙事”的必然结果,故而令人“敬而远之”,没有人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法律关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例,正如法案的题目所示,其应当立足于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可是就法律的内容来看,其更多是对于民办学校的办学规范与条件约束,反而缺乏实质性的“促进”内容,更缺乏民办学校作为事业法人的权利保护。因此,该法律并不能为民办学校伸张公平与正义,其令人失望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教育法的道德宣示与司法执行力。法律意味着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然,对于社会行为的规范,除了法律强制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弘扬的道德引领。但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同,也恰恰在这里。“有很多情形,是因为陈义较高的伦理态度,未能充分形成群众意见,以致没有产生与它相当的法律行为。”[9]道德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俗力量,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然而,道德意义也就在于,它是一种引导力量,而不是强制力量,否则就会沦为“道德绑架”的嫌疑。法律规范的意义,就在于其强制力,这是基于国家的政权力量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反观中国现行的教育类法律,法律的说教化与宣示性往往占据重要内容,真正的法律规范及其违法责任反而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保障功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为例,作为特定群体类型的法律,其核心意义应当在于对教师权利的保障,应当成为教师维权的法律依据。可是,现行法律更多的是以道德化的方式提出教师的责任,成为了道德化的法律。显然,它缺失了权利保护的色彩,其自然难以充当教师们的维权“法宝”。
第四,司法部门的法理观念与司法执行。教育法的执行,归根结底还在于司法部门的执行。这种执行力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也在考验着司法者的法律素质。换句话说,是否能够自觉地以教育法的视角来审查教育案件,这是对基层司法实践的职业要求。“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10]。美国教育法的司法执行力,正是源于其内在的判例传统,对于法律精神的真正把握。实际上,除“萝莉案”之外,还有很多涉及特殊教育及其服务的争议,最终都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如1984年德克萨斯州的“欧文独立学区与塔特罗诉讼案”(Irving School District Independent V.Tatro)等[11]。这些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于法律的敬畏态度以及法官的职业精神,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能够从立法精神的角度来解读法律,无疑是弘扬教育法司法执行力的生动教材。
总之,从美国“萝莉案”可以看出,教育法的司法执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将教育立法纳入司法的审判执行过程,教育法的生命力才能够真正彰显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可执行性应当是我国未来教育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使命。从立法的角度分析,提高我国教育法的司法执行力,其先决条件应在于教育司法体制的改革:即从事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从教育法的应然体系走向实然体系,并强化教育法的执行标准与法律责任。与此同时,司法部门如何自觉地运用教育法的教育思想与法律理念,积极提高教育法的司法执行力与社会影响力,也是新时代中国教育法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1]李效同.教育法须走出“软法”的尴尬[EB/OL].(2012-01-12)[2017-12-01].http://www.sdjys.org/index.php/News/view/id/11848.html.
[2]钟玉瑜.中国特色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
[3][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1.
[4][美]米基·英伯,泰尔·范·吉尔.美国教育法(第三版)[M].李晓燕,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8.
[5]李庆良.特殊教育行政与法规[M].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4:87.
[6][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273.
[7][美]内尔达·H·坎布朗-麦凯布,等.教育法学(第五版)[M].江雪梅,茅锐,王晓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
[8]申素平.教育法学:原理、规范与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6.
[9][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张茂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0.
[10]张维平,马立武.美国教育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5.
[11]BOYLE J,WEISHAAR M.Special Education Law with Cases[M].Boston:Allyn and Bacon,20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