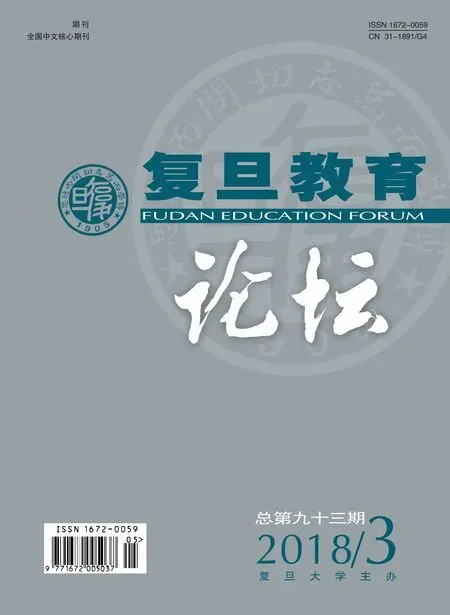从“商改国立”到国立:私立南开大学复校进程中的国家意志与恩怨纠葛
金 国
(1.常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江苏常州 213164;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私立南开大学(下文简称“私立南开”)创办于1919年,1946年改为国立。在社会转型变革之际,经校长张伯苓苦心经营,私立南开迅速蜕变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府。抗战期间更是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成就了“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1]。1941年12月8日,私立南开首提复校计划。1945年8月,蒋介石通过文官处致函张伯苓提及“商改国立”。1946年4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私立南开的复校进程告一段落。收归国立非私立南开所愿,但为生存别无他法。
私立南开的复校已有学者关注。有观点认为,蒋介石在帮助解决复校经费时希望私立南开“商改国立”,可能并非如人揣测有控制南开教育的用心,或许只是为了管理制度上的需要,以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2]如若还原蒋介石提及“商改国立”的时代背景以及国民政府复校阶段的相关举措,以防“群起效法”一说似可商榷。
本文将私立南开置于抗战复校的大背景之中加以分析,认为私立南开从“商改国立”到“国立”的复校进程背后既有国家意志的强势介入(整合办学资源、控制意识形态),也掺杂着个人恩怨纠葛。因此,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以防“群起效法”,并不符合史实。私立南开收归国立,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作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私立大学,对私立南开复校进程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可以呈现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复杂环境,有助于理解特定背景下政府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府学关系”。
一、“商改国立”的背景:蒋介石的“承诺”与私立南开的复校困境
“商改国立”的动议由蒋介石于1945年8月通过文官处向张伯苓首次提出。1945年8月11日,就复校经费问题,张伯苓致函蒋介石,希望政府能比照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的经费拨付予以扶持。随即,文官处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向张伯苓提出“商改国立”。[3]当然,张伯苓不赞成由“私立”改为“国立”,仍愿以“人民团体立场”[4]继续办学。蒋介石之所以提出“商改国立”,与其“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有关,更与私立南开的复校困境密切相关。
应该说,复校困境是所有内迁高校共同面对的问题。私立南开因其在抗战中的特殊“遭遇”,复校进程尤为艰难。当然,这一特殊遭遇也促成了蒋介石“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
私立南开是最早被日军轰炸的大学之一,校舍、设施和设备等均遭毁灭性的破坏,客观上造成了复校基础薄弱的现实。日军轰炸给私立南开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据1937年7月30日《申报》记载,“二十九日下午津战甚烈,飞机四出到处轰炸,声震屋瓦,以市政府、警察局、南开大学、东总两车站等处尤甚。……同时有两架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投弹,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5]7月31日,《申报》接着报道:“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6]日军的轰炸给私立南开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私立南开也因此成为抗战以来首批遭此劫难的高等学府。经由媒体的广泛报道,私立南开成了战时高校面对强敌不屈之象征,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关注。[7]也基于此,蒋介石在1937年7月13日召开的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许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日军蓄意轰炸对于私立南开是灾难性的,数年苦心经营毁于一旦。虽然蒋介石允诺“有中国即有南开”,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亦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8],但真正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私立南开若要重新开始,则非易事。私立大学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而战争带来的社会环境破坏,非短时可以恢复。战后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办学环境较抗战之前更为恶劣。因此,相比一般私立大学,私立南开要面临更为薄弱的复校基础。
除却校舍被炸之外,私立南开复校困境还体现于师资的严重亏缺。1946年3月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汇报三校教职员数,提出私立南开亟须聘任教员约30人。[9]何廉的回忆大体能反映私立南开师资短缺的“现状”:“经过八年的抗战……大多数主要的教员也分散了——有的参加政府工作,有的被业界拉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张伯苓的老同事,都是富有经验和忠于职守的人,但是他们由于年老且饱受战争摧残而逐渐凋零;张伯苓校长本人也已是很大年纪了。”[10]这段回忆不仅描述了私立南开师资短缺的困境,也道出了私立南开师资短缺的重要原因,即:战争对于教育生态、办学环境的破坏,给师资留任与延聘带来困难。
面对私立南开尤为艰难的复校困境,蒋介石提出“商改国立”,大体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回应其“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不仅是对私立南开的承诺,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所有因战争而被毁坏的私立高等学校的承诺。倘若私立南开因办学经费而停办,无以展示政府支持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诚意,也不利于团结更广泛的教育界人士参与国家在战后的重建。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其与张伯苓之间的“情谊”。应该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蒋介石、张伯苓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和“情谊”。关于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情谊”,有学者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论证[11],本文不再赘述。蒋介石之所以通过文官处向张伯苓提出“商改国立”,即是顾及二人之间的“情谊”。“情谊”虽在,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之意并未就此消弭。
二、从“商改国立”到国立:复校进程中的国家意志
私立南开从“商改国立”到国立的复校进程背后体现着国家意志:一方面,收归国立是整合办学资源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收归国立也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内在要求。
(一)院校调整,整合办学资源的需要
其实国民政府在制定战时教育政策时,也在规范和调整高校的设置与布局。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总则与教育)》《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大纲》等文件,指导战时院校调整,整合办学资源。
为使战区专科以上学校不受战事影响,国民政府决定将高等院校先行迁入内地,并借以整合调整。“据统计,专科以上学校迁入后方的共有76所学校,在本省境内迁移的共有17所学校,迁入陕甘地区的有5所学校,迁入云南、广西的共有17所学校,迁入湘川的有17所学校,迁入上海租界以及香港的有20所学校,等等。”[12]为提高办学效率、整合办学资源,国民政府有意将性质相近的学校进行合并,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资源,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例如:将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与私立南开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将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北洋工学院合并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将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将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办理;等等。
当抗战结束,复校工作即被国民政府提上议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面临着复员经费紧张的窘境。“据统计,苏、鲁、晋、豫、冀等十六省,以及京、沪、平、津、青岛五市专科以上学校30所,几全数遭受损毁,加之中等学校、小学等校舍、设备的破坏,使得复校经费剧增,仅湖南一省而言,即需五百七十余亿。”[13]以1946年为例,国立学校复员经费预算总数为600亿元;[14]年度全国教育经费预算总数为2101387000元,临时费586236000元,两项共2687623000元,仅占年度经费预算总数的5%,其中高等教育经费仅为1617855000元[15]。虽然复员经费加上年度教育经费预算与抗战之前相比总数可观,但鉴于物价飞涨、后方学校遭受破坏之严重、复员学生数量较之前不降反升等因素的存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费支绌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办学资源,提高复校后的办学效率?有媒体指出,“教育复员,并不是恢复到战前的情况,而是要根据八年来的经验教训,想出办法来改变我们的教育缺点,充实我们的教育内容,实践教育‘中国化’的号召,让全国学校真正成为建国人才的培养所”[16]。因此,需要国民政府对教育复员进行资源整合、统筹安排。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对各类复校问题进行决议。会议提出要对“专科以上学校作合理之迁移与分布,其因战事停顿而具有历史之学校应予恢复”[17]1,并希望各校在1946年9月完成复校工作。此外,会议着重强调了“复员非复原”的复校基本原则,就专科以上的复校工作作了部署,要求“对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暨其院系科别之增减,必须先有通盘计划,方足谋日后之合理发展”[17]2。在此方针指导之下,政府复校工作拉开帷幕。
对于私立南开来说,早在1941年12月便将复校提上议程。按照复校计划,学校将分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与工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文学系、英文学系、历史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设算学系、化学系、物理学系;法商学院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工学院设电工学系、化工学系、机械学系。[18]1945年春,私立南开正式向国民政府递交复校申请。
相比以往,1945年的复校计划增加了学院数量和招生规模,以图事业发展。具体来说,学院数量从3个扩充至5个,较之前新增了工学院和医学院,并准备在工学院筹设纺织专业,在法商学院筹设新闻学系,且计划招收医学预科学生,以建立医学院、实习医院等;学生人数预计第一年为830人,至第四年为2020人,其数量为抗战前的四到五倍。院系增添以及学生规模的扩充意味着经费预算的增加。就国民政府复校预算而言,私立南开的复校计划无异于“狮子大开口”,也违背了院系设置通盘考虑的基本原则。以工学院为例,尽管张伯苓想筹办工学院,但教育部以“平津一带设置工科之院校甚多,原有机械、电工、化工等系毋庸恢复”[19]为由未予批准,并要求“已招新生应移交国立北洋大学收容”[20]。
国民政府面对声名卓著且一度成为战时高校不屈之象征的私立大学,确如文官处所言,“倘南开以私立之故,竟因经费无着而停顿,实非政府维护教育之至意”[21]。国民政府事实上面临两难选择:其一,就私立南开的特殊性而言,政府必然要尽力补助,甚至“逾格扶持”[21];其二,就学院、系科的通盘考虑而言,私立南开的复校计划存在有违国民政府复校基本原则之处。而从教育部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整合办学资源,调整院校、系科的设置,是战后复校的重要考虑之一。
国民政府既要补助私立南开,又要合理配置平津地区的办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面对私立南开如此“狮子大开口”式的院系设置和招生规模,要妥善解决其复校问题,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使之完全听命于教育部,为院系调整和提高办学资源的利用率提供便利和保证。
(二)推行党化教育,控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
蒋介石重视教育,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是经济和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12],另一方面也因为教育能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抗战伊始,国民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强化青年学生的训育工作。
为争取青年的支持,借以培植“党魂”,巩固“党基”,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2月就出台了《青年训练大纲》详细指导青年训育工作,特别提出要使得青年“一信仰三民主义,二信仰并服从领袖”[22]。“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传授而忽略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过于商业化起见”[23],同年3月颁发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9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通令各级学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并颁发党员守则十二条,使青年体会力行”[12]。
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对于青年学生对革命和政党的作用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国家暂未统一之前,国民政府对待学生运动“秉持一种相对支持的立场,并且受最初相对进步的民众政策影响,也曾一度努力为学生运动创设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24]。但在国民政府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后,对学生运动开始采取高压和限制的政策。因此,强化训育即被提升到重要位置。于共产党而言,在其早期创建之时,就认识到青年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说,“青年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25]因此,对共产党来说,争取青年学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争取有助于未来胜利的重要力量。
虽然国共实现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抗战背后,两党之间依然“暗战”,乃至“明战”不断。193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施限共、反共、剿共政策。[26]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国民党则通过遍设党团支部,加强渗透,以对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西南联大也概莫能外,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联名致函蒋梦麟,要求在联大设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27]128
鉴于周恩来与私立南开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为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抗战期间,周恩来与私立南开接触甚密,多次以校友身份造访张伯苓以及南开师生。应该说,周恩来数次“南开之行”并非仅是畅叙师生、同窗之情,也有争取和说服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就曾明确表述过,“过去共产党并不是没有争取过张伯苓,但是跟他说谈,他不听,介绍书给他看,他不看”[4]。其时,张伯苓担任三青团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正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推进党化教育,并号召教育界同仁鼓励学生加入国民党,为抗战建国而努力。针对张伯苓向国民政府“靠拢”的现实情况,周恩来也曾积极争取,但效果甚微。据相关回忆,周恩来常去看望张伯苓,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争取张伯苓之外,中共也积极争取联大学生(包括南开学生)。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在此之前,1938年底,中国国民党三青团直属分团部筹备成立。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共地下支部成员以及进步学生进行抓捕,对联大进步师生进行打压、威胁,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致使进步师生流血牺牲。
西南联大进步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国民政府认识到控制学生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抗战结束,复校之际,国民政府在核准学校补助费用时特意反省:“我们对各学校实在情形,不够明了”,并要求“高等司分工,应分学校单位管理,使每一主管同事,能对学校设备情形,教授如何,学生活动有无政治背景,都要明了才行”[28]。早在1945年10月,教育部就公布了《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用以指导学校训育工作,其任务包括“关于三民主义教导之研究事项;关于训导人员之培养及指导事项;关于军事教育、童子军教育之督导及考核事项;关于学生自治团之指导事项”[29]。
私立南开改为国立后,国民政府更是加强了在校学生的训育工作。1946年,南开大学遵照教育部命令,组织校级训育委员会,并颁发《训育委员会组织规程》。应该说,国民政府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有利于强化对南开大学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其推行党化教育提供了便利和保证。
此外,从个人经历来看,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对于推行党化教育甚有心得。朱家骅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而中山大学正是以党化教育而享有盛誉。朱家骅主政期间,中山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校内设了一个政治教育办公室,负责学生思想训练,并直接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办公室负责在大学里开设三民主义课程。并且监督学生的课外活动,监督范围从学生报纸《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的编辑方针到学生细微的行为举止及学生宿舍的衣物式样等,无所不包。”[30]也因此,蒋介石在选择中央大学校长时“钦点”朱家骅。朱家骅到中央大学之后,便延续其治校方略,强力推行党化教育,加强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甚至“出钱收买部分学生,暗地里监视师生的思想与行动”[31]。而将党务带进校园后来也成为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27]126有鉴于朱家骅在推行党化教育和控制高校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在面对私立南开复校的具体情况时,考虑将其收归国立,也似可理解。
三、朱家骅与张伯苓的恩怨纠葛:国立化进程中的“催化剂”
梳理相关回忆录,可以发现朱家骅在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除上文所述朱家骅对于党化教育甚有心得之外,朱家骅与张伯苓的“恩怨”也是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的“催化剂”。据何廉回忆:“在张伯苓的计划(笔者注:即‘复校计划’)提交行政院讨论时,我是作为南开大学的代表参加的。政府对这个计划并不赞成,而教育部长朱家骅则正式提出南开大学改为国有、由张伯苓作第一任校长的提案。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张伯苓只能勉强默认。这个提案在行政院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10]朱家骅为何提出将私立南开改为国立?是秉公办事,抑或其他?要明确朱家骅在私立南开收归国立过程中的态度和立场,就有必要分析其复校经费的分配原则。
1946年8月,教育部召开本年度第六次工作计划讨论会,部长朱家骅针对复校工作作了十六条“指示”。涉及经费分配原则的事项列举如下:“十五、对大学设备,应制定标准,应规定在中国现况之下最低限度。先调查不及标准者,有若干,哪几个?够标准的有若干,有哪几个?对不及标准者,应设法帮助,使之达到标准;够标准者,要扶助之发展为国内第一流大学。国内第一流大学要发展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如中山、中正、英士各大学,更应特别充实。特别注意,此种情形,全在认清重点,妥为运用。中等司亦同。十六、对各校经费,应视其学校设备、校舍、建筑、教授人才一切内容,而定其多寡。不可一视同仁,平均分配。不然,则是没政策。”[28]
从朱家骅的复校经费分配原则来看,一方面强调设备的增设要制定标准,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各校经费应视“学校设备、校舍、建筑、教授人才”等所有内容,综合考虑再行定夺。并且着重说明,“不可一视同仁,平均分配”。在实际操作中,确实遵循了“不可一视同仁”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关于工学院的设置整合之中。其时,天津北洋大学设有工学院,北京大学拟增设工学院,与此同时,教育部却正打算取消办学历史更为悠久的国立北京工学院。[32]虽然教育部有整合办学资源之必要,但如何整合资源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值得商榷。
在工学院的设置上,朱家骅撤销了办学历史更为悠久的“国立北京工学院”,反而在北京大学筹设工学院。对此,以胡厥文为首的国立北京工学院复校委员会40余人联名上书朱家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学校悠久的办学历史以及继续办学的必要性,并在文末特别强调:“抗战胜利之后,各内迁之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工学院与专科学校,均已先后奉准迁回原址,继续开办。且历史不若本校之悠久,性质亦不若工科之重要,成绩不若本校之优越者,特邀政府之重视,奈何本校独抱向隅?揆诸情理,殊失其平!亦与钧部最近领导之全国教育复员会议所规定之原则似有未符。”[32]
从表述内容来看,国立北京工学院立场坚定,表达了对朱家骅复校工作有失“公允”的不满。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复校问题上。抗战伊始,北平师范大学奉命西迁。但在战后,教育部并没有将其列入复员计划名单,由此引发了师生、校友的“复员”“复大”运动。在师生、校友的极力争取之下,终达迁回继续办学之目标。北平师范大学的复员、复大运动,也反映了朱家骅在复校过程当中“没有一视同仁,采用双重标准”[33]。
这一双重标准也体现在私立南开的复校过程中。按照1945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精神,“其因战事停顿而具有历史之学校应予恢复”[17]1,这与朱家骅所提出的将私立南开改为国立大学是相违背的。由私立变国立,属于办学性质之改变,何来恢复之原意?
朱家骅为何如此对待私立南开?何廉的另一段回忆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节录如下:“张伯苓来信说,1948年春蒋介石委员长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他接受了,但是有一个默认的谅解,就是他同时还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后来,教育部长和北大集团首脑朱家骅提出来,张伯苓应该辞去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张伯苓抵不住教育部对他施加的压力,但他要求由自己提出负责南开的人选……我了解事情的背景,知道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分歧的原因。”[10]结合上文何廉的回忆,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教育部长朱家骅在私立南开国立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二,张伯苓与朱家骅之间存有分歧,这一分歧应能部分解释朱家骅为何提出将私立南开改为国立。
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到底因何存有分歧?何廉对此未作交代,但从其他人的回忆中仍然能找到一些线索。张锡祚(笔者注:张伯苓的儿子)在回忆中就曾提及张伯苓与朱家骅之间存在“恩怨”:“他(笔者注:朱家骅)有个儿子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个学生倚仗权势,目空一切,屡犯校规,且又屡教不改。学校为维护校风校纪,就照章给予了开除的处分。为此,朱家骅像是挨了一记耳光。”[34]且不论张锡祚所说是否属实,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存有恩怨,这在南开教职员中广为人知。诸如1946年黄钰生致函张彭春,提到相关“恩怨”:“回头再说南开。教育部像猫整老鼠一样整治我们……我们完全攥在教育部的手心里……如果教育部长根本不想改变,我也怀疑这种状况是否能有所改变……”[35]张伯苓开除朱家骅的儿子是否导致二人之间产生“恩怨”?朱家骅虽贵为教育部长,但毕竟也是孩子的父亲,儿子被开除,作为父亲难免感觉“难堪”。张锡祚的言论是否可信?这涉及“价值中立”的问题。如果确系此事导致张伯苓与朱家骅之间产生隔阂,结下“恩怨”,在有着刻意避讳、有意美化历史人物传统的社会,这样的原因恐怕也只能由张伯苓的亲属提出。具体所谓何事,不好妄加臆断,但不管怎么说,张、朱二人之间的“恩怨”应是成立的。这也导致朱家骅在诸多问题上坚持“照章办事”,从而做出诸多让张伯苓及私立南开“难以理解”的事情。例如,除了本文提及的坚持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坚决辞去张伯苓的南开校长职务之外,还有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款项分配上回避私立南开[10],等等。
四、结语
国民政府为何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以防“群起效法”一说有待商榷。其实,国民政府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背后包含着国家意志的考虑,以及围绕张伯苓而生发的个人恩怨纠葛。
就特殊性而言,私立南开是近代中国其他私立大学难以比拟的。作为首批遭到轰炸的私立大学,私立南开备受媒体关注,从而获得了蒋介石“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因此,在复校阶段,私立南开受到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格外关照”似可理解,其他私立大学怕也不会“群起效法”。况且,政府在复校阶段,补助范围也涉及其他私立大学。事实上,在抗战之前,私立南开就曾获得较多的政府补助,而并未见“群起效法”之说。此外,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处理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的风波中,亦作出让步,使得大夏大学不单维持了私立身份,还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高额补助。[36]因此,以防“群起效法”一说似不能完全解释国民政府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国民政府曾两次婉拒张伯苓将私立南开送归国立的提议。而复校期间,在张伯苓恳请继续维持私立之时,蒋介石却向其提出“商改国立”,这背后的原因与国民政府在战后对私立大学重视度的提升有关。所谓重视,体现在院校调整、整合办学资源的种种举措之中,更体现在强化私立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上。然而,国民政府也面临办学经费支绌的窘境,而不得不在复校阶段鼓励私人办学。据统计,1945年下半年,全国共有145所大学,其中私立大学50所,[37]约占全国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一。复校阶段,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希望更多民间资本襄助复校,希望“友邦之援助及人民自动捐献”,同时“深盼热心教育人士群起响应”[17]7。所以,落实到个案,从国民政府财力来说,非有国家意志的考虑,其实不希望在此阶段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当然,在收归国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个人恩怨纠葛等非制度性因素,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总之,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以防“群起效法”,并不符合史实。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私立大学,分析私立南开收归国立背后的多重因素,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多重因素呈现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生存环境,有利于理解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历史境遇与时代命运;另一方面,可以从私立南开的个案中管窥国民政府的私立大学教育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具体状况,有利于理解特定背景之下政府与学府、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1]陈平原.大学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7.
[2]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J].民国档案,2011(1):75.
[3]张伯苓.呈蒋介石函(两则)[G]//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097-1099.
[4]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5]佚名.南开大学损失奇重[N].申报,1937-07-30.
[6]佚名.日机继续轰炸南开[N].申报,1937-07-31.
[7]佚名.南开大学被炸毁各方深表痛愤[N].申报,1937-07-31.
[8]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36.
[9]佚名.西南联大致教育部代电[G]//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73-474.
[10]何廉.何廉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11]张晓唯.教育与政治: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国民政府[EB/OL].(2014-04-25)[2017-04-13].http://news.nankai.edu.cn/xs/system/2014/04/25/000178554.shtml.
[12]朱子爽.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M].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
[13]佚名.各地教育复员经费甚感困难[J].教育通讯月刊,1946(1):18.
[14]佚名.本年度复员经费预算[J].银行周报,1946(15-16):45.
[15]缪振鹏.谈教育复员[J].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46(2):1.
[16]佚名.教育复员[J].学生时代,1945(1):2.
[17]朱家骅.教育复员工作检讨[J].教育部公报,1947(1).
[18]佚名.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议(一)[G]//王文俊,梁吉生.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89.
[19]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来电[G]//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170.
[20]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致张伯苓电[G]//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151.
[21]佚名.文官处呈蒋主席签呈[G]//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22]国民政府教育部.青年训练大纲[J].教育部公报,1938(12-13):34.
[23]国民政府教育部.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J].教育部公报,1938(12-13):39.
[24]柳轶.1919-1949年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5.
[25]李大钊.《晨钟》之使命[G]//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7-182.
[26]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272-273.
[27]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6(4).
[28]佚名.教育部三十五年度第六次工作讨论会记录[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9]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公布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54-55.
[30]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7.
[31]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19.
[32]胡厥文,张泽垚,等.胡厥文等为恢复国立北京工学院致教育部代电[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33]孙邦华.抗战胜利后北平师范大学复员运动述论[J].北京社会科学,2014(6):75.
[34]文史资料研究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11.
[35]黄钰生.黄钰生致张彭春函[G]//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137-1140.
[36]韩戍.抗战期间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J].近代史研究,2016(1):124-137.
[37]佚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之院科系数(学院数)[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