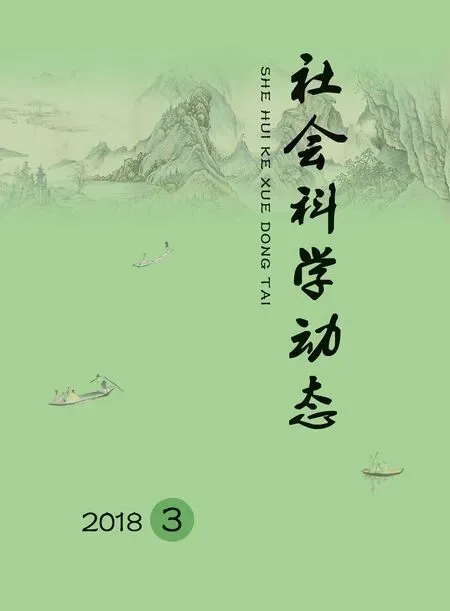论李传锋乡土小说“进城—返乡”模式
朱 旭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传锋“动物小说”系列的耀眼光芒遮蔽了他的乡土小说的独特魅力,使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李传锋在保持一定连贯性(即“进城—返乡”模式)的同时,又有新变和发展。在80年代的小说中,进城后又返乡的农村青年多是农村知识男青年。李传锋小说中这种农村知识男青年“进城—返乡”模式,主要在《人生,将从这里开始》 (1981)、《十里盘山路》 (1982)、《定风章》 (1982) 等小说中呈现出来。新世纪以来,农村打工妹进城后又返乡成为这一模式的重大发展变化,以《白虎寨》 (2014) 最为典型,但《白虎寨》并非空降而来,更是对早期《烟姐儿》(1981)、《警官罗立瓯》 (1986) 等小说跨越了时空距离的回响。这种继承、新变和发展,既是文学创作内在机制的演化,也是作者紧贴时代脉搏的生动表现。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各方面急剧变革的时期。“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中国的乡村如何在大变革中发展,乡村中的人又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紧跟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是乡土小说争相呈现的问题。李传锋的乡土小说创造性地通过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返乡”模式的书写,为乡村共享现代化成果和价值重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更是乡土小说发展到今天求新求变的有益探索。
一
在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对农村知识男青年进城后又返乡进行书写,李传锋并不是独一份。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路遥的《人生》等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模式。这些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气质不同,生命经验各异,但大致都经历了类似的人生轨迹:农村—城市—农村。他们如鲁迅笔下的那只苍蝇,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但内里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作品大都建立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从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势描写农民进城后又返乡。农民离开赖以生存了数千年的土地而进城,是对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向往,而返乡则是这种向往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的无奈之举。进城的农民往往水土不服,不得已返乡疗愈精神创伤,还乡是为了精神、灵魂能有所安放。因受经济事件牵连而被迫还乡的金狗(《浮躁》),“他求索,他斗争,他义无反顾地直面现实,他经历了生活的波折与苦涩之后又回到了‘河上’……他的全部命运际遇及心灵轨迹所呈示的思情启迪,都向我们诉说着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烦难艰巨,诉说着一个富有传统的民族在锐意进取的道路上必然会领受到的种种来自进取者本身的束缚与制约,诉说着农民的命运在急剧变迁的时代机遇中不能不产生的千姿百态的缓慢转变。”②还有因经商失败又身患绝症而还乡的隋见素(《古船》),“见素这个人物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也激荡着他强烈要求恢复‘人’的尊严、权力和价值的渴望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雄心胆量。他曾面对抱朴大声呼喊:‘你让我趴在地上过一辈子。你让我像你一样埋在活棺材里……不,我不干。’他以实践的力量迅速迎接着那不断冲击而来的经济观念:办厂、经商,计划准备成立更大规模的公司商店,对农村旧有的经济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③或者“走后门”东窗事发而被开除的高加林,“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高加林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路遥通过高加林命运的浮沉反思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弊端。”④变革时代的农村青年,进城尝试去做时代的弄潮儿,但由于城乡之间的鸿沟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最后的还乡几乎都是寻求精神的安放,都在败走城市后希冀通过还乡达到灵魂的救赎。
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青年在返乡后的生活和作为,《浮躁》 《古船》 《人生》等80年代的乡土小说并未着墨,似乎还乡就是结局,而还乡后是否适应,又如何开展新的生活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农村依旧作为“乌托邦”的载体存在,农村还是原始意义上农耕文明的栖息地。但是,还乡之后的经历往往才是生活的真相,今日的农村不能以旧有的眼光来看待,农村也有权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中来,农民也有共享现代化成果的需要,在变革时代如何重建农村的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迫切需要解决。《浮躁》 《古船》 《人生》等小说,在8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思考,也展现出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种种问题,但并未就此继续深入。李传锋此时的乡土小说,通过农村知识男青年进城后又还乡模式的书写,对80年代乡土小说最大的突破就在于详细呈现出农村知识男青年们还乡后的生存状态,返乡成为重中之重。这样的书写更是建立在城、乡作为相融共生的二元存在的态势之上,乡村也能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找寻到合适的道路。李传锋笔下的农村知识男青年们返乡,呈现出“土地崇拜”的情结,并身体力行参与到农村现代价值重建的过程中。即便是不得已的被迫还乡,他们都在经历人生的涅槃后,深悟出农民与土地的血脉相连。现代化不该成为农民脱离土地的借口和托词,土地不仅是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中生存、繁衍的依凭,到了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土地在乡土中国,依然至关重要。农民如何在新形势下扎根土地,进行现代化建设,重建乡土价值,是李传锋通过这些小说具体探讨的问题。而这种突破性的尝试所依凭的就是新形势下的新型“土地崇拜”。李传锋在他的乡土小说中认同农村紧贴时代脉搏做出相应改变,进行现代化建设乃至重构农村价值理念的诉求。返乡的知识男青年们带着新的眼光,带着否定之后的肯定重新审视自己的乡村,重新规划人生的道路,便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和更为深刻的意蕴。
李传锋80年代乡土小说的这一突破并非一成不变,对于农村知识男青年还乡后生存状态的呈现,对于他们能否扎根农村、如何扎根农村,作家在动态的探索中为读者勾画出一条脉络清晰的流线图。这个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思想摇摆——尝试扎根——找到路径。通过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走向,作者生动且有力地呈现出了这一动态过程。
在《人生,将从这里开始》 (1981)中,进城后又返乡的知识男青年鹤峰,高中毕业后“成为全世界第一届不能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梦想夭折,被迫还乡。一开始他内心无比苦闷,“我刚回农村那阵,好比一只跛脚的孤雁,完全是一副疲惫、颓丧的神情”,但“泥土和牛粪”,这些具有乡土气息的存在,使得他重新找回了安全感,苦闷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鹤峰坚定地相信“最有害的莫过于把胸无大志跟献身农村混为一谈”,这似乎是作者借鹤峰之口道出了内心最真实的态度:进城上大学与献身农村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当县里通知他因为父亲的烈士身份,可以到县城去待业的时候,鹤峰在寄给女同学的信中写道:“我没有理会这事,我有业了,何待之有?……国家在振兴,我也被‘振兴’了。”是对于土地怀有的复杂、深沉的情感“振兴”了他,“泥土和牛粪”振兴了他。尽管摇摇晃晃,一度摇摆不定,但在无数历练之后他终于重燃希望,坚定了信念要扎根农村,深悟出他的人生将从这里,从此刻开始!
如果说《人生,将从这里开始》更多的是探讨返乡知识男青年思想上的摇摆,那么李传锋随后创作的《十里盘山路》 (1982)便是还乡青年开始尝试着找到扎根农村的正确路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两个进城后又还乡的农村知识男青年的形象:王有志和王有方。还乡后两人的表现和人生经历很不一样:一个在扎根土地的基础上开动头脑种地,响应改革时代的经济政策,并做出了一定成绩;另外一个一直沉不下心来做实事。这篇小说不同于之前的《人生,将从这里开始》,还乡的知识男青年思想上不再摇摆,在如何扎根建设农村的道路上开疆拓土,并积极响应国家的经济改革,主动融入到变革的洪流中去。
到了《定风章》这篇小说,返乡的知识男青年成功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充分利用经济形势和改革的东风,扎根农村,融入土地,科学种地。《定风章》中进城后又还乡的知识男青年田百枝,他的父亲田福卿是响应经济政策的一把好手。田百枝开辟一块试验田,培育人工天麻,而父亲田福卿却在制作假天麻。当田福卿自己生病需要天麻入药,而儿子高价买回了假天麻的时候,田福卿意识到:“报应,报应!这是报应!”后来,田百枝的人工培育天麻实验终于成功,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决定把这项技术教授给乡亲们,让家家户户都种几窝。同是利用天麻做文章,田百枝和自己的父亲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子。在变革的时代,市场和经济政策的放开,给农村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但由于经验缺乏,各种机制也还不成熟,当大量资本涌入市场时,人很容易失去方向,父亲田福卿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儿子田百枝则一心运用自己的知识科学种田,人工培育天麻再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最终达到了多方利益共享。尽管技术突破的道路不易,但田百枝始终没有放弃对土地的深情和眷恋,要做新时代的知识农民。
在《浮躁》 《古船》 《人生》这些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对于青年们离开农村进城又还乡的书写,作家们有着几乎一致的价值认同:将他们脱离土地进城的行为,看作是打破旧有生产、成长方式,冲破习惯势力的羁绊,以此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还乡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使他们不得已还乡寻找灵魂的栖息。“他们写的是‘交叉地带’,但立足点似乎总离不开农村,无意中以农村的宁静反衬了城市的喧嚣,以农民的纯朴反衬了城里人的狡黠,以传统道德的温情反衬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这种‘对位’法难免会有‘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嫌。”⑤正如有学者论述《人生》中高加林时所说:“他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合法途径,努力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生存空间的跨越,完成由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但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与城市对农村的索取,造成了乡村与都市的隔膜。城市与文明、先进、富裕等有着天然的联系,乡村则与愚昧、保守、贫困落后、信息闭塞等相生共存。”⑥李传锋这一时期创作的乡土小说,就以“土地崇拜”突破了80年代乡土小说的这种叙述陈规。在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还乡的农村知识男青年在返乡之后,经历过思想上的摇摆,也在尝试扎根农村的道路上有过失败,但最终找到了一条既响应时代精神又符合农村自身发展实际的道路。农村可以与城市一起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农民也可以在中国人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的土地上翻出新花样。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也可不以抛弃土地作为代价。“靠种地为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⑦土地对于乡土中国而言,是赖以生存的根基,更是农村乃至乡土中国物质和精神的最终皈依。
“‘改变乡村’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主导形式,但也有一些作家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现代性思考。二三十年代的废名、沈从文,80年代的汪曾祺、李杭育等部分‘寻根’作家,以及90年代的贾平凹、张炜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与‘改变乡村’者完全相反,他们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思维理念是守望,他们对乡村既有现实和文化持肯定和留恋式叙述,对现代文明于乡村的改变持明确的拒绝和批评姿态。……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是以支持和呼应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它的方式也与现代性内涵完全一致——就是改变乡村。……与之相关联,在同样的改变主题下,蕴涵着侧重点有差异的方式和角度:一种以文化改造为中心,另一种则更着力于现实的变革。”⑧以《浮躁》 《古船》 《人生》为代表的大部分80年代乡土小说,对乡村现实进行批判的立场明确,但批判之后如何重建价值理念,作家们往往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农村知识青年的还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表现出来的是向后的退却姿态,是向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作家“脱离了旧的东西,可是还没有新的东西可供他们依附;他们朝着另一种生活体制摸索,而又说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种体制”。⑨李传锋的小说通过书写这种新时代的“土地崇拜”方式,突破了80年代乡土小说的创作陈规,提供了一种进行现实变革,找寻到新的归依的可能性。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不管什么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他们坚定地扎根于乡村,创业于乡村,这是需要理想,需要一种精神的,我看重的就是这种理想,这种精神,我写的也是这种理想和精神。”
二
90年代中期乃至新世纪,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深入,农村开始出现进城打工潮,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留守在乡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文学作品中出现大量农村女性进城的书写。作家毕飞宇说,中国历史与文化有着一个怪圈:“每一场血和泪的呻吟之后,总要挑出两个人来买单——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女人。”⑩李传锋乡土小说中农村青年进城后又还乡的模式发展到此时,呈现出又一崭新的面貌和特质:将着力点放在了农村年轻女性身上,书写这些打工妹进城又还乡的独特生命历程。在这一社会转型期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模式的刻画也不鲜见,比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 (1996) 和《麦河》 (2010)、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2006)等。尽管都是对农村打工妹进城又还乡的呈现,尽管大都把乡村现实的复杂性与人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并且重新唤回对土地的深沉情感,但李传锋《白虎寨》 (2014)中对打工妹们的书写,是在对新型农民心路历程和精神历程的解剖中,展现出农村女性的现代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世人昭示:今日之乡村并非完全是“礼崩乐坏”的藏污纳垢之地,“桃花源”式的理想氛围依然存在,农村现代性价值理念也在逐步构建。李传锋在《白虎寨》中塑造的新型农村女性形象,也是对其早期创作的小说《烟姐儿》 《警官罗立瓯》等的继承演变,通过对农村打工妹进城后又还乡模式的书写,以农村女性现代意识为切入点,突破了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痼疾,也是对“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觉醒的遥相呼应,乃至发展创新。
关仁山在90年代中期创作的《九月还乡》和新世纪创作的《麦河》中,都刻画了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进城后又返乡的人生路径。《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和《麦河》中的桃儿,几乎都美丽、多情又十分勇敢。她们都有进城后做皮肉生意的经历,在洗心革面之后又自始至终都默默地付出,为振兴故土农村的经济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以身体和尊严为代价。“在她(桃儿)身上,我们看到了关仁山早期小说中《九月》这类被城市吞噬的农家女孩的身影,回答了这些堕落了的女孩回乡后怎么办的问题,以及她们能否被拯救,如何拯救的问题。”⑪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从北京还乡时一无所有,但她坚定拒绝了村主任弟弟的求婚,并自作主张大胆地与穷小子旷开田结了婚。她不再延续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是利用土地重新大做文章,开展旅游、食宿生意。暖暖更是出谋划策,多方斡旋,使得丈夫开田当选新一届村主任。暖暖不仅具有一定的现代商业意识,更是将触角伸到了农村权利和治理的方向。这类美丽善良的农村还乡女性,从乡村走进城市,最后又皈依土地,是经由欲望放纵到自尊自强的新型女性农民形象,她们具有人类很多美好的品质。在中国改革开发渐趋深化的变革的时代,她们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作用,又是城乡发展内在机制的必然演化。但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形象,最大的局限在于,对于她们的刻画,作者依旧没有摆脱女性形象塑造的窠臼,她们只是乡村建设主力军——男性的附属品,尚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人格,更遑论现代女性的独立思想。尽管在《湖光山色》中,楚暖暖这一形象闪现出现代意识的亮点,但作者又陷入了另一重迷雾,即将暖暖刻画成了完美、高大的“大地圣母般”的形象:聪明、美丽、善良、无私奉献、重情重义、朴素纯洁并且心存高远。周大新曾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罪恶和苦难都是男人制造出来的”,因此,他“想把温暖的、深情的颂歌唱给女人。”⑫他笔下的楚暖暖几乎完全合乎中国传统伦理对女性的要求,乡村道德完美地展示在她身上,甚至还把乡村智慧的所有“法力”都集中在她身上,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神性光辉的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会使人生出敬佩之情,但又缺乏人气,烟火气,更缺乏现代性特质。
李传锋在《白虎寨》 (2014)中,刻画了进城后又还乡的打工妹群像:幺妹子、春花、秋月、荞麦。受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波及,工厂被迫停工,打工妹们陆续还乡。以幺妹子为首的打工妹们在感受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之后,对家乡贫困、落后、封闭的现状十分痛心,对村里公路不通、手机没信号、夜晚无电的现实感到诸多不便,也对村里脏乱差的恶劣生活环境极不适应。这里看似是将乡村处理为现代化建设的遗留地,但实际是幺妹子们扎根乡村的现实诉求和情感渊源。最终幺妹子和打工妹们决定留在白虎寨继续为乡亲们打拼,这样的处理方式,是试图探讨乡村权利建设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秋月就曾说,“幺妹子姐会当官,开始当我们的领班,后来当上了线长,再后来当上了经理助理”。领班制作为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具体呈现,在城市的打工生涯,为幺妹子在乡村大展拳脚奠定了基础。幺妹子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深谙乡村现实的父辈们的帮衬下,在乡里、县里领导的支持下,依靠国家的惠农政策等多方力量的合力,开始放手大干起来。幺妹子认识到知识对于农村变革的重要性,带领一帮姐妹们巧妙使用计策,将省里下派到别村的农艺师抢到了白虎寨。这样的见识和魄力就很鲜明地将幺妹子与传统农村女性区分开来。紧接着白虎寨通了电,建了通讯铁塔,更是打通了天堑敲梆岩,修通了公路。电、通讯网络、公路,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以幺妹子为首的打工妹们将新的建设家乡的理念,和崭新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带到了古老的白虎寨。村民们更是利用白虎寨丰富的自然资源招商引资,依靠科技建立魔芋生产基地,进而开办精粉加工厂,开寮叶公司等。她们紧跟时代的步伐,利用互联网线上销售农产品,成为当前农村改革的生力军。昔日武陵山深处的世外桃源白虎寨,如今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与传统基层干部相比,幺妹子尽管有时对农村的现实估计不足,但在她身上体现出了现代素质和文化品格,南方打工多年的经历更是锻炼出极强的适应能力。这群打工妹们在白虎寨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体现着农村青年们的魄力和锐气,更展示了富有开拓的智慧和现代意识。正如有学者所言:“幺妹子还具有新一代农民的现代意识。改革开放中的新兴都市的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不仅开阔了她的视野,也注入了这一代新农民的新观念、新思维。”⑬幺妹子的现代意识不仅体现在工作上,她对自己婚姻的想法也有深刻体现。技术员向思明认为农家汉金大谷配不上幺妹子,幺妹子却说:“婚姻有点像合伙做生意,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事业型的人,有能力、有知识,下派几年,回去还得升官,所以,得有人为你作牺牲,你如果想找一个事业型的女人,想比翼齐飞,结果是互不相让,那你的事业也就完了。”⑭幺妹子很明确地说明她是事业型的女人,不适合与同为事业型的向思明在一起,她“想找一个拿工资的男人,可是,幺妹子觉得自己也不会做那种贤妻良母,更不愿意吊在男人的腰带上过一生。”幺妹子渴望婚姻和家庭,但不愿依附男性而活;她为了白虎寨倾尽所有,但她不是一味奉献、牺牲的“大地圣母”。李传锋对农村知识女性还乡后的书写,是自身创作的内在机制的发展演变,也是紧跟农村现实变化脚步的创造性书写。
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乡村权力,是叙述中国乡村现实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批判之后更应该思考如何变革和重建。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在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或者对农耕文明顶礼膜拜,沉湎于‘田园牧歌’的浪漫抒写,以传统价值观念来批判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恶’,或者以现代价值观念批判传统农耕文明中那些落后因素。他们迷惘地游移在两种社会形态和两种价值观念体系之间,对‘新’的与‘旧’的都有一种迎拒之情,如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秦腔》等都沉陷在价值观念的错位与困窘之中,这使他们在价值重建中难有新的发现和创造。”⑮乡村如何进行现代价值的重建,是摆在作家们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面前的现实问题。尽管《白虎寨》体现出来的乡村价值理念的重建有些理想化,但“作家摈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整体上认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整合各种思想资源,通过对一系列充满正能量人物的塑造,试图重建一种价值理想,并以此烛照生活”。这种有益的尝试,就是通过农村知识女青年返乡后的生活、事业体验来展现。李传锋在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打工妹们身上,寄寓了深沉的情感和希望。“我退休后写《白虎寨》,和三十年前写《烟姐儿》,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幺妹子、春花等应该是烟姐儿的子女一辈,中国社会转型已今非昔比。”李传锋80年代创作的《烟姐儿》也是反映在变革时代,女性如何站出来,迈出尝试变革的第一步,但由于时代语境的不同,烟姐儿们的大胆改革仅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到了当下,烟姐儿们的子女幺妹子们成长了起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由此可见,李传锋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刻画并不是空降而来,是文学创作倾向一以贯之的当代新解读。他自己也曾明确表示:“我不知道我笔下的女性是否成功,是否写出了她们身上新的精神因素,新的思想和情怀,但我爱她们。写女性并非我刻意为之,可能是生活的引导。我的父亲是一个勤苦的老实人,我的母亲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妇女,为了养活八个孩子,父母含辛茹苦在贫困的泥沼中拚命挣扎……在我的印象中,女人比男人重要,女人比男人能干……我写作时,她们的所作所为,她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争相进入我的故事,因为她们就是故事的主角,我不能不写她们。”
正如西蒙·波娃所说:“女人第一件要做的是在痛苦和骄傲中去放弃传统。”⑯李传锋笔下的幺妹子们,放弃了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约,在变革的时代中,勇敢地走到时代前列,她们不依附男性而活,不做一味付出的“大地圣母”,她们作为鲜活的独立“人”而存在,作为树的形象顽强站立着,甚至深入到农村权力体系和治理危机的破除之中。这样的现代意识,这种独立的思想精神与“五四”作家笔下的女性们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五四”作家们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多是从女性自身的情感、生命欲望出发,刚刚萌发对精神独立的追求,希冀寻找到女性存在的意义,从而树立起自我价值。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一改以前女性蒙昧的状态,具有一定的精神独立的进步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虽然己经开始觉醒,有了足够的勇气走出传统礼教家庭,甚至付诸实践,但结果并不那么美好,因为她们尚缺乏足够的心理、物质准备,来面对真正独立的人生。李传锋笔下幺妹子们的返乡,首先是国家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给她提供了这种可能,其次是她们本身挣脱了对土地的依附,掌握了自身命运,参与甚至主导着乡村的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她们真正做到了走出家庭,并有自己赖以存活的事业,甚至更进一步,是为了全村人的幸福在打拼,建设新型农村,试图破除转型期农村的治理危机。李传锋笔下进城后又还乡的知识女青年,承继“五四”以来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探索,并依据变革时代的特殊背景,创造性地发展了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对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刻画的一个重要突破。
注释:
①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页。
② 周政保:《〈浮躁〉: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小说评论》1987年第8期。
③ 李春:《论抱朴及见素形象看人生苦难历程》,《前沿》2009年第9期。
④ 周新民:《〈人生〉与“80年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⑤李先锋:《同一种情感倾向所产生的巧合——试析几部小说关于农村青年进城的处理》,《小说评论》1988年第8期。
⑥ 崔莉莉:《“城乡二元对立”下的〈人生〉写作》,《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⑧ 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⑨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⑩ 毕飞宇:《〈平原〉让我踏实》,《金陵晚报》2005年9月22日。
⑪吴义勤:《新乡土史诗的建构——评关仁山长篇新作〈麦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
⑫李丹宇:《让世界充满温情和美好——作家周大新访谈》,《黄河》2007年第1期。
⑬江少川:《土家儿女的白虎梦——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时代画卷》,《小说林中的动物——李传锋小说研究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页。
⑭ 李传锋:《白虎寨》,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页。
⑮丁帆:《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⑯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