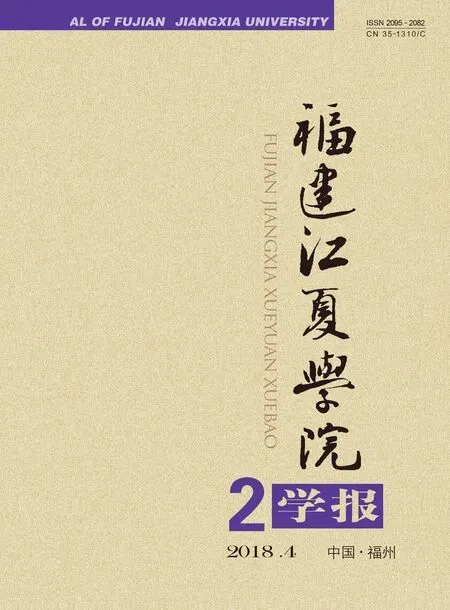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为刘勰“树德建言”的子书
魏伯河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国学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31)
刘勰(约465—520)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巅峰之作。此书的问世,属于魏晋以来文学逐步自觉的时代产物,但这只是后人尤其是今人的认识,与刘勰的初衷并不一致且相距甚远。如果用陈寅恪(1890—1969)先生“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细读《序志》,兼顾全书,进入刘勰的语境乃至心境,深入体察“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1],就会发现,刘勰的本意其实是要写一部子书。而且他的《文心雕龙》,从内容到体例,也完全符合子书的要求。前贤今人论著对此已有所涉及,但大多点到为止,未能引起重视和进一步探讨。而这一点,对全面认识刘勰其人和《文心雕龙》其书事关重大,决非无关宏旨,故而尚有进一步申论之必要。
一、刘勰的本意是写一部子书
在《序志》中,刘勰对《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和选题、定体的过程,本来都有比较明确的交代。如能细读原文,总体把握,还是不难进窥其独特“用心”的。要之,就本书的作意即写作动机而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并非要写作一部《文章作法》之类的实用读本(与其抱负不符),也不是要写一部《文学概论》之类的学科专著(因为那时还没有此类观念),而是要写一部通过“论文”来“述道见志”进而“树德建言”的书。他之所谓“文”,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是以“圣贤书辞”为代表的所有“文章”,其范围接近于整个的学术文化。他写作这部书,不是来自任何机构或个人的委托或要求,纯属“自选课题”,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而其“所为”,他说得很明确,就是要“树德建言”。
刘勰在《序志篇》里写道:
夫宇宙绵邈, 黎献纷杂; 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 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我们知道,刘勰写作此书时,年逾而立,血气方刚,既有岁月飘忽、时不我待之急切,又有睥睨天下、目无余子之自负。但是,在特别讲究出身门第的中古时代,他作为庶族士子,不可能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而且由于少孤家贫,成为一介布衣,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上升之阶。孑然一身、两手空空的他,仅有的资本,就是胸中的志向和才学;其可以发抒之地,只剩下了著书立说一途。通览全书可以发现,除了这里所说的“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之外,在《程器篇》里,他曾宣称:“君子藏器,待時而动。”而在《诸子篇》的赞里,他则这样写道:“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刘勰显然是以“君子”“丈夫”自任的,他决不甘心于平庸:既然通过长期的苦学,自己已经“怀宝”“藏器”,当然应该“待时而动”,力争早日“挺秀”于世。他自信有“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的能力,按照“立德何隐?含道必授”的信念,他决心要写作一部书——一部“条流殊述,若有区囿”、不同凡响、可以让他一鸣惊人的大书,借以引起时人乃至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和青睐,进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写作,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为情而造文”,属于“发愤著书”,而决非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
但是写什么题材的书呢?按他长期形成的尊圣、崇儒观念,还有“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的梦境的启示,他认为著书立说应该以“敷赞圣旨”为正道,而“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可是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因为“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自幼浸润其中,且自认为颇有造诣的“文章”:“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这样看来,写一部“论文”的著作,也是可以“敷赞圣旨”“树德建言”的!联想到当时文坛的种种弊端,他愈发感到应该写作这样一部书。而凭借这样一部书,也足以实现其“立家”(即自成一家)的心愿。
可是,专门“论文”的著作,自魏晋以来,已经有不少了。如刘勰所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既然如此,还有必要进行新的创作吗?通过“论文”还能够实现“立家”的目的吗?但刘勰审视后很快发现:前人的这些著作,“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他认为,前人的这些论著,固然开辟了“论文”的道路,成为可资利用的材料;但他们的种种不足,留下的巨大空间,恰恰是自己的用武之地。尤其是上述论著,大都“适辨一理”,不能“博明万事”;往往“诠序一文”,而不能“弥纶群言”。从内容说,都是就文谈文的(“不述先哲之诰”);从体制说,都缺乏宏大的规模和气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从效果说,都是不能挽救文坛颓风的(“无益后生之虑”)。自己要写的这部书,应该超越他们、后来居上,写成一部以“论文”为主要内容,但能上承道—圣—经(即“镕铸经典”“敷赞圣旨”)、下涉每一种文体、每一家学术和写作中每一个重大问题(即“条流殊述”“弥纶群言”)的书,来集其大成。这样的一部书,一定能远迈前贤,轰动当世,悬诸日月,炳耀千秋!
选题确定之后,就要考虑作品体类选择,即写成一部怎样的书的问题。刘勰对所有各种文体素有研究。在各类文体中,他显然觉得只有子书才能和他如此宏大的愿望和重大的题材相适应。请看《诸子》篇里,刘勰对子书的总体认识:
诸子者,述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
现在看来,这样的表述,既是对子书重要地位的标举,又何尝不是他写作目的的自然流露?他显然是认为,只有子书才能容纳作者丰富的思想,会通学术之道,显示作者的“英才特达”,也因而与自己的初衷吻合。尽管过去那些子书的作者有不少“身与时舛”,当时并未受到重用或尊崇,但因为“志共道申”,通过其著作实现了“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所以仍然能“名逾金石之坚”(“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决定把自己“论文”的著作写成一部足以“立家”的子书,并且按照子书的要求精心设计了《文心雕龙》全书的格局。
对刘勰的这番用意,清代以来不止一位学者已有所觉察和揭示。如清人纪昀(1724—1805)在《诸子篇》“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处加有批语云:“隐然自寓。”[2]114尽管纪昀在主编《四库全书》时仍把《文心雕龙》归入集部之“诗文评”类,但这条批语却足以证明他体察到了刘勰的初衷。晚清词人谭献(1832—1901)在其《复堂日记》中则明确判定:“彦和著书,自成一子:上篇廿五,昭晰群言;下篇廿五,发挥众妙。”[3]刘咸炘(1896—1932)进一步指出:“彦和此篇,意笼百家,体实一子。故寄怀金石,欲振颓风。后世列诸诗文评,与宋明杂说为伍,非其意也。”[2]115刘永济(1887—1966)也认为:“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同矣。彦和之作此书,既以子书自许,凡子书皆有其对于时政、世风之批评,皆可见作者本人之学术思想,故彦和此书亦有匡救时弊之意。”[4]1程千帆(1913—2000)在《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心雕龙》一书可以说是刘勰的子书。……足以上追《吕氏春秋》,下启《文史通义》”[5]的观点。台湾学者王更生(1928—2010)认为:“因为朝于斯,夕于斯,反复揣摩,愈觉得《文心雕龙》乃‘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6]今人如周勋初(1929—)先生也明确指出:“他(刘勰)要写作《文心雕龙》,藉以‘树德建言’,并由此而‘立家’,可知他的写作《文心雕龙》,是想完成一部子书。”[7]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万奇(1964—)也认为:“就彦和写作的深层动因来看,他想把《文心雕龙》写成一部‘子书’。”[8]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游志诚教授则指出:“盖刘勰文心之作,乃刘勰以‘子家自居’之志,畅论‘为文之用心’。”[9]诸家所说,是符合《文心雕龙》实际,也是深得刘勰“为文之用心”的。可惜均属点到为止,未予畅论,因而未能引起学界重视。学界对刘勰其人其书总体把握上,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种种偏差。本文对刘勰写作动机和选材、定体过程的梳理还原,其针对性即在于此。
现在的不少人对《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的观点之所以难以接受,甚至视为奇谈怪论,应该和以下因素有关:其一,历来诸子都被视为哲学思想类著作,其中还没有过专门“论文”的品种;其二,历来的目录学著作大都将其作为诗文评附于集部;其三,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将此书定性为“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尤其在我们今天看来,一部好的文学理论书,价值决不低于一部子书。因而许多人认为,辨别刘勰是否想写成一部子书,《文心雕龙》是否算一部子书,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殊不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子书与诗文评(当时没有文学理论之类概念,在四库分类中,有关著作均归入“诗文评”,附于集部之末)二者的地位却是大有区别的。
在我国古人的心目中,纯粹的文人(即今天所说的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属于“有文无质”“雕而不器”(《程器》)者,历来是不被看重的,即便侥幸进入了宫廷里面成为皇帝侍从,也只能被“俳优蓄之”,故有所谓士子“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说。至于也有许多文士显身当时、扬名后世,往往是由于他们立有“一家之言”(即子书),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由于其文学创作的成就。他们的学说,有的在当世即大行其道,实现了“奉时以骋绩”,在政事上有所作为;否则亦可“独善以垂文”,赢得身后名声。这样的人,才得以享有“梓材”或“桢干之士”的美誉。而成为那样的人才,恰恰是以“君子”“丈夫”自命的刘勰的理想。而如果将其视为“有文无质”“雕而不器”的纯文人,把他精心制作的《文心雕龙》视为单纯的文论,对刘勰来说,则不啻是一种侮辱!这样的感受,如果不深入其语境乃至心境,是很难体会的。刘永济先生在《程器篇》的校释中说:“全篇文意,特为激昂,知舍人寄慨遥深,所谓发愤而作者也。乃后世视其书与文评诗话等类,使九原可作,其愤慨又当何如邪!”[4]188时隔千载,刘勰终于有了知音。
认为纯文学作品与子书相比地位悬殊这样的观念,属于古人长期以来的共识,也早已体现于魏晋以来的图书分类中。子书虽不能与经书相提并论,但一直是一个单独的部类,不仅一直高于集部,还曾一度高于史部。①据《隋书·经籍志》,西晋秘书监荀勖开始对图书以四部别之,甲部包括六艺、小学等;乙部包括诸子百家、兵书、数术等;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等。至东晋秘书郎李充,则调整了乙、丙两部的次序;至魏征等修《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代替甲乙丙丁四部之名。此后长期沿用,至清代修《四库全书》而集其大成。而单纯论“文”的著作,从来都是被归入诗文评,附于以辞赋为主体的集部之末,其不被重视,自不待言。了解了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可以知道,刘勰是决不甘心自己用以“树德建言”的著作被作为“文论”或“诗文评”附于集部之末的。
二、《文心雕龙》符合子书的标准
那么,刘勰写成了一部子书没有呢?按照他所论述的子书标准加以检视,可以发现,《文心雕龙》是具备了子书的基本特征的。
第一,刘勰认为,“诸子者,述道见志之书”。《文心雕龙》以“道—圣—经”为“文之枢纽”,以《原道》开篇,以“宗经”思想贯穿全书,显然是符合“述道”要求的。他认为,前代子书“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而他的《文心雕龙》以宗经为旗帜,力倡“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丈夫学文”必须“达于政事”(《程器》),写作任何文体都必须“进有契于成务”(《论说》),都是在“论文”的同时也在“言治”的。至于“见志”,全书及其各篇均主旨鲜明,许多观点在当时属于独到见解,不同流俗,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刘勰在行文中,议论风发,笔端常带感情,作为庶族士子的“孤愤”常于行文中不经意间宣泄出来,其人生观点和个人情志鲜明地散见于全书各处。说明此书也是符合“见志”要求的。他评论前人子书,衡以儒家经典,认为“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诸子》)。所以他坚持摒弃“怪力乱神”等不经之谈,明显是以子书中的“纯粹者”自居的。
第二,刘勰认为,子书在体例上应该是“条流殊述,若分区囿”的,为此他对全书的结构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安排。他按照“大易之数”,确定全书正文为四十九篇;加上最后的《序志》,全书正好五十篇。其中,为了突出“宗经”的主张,他特别设计了前五篇“文之枢纽”。针对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的弊端,他在上篇以二十篇的篇幅畅论各种文体,借以规范文章“体式”;为了解决写作中的种种问题,他在下篇用了二十四篇的篇幅从多个方面分别予以深入的探讨。从而完美地实现了“条流殊述,若分区囿”的追求。
第三,他认为子书与论文不同。在《诸子篇》里,他专门对子书和论文作了这样的辨别:“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刘勰写作的这部书,规模宏大,自然是不限于“适辨一理”,而是要“博明万事”,借以“述道见志”的。但“博明万事”应以“适辨一理”为基础。所以读者分览《文心雕龙》各篇,无不“适辨一理”;合观全书,则能“博明万事”。他的《原道》从天文、地文讲到人文,从伏羲讲到孔子,强调圣人经典“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的巨大功能;而他的“论文”,固然是以“文”为论述对象,但并非就文论文;而且他之所谓“文”,是镕铸经典、会通子史的,范围广阔,已经接近于整个的文化学术。所以,他才会有“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的宏大期许。
第四,刘勰在《诸子篇》里,评论了历代子书的得失,实则为自己的著作树立了最高的标准。他要兼取各家之长,“得百氏之华采”“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写出一部空前的子书类著作来。这一方面表现在,前人子书从无专门“论文”,《文心雕龙》以“论文”为使命,属于和六国之前的诸子一样,是“自开户牖”的,有填补空白之功,而无两汉以后诸子的“类多依采”之弊;另一方面,他的这部书不仅文士们读后可以得“为文之用心”,而且由于其“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程器》),从政者乃至治国者都可以从中受益。我们还应该看到,刘勰对前代诸子之书内容上、行文中的各种弊端,都在本书写作中有意进行了规避。例如,对陆贾《典语》、贾谊《新书》之类“蔓延杂说”的缺点,就进行了矫正。他的“论文”,“体大虑周”,紧紧围绕着中心展开,不枝不蔓,后出转精,在体制上达到了空前的完美。
有人反对《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的观点,认为:“仔细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刘勰倾向于将《文心雕龙》归为‘论’体,同时他又赋予它以独特的‘论’体特征, 即它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的。这一定义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论’,也有别于战国、两汉时期的子书。”[10]此说似是而非,有以偏概全之弊。刘勰明言:“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说》)。《序志》里也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视《文心雕龙》各篇,可以发现他正是致力于此。如此说来,认为“刘勰倾向于将《文心雕龙》归为‘论’体”,似乎是有根据的。但论者知其一未知其二,即按照古人的书籍分类,若干篇各自独立、斐然成章的“论”,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就不再是“论”,而已成为“子”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诸子篇》里,前代不少以“论”为名的书,如王符(约85—163)《潜夫论》、崔寔(约103—170)《政论》等,也被刘勰归入了子书之列。诚如论者所说,《文心雕龙》当然“有别于战国、两汉时期的子书”,但它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论’”,何以就只能是“论”而不能是“子”呢?
三、认定《文心雕龙》为子书的现实意义
那么,在当今时代,确认《文心雕龙》是刘勰“树德建言”的子书有何意义呢?笔者以为,其现实意义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揭示刘勰的初衷本来是要写成一部子书,而且分析认定《文心雕龙》符合子书的主要特征,对全面准确地认识刘勰其人是很有意义的。刘勰不满足于仅做“文”的评论者,更不甘于做“有文无质”的文人。他重文而不轻武,笃学而谙政事,强烈希望能在社会事业上有所作为,是一位志向远大、学富才高的优秀人才。他后来“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梁书·刘勰传》),不过是牛刀小试。可惜历史没有给他更多更好的施展机会,使他未能“奉时以骋绩”,其命运只能朝着由文人而僧人的轨迹滑行。但是他因为著有《文心雕龙》,实现了声名的不朽,则可以算是“独善以垂文”了。至于20世纪以来,他被后人尊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论家,声名远播海内外,其影响甚至超过许多帝王将相,则决非刘勰当时所能想象,只能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有的文学传记之所以把刘勰写成了几乎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正是由于在对刘勰形象的总体把握上出现了大的偏差。
其次,确认刘勰的初衷是要写一部子书,根本目的在于“树德建言”,借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和地位,对把握全书的主旨也极有必要。应该看到,与这一根本目的相比,他在书中一再申明的“矫讹反浅”,从写作目的来说,其实是第二位的。只是由于著书立说必须有破有立,种种文坛弊端因之被他作为纠弹的对象,屡屡言及,似乎成了直接目的。但究其实,他对文坛弊端的批评不过是借以“树德建言”的材料和工具而已,直接目的还是服务于根本目的的。对此如有总体的把握,则书中若干看似自相矛盾之处就可以豁然贯通。例如,多年以来,人们受纪昀评语的影响,把“齐梁文藻,日竞雕华”认作刘勰此书反对的主要对象;对书中关于文章形式美的大量研究和论述,认为是其“自相矛盾”,已经是很大的误解。至于由此进一步认为刘勰是在“标自然以为宗”,乃至把所谓“自然之道”作为刘勰所原之“道”,则误解更甚。②笔者有《走出“自然之道”的误区——读<文心雕龙·原道>札记》一文对此专门予以研讨,见《中国文论》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这些都是后人用唐代以来古文家的眼光以今律古,而且没有认识到《文心雕龙》是刘勰的子书的产物,与刘勰本意则相去甚远。刘勰对当时文坛的现状,当然颇为不满,但他的矛头所向,并非“雕华”,因为他是笃信“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的。所谓“雕华”,其实不正是“雕缛”吗?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文学观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意见并无根本的不同。所以,《文心雕龙》才能被当时的文坛宗主沈约(441—513)阅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刘勰所反对的,乃如《序志》中所说,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其中的关键词,一是“文体解散”,即不符合文体要求的作品大量涌现;二是“离本弥甚”,即背弃了儒家历来倡导的文章写作经世致用的根本目的。正因如此,他采用大量的篇幅,畅论各种文体;并以原道—征圣—宗经作为论文纲领,力图返本开新。[11]
至于《文心雕龙》一书长期以来在图书著录中主要还是被视为诗文评,列入集部(亦有个别置于子部或史部者),到了现代更被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章作法之类的专著,很少有人将其作为子书看待,自有其时代的、客观的原因。这些认识,固然与刘勰的初衷不合,但在笔者看来,却无须一定视之为“错误”。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古代典籍,现代的许多学科和不同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有所取资。就像刘勰《辨骚篇》里讲的后人对《楚辞》作品一样,“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作为一部以“论文”为内容的重要古籍,今人在研究中国文论或古代作家作品时给予高度重视,更属理所当然,事出必然,无可非议。要之,刘勰想写成一部什么书、他最后写成了一部什么书、历史上别人把它看作什么书、我们现在把它看作什么书以及作何用途,这些方面是不应该也不必要强求一致的。不止是《文心雕龙》,即如同样的几部儒家经典,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就有过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当今学者也是言人人殊,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在众说纷纭和无数次的争执辩难中,学术才得以发展;而某一权威自认为得了独家之秘、排斥各种异端的做法,却往往扼杀了学术的生命。适如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1945—)所说:“不存在什么人,被人理解一次,就能被人永远理解;没有什么高级的书,翻译一次,就永远不需要再翻译。我们需要不同的解释和译本,因为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变化,我们反思的对象也随着我们在变化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最终和真实的理解或翻译,有的只是瞬间的理解和翻译。”[12]此说虽有相对主义之嫌,但却有助于帮助人们从这样那样的牛角尖里解脱出来。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79.
[2]刘勰.文心雕龙[M].戚良德,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5.
[4]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12册)[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97-98.
[6]王更生.文心雕龙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133.
[7]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03.
[8]万奇.《文心雕龙》之书名、框架和性质今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01-105.
[9]游志诚.政事乎?文学乎?——《文心雕龙·议对》细读[C]//中国文论(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34.
[10]凌川.《文心雕龙·序志篇》新探[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49-51.
[11]魏伯河.《文心雕龙》书名命意之我见[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3):7-10.
[12][德]沃尔夫冈·顾彬.误读的正面意义[J].王祖泽,译.文史哲,2005(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