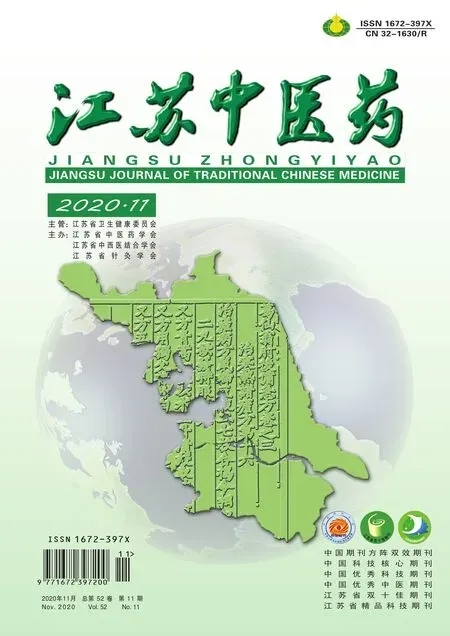王雨三《治病法轨》学术思想探颐
王明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金华医院,浙江金华321000)
王雨三(1877—1945),字汝霖,江苏太仓人,业本务农,初非习医。方在弱冠,一家颠沛,五年之间,继以离世者五人,皆由小病迁延,终至不起。后自病噎膈,延医服药,不愈反剧。感而发愤,自购医书,翻阅古方,服之而愈。始察从前一家之性命,皆由庸医治不得法而枉死。愤而砥砺,潜心岐黄,自内难以下,以至《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及仲景、河间、东垣、丹溪等诸家之书,穷经皓首,孜孜以求,寒暑不辍,甚则寝食俱废。后心领神会,得其奥旨,借以治病,效验如神,求诊者接踵。
《治病法轨》为王雨三毕生经验集萃,该书总分三卷。上卷详辨阴阳、气血、表里、虚实,着重阐述脉法,主张以脉理辨别病机,认为脉理为医者至切至要之法,不明脉理者,无以言治病;中卷论及临床疑难变幻之奇症、险症及其治验,多为他医屡治不效,转而求治获效者;下卷则言各科证治扼要,皆为王氏积数十年经验反复求证、独出心裁之作,非人云亦云、尚事空谈者可比。全书脉络清晰,说理晓畅,理法兼备,切中时弊,探幽引微之处,往往令人击节称快。秦伯未先生序中高度评价此书:“无门户之见,无迂远之论,无隐约之词,无浮泛之方。命曰‘法轨’,信副其实。他日与耐寒《付氏三书》,肯堂《证治准绳》并垂不朽,可预卜也。”认真研习此书,于医者而言,每逢临证犹疑、漫无定见之时,或可厘正思路、见病知源。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该书的学术思想,不当之处,望学者斧正[1]。
1 治病求本 贵先识病
王氏言:“凡百病症,不外阴阳、气血、表里、虚实之偏胜而致。”疾病的产生,乃阴阳不相平衡的结果。其以权衡、舟楫为例论之,曰:“权衡平,则无偏倚之患;舟楫平,得免倾覆之虞。”故治病之法,当明辨阴阳、气血、表里之虚实,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协其平。反之,则易犯虚虚实实之戒,病必不愈。故王氏主张:“医者不贵乎识药,务贵乎识病。病情识透,则温凉补泻之药,无不皆起死回生之物。如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必轻病变重,重病致死。医之用药,岂可草草乎哉?!”与喻嘉言“先议病,后议药”之论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2 以脉定证 四诊合参
治病之法,当明辨阴阳、气血、表里之虚实。但如何判定阴阳、气血之虚实,古书并无详载,亦无人能证实其真情,自然也成为困扰王氏内心良久的难题。倘学术不精,见识未明,如遇正虚之病,不知阴阳气血之何虚,阴虚反补其阳,阳虚反补其阴,气虚反补其血,血虚反补其气,南辕北辙,病无愈者。遂精勤日甚,广收博采,后推求脉理,方得其奥,借以治病,无不神验。概括其脉理思想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左手脉以候血之虚实,右手脉以候气之虚实 王氏遍阅古籍,寤寐思求,终于“人迎紧盛伤于风,气口紧盛伤于食”(《内经》)句中悟出:左脉盛即是阴盛,左脉虚即是阴虚;右脉盛即是阳盛,右脉虚即是阳虚;以左右手脉息判别阴阳之盛虚,即是确切不移之至理。又据古人言“左半身属血,右半身属气”,悟出:左手脉以候血之虚实,右手脉以候气之虚实。明此,则凡百病情,了然于指下而无所遁形。这点在众多医家看来可能囿于教条,但笔者认为,这是中医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必然结果。对于前人留下来的遗产,我们不应该盲目否定,而应以尊重、包容而审慎的态度,反复证之于临床实践,方能去伪存真。
2.2 以脉定证,凭脉选方,四诊合参 王氏列数篇阐述脉法的意义,详辨脉形与主病、左右两手脉候用药补泻法、《内经》分配脏腑诊候图等,认为仅凭外部之见症,很难分辨气血之寒热虚实,尤其是在面临难症、奇症、重症、险症之时,如脉理不明,极易误治。因此,确定了以脉定证、凭脉选方的法则。譬如左脉浮弦有力,右脉浮大而散者,是气虚夹风证,宜用消风散除藿朴加芪术治之;右脉洪数有力,左脉浮虚或细弱者,是肺胃火盛耗及精血之证,宜用白虎汤加生熟地治之;两手脉俱浮洪数实者,是表里气血具有风热之证,宜用防风通圣散加减,诸如此类。需强调的是,以脉定证并不是仅凭脉象武断地确定病机、治法,而是在四诊的基础上,参合用之,正如王氏言:“至于四诊,亦须彻底相参,心领神会而用之,庶能应无穷之变。霖之治病,每将左右手之脉息,定气血之虚实。再参以望闻问之见症,而用攻补兼施,或补气以配血,或补血以配气,或气血平补等法。”且谓数十年来,借此以治病,无不应如桴鼓。反观世之医者,不知脉理,不辨虚实,胸无成竹,草草成方,令病日重,无异于催命之鬼。
2.3 脉案治验 中卷论及阴盛格阳、阳盛格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上病治下、下病治下及中风、劳损、鼓胀、噎膈等,并附精彩验案以佐证之。观其治验,识见卓绝,迥于俗医。兹举数例,以概其余:治顾某盗汗如注、卧床不起案,诊其脉左尺脉弦紧异常,断为风寒径入足少阴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桂枝、别直参一汗而愈;治沈氏妻,双目失明数载,屡治不效,诊其脉沉微,左手及两尺尤甚,知为肝肾水火两亏,用附桂八味汤,服十剂,目即明亮如初;治金某子,年约二十,患头痛症,医者不察,误用辛散,且一误再误,致头痛如裂,呼号欲绝,目珠突出寸许,不识人而口不言,危险至极,切其脉浮散且濡,知为肝肾亏极,以大剂地黄饮子,除菖蒲之辛散,加杞子大补肝肾,一剂而神志清,口能言,目珠渐收,三剂平复如初。
3 匡正除邪 顾护元气
宗《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欲泻其邪,先补其虚”之旨,王氏认为“凡病之起,无不皆由元气之虚。虽外感由于天时之不正,实则亦由正气之先虚,不能固御其邪。内伤之证更不必论矣。”揣度仲景麻桂、柴胡剂等应用枣草、人参意及后世参苏饮、再造散、人参败毒散、麻黄人参芍药汤等,皆攻补并施、助正祛邪之剂,非顾此失彼者可比。因此,主张治病当时刻顾护元气,反对一味攻伐,批评时医妄用牛蒡、枳实等泻肺破气,力辟“虚不受补”“补牢其邪”“气有余便是火”“小儿纯阳之体”“急则治其标”等说之非,详析其理,以正其偏,然言有激烈处,皆救世之心殷切使然,学者当明辨。
4 重视温补 师古不泥
王氏用药,重视温补,反对恣用寒凉。兹举其治发热经验而论:内伤之发热,每取法东垣甘温除热法,应手辄效;外感之发热,误服凉表药以致元气虚极之证,以大剂甘温药投之,亦无不应验;即温病之脉浮、发热、口渴,亦用桂枝汤加生地、青蒿以解肌清热,亦无不效者。此感于时医竞尚寒凉,废弃温补,戕伐元气,以致坏证迭起、误人性命,不得以而纠正之,并非偏颇,泥古不化[2]。从其治陈某四肢厥冷、形神疲倦,时医用姜桂,病反增剧,诊其脉,左关沉实滑数,以龙胆泻肝汤加川连、石决明治愈;治张某四肢不收、卧床不起半载,百药不效,诊其脉,左豁大,右沉实且滑,断为火旺血枯、不荣四末,以调胃承气汤加味治之而愈等案中可见一斑。
书中列“论用热度表验病人之寒热”篇,批评时医以热度表验热之轻重而决治法以及见热用凉、见寒用热的做法。因为证有上热下寒、下热上寒、阴盛格阳、阳盛格阴之别,亦有风湿暑燥、劳倦食积、七情六郁之分,同时尚有表里气血、脏腑经络之不同。徒凭温度计,何能分别寒热真假?何能分别脏腑经络?又何能分别在气、在血、在表、在里?况且药有归经之不同,仅凭热度表,又如何选择的当之药?若不能探源知本,投之孟浪,恣用寒凉,不免戕伐无辜、涂炭生灵。这对现今一见体温升高即用冰敷、退热药者,无疑是当头一棒。所以,寒热温凉,不可泥定,必使见病知源,择其适合者用之,方可左右逢源。
王雨三之《治病法轨》,以脉理立言,揭辨证法要,阐幽发微,独出机杼,诚以济世之心,冀能示人以矩,读之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书中的某些言论可能过于激烈,某些论点也有待商榷,但是白璧微瑕,我们应以审慎而宽容的态度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