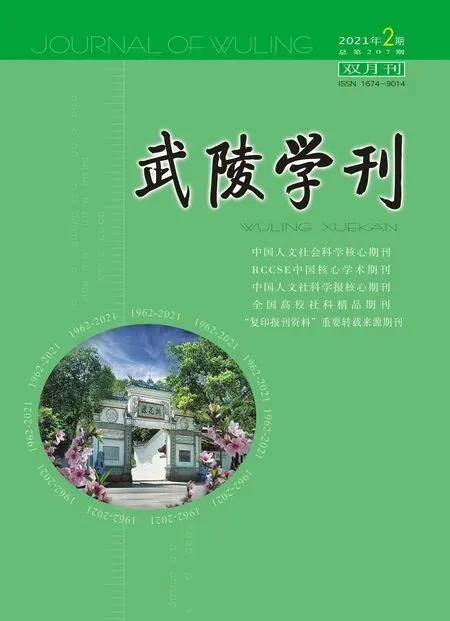《袁氏世范》家庭教育思想探析
张文渊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正如《礼记》记载:“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1]1599-1600在重视家庭教育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献资料——家训。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国人教育孩子最简洁、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教化方式。虽然时代在变化,但家庭在人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习近平希望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2]。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家庭教育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袁氏世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家训文化的经典之作,是由宋代袁采所作。袁采,字君载,宋代衢州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任乐清县令,任职期间,为改善当地的人伦风俗,他撰写了《袁氏世范》一书。该书原名为《俗训》,书成之时,袁氏请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承议郎且代理隆兴军府事通判刘镇(1110—1165 年)为其作序。刘镇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该书“其言则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3]181,并进一步指出“是书也,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3]181,认为该书既可以推广全国,还能流传于后世,于是强烈建议作者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虽有所推辞,但最终还是将之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一经刊发,便备受世人推崇,也引起了近现代西方汉学界重视①。《四库全书提要》这样记载:“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4]书中有关家庭教育的思想,颇具特色,理应继承和弘扬,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
一、教子在幼:最佳的教育时机
中国历来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甚至把育子的时间提前到了胎教。关于胎教,《大戴礼记·保傅》中记载:“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5]汉代的刘向以周文王为例对胎教的重要性作了较为生动的论述,认为文王之所以为文王,与他母亲良好的胎教是分不开的。“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6]明代的《许云邨贻谋》认为胎教需要做到“五宜”:“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止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7]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孩子能否成才与胎教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但科学的胎教对孩子尤其是胎儿的健康成长确实有一定的帮助。
北齐的颜之推在吸收前人有关早教思想之后,提出了“教儿婴孩”的观点。他在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中从两个方面对早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从正面来讲,幼儿时期的孩子可塑性好,“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8]12,这种可塑性就是他说的“使为则为,使止则止”[8]8。除了可塑性好外,幼儿时期的孩子学习效率也最高,“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8]163,并以日光和烛光来比喻少老之间学习效率的差距:“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8]163在颜之推看来,孩提之时,精神专一,其学习能力和效果,如同早上初升的太阳,又快又好;而老年人学习,其效果如夜晚依烛光而行,既慢且差。从反面来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早期的良好教育,一旦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想要再纠正会难上加难,“捶挞至死而无威,仇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于败德”[8]8。因此,必须从小对孩子进行系统的教育,否则就会“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1]1062。
《袁氏世范》在继承《颜氏家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早期教育观。首先,它论述了教育在人成长中的重要性。它指出,人之禀赋天资虽各不相同,“人之德性出于天资者,各有所偏”[3]71,人的性格也各种各样,“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3]5。但天资和性格并不是一个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后天的学习教育才是成功的关键,正所谓“习相远也”[9]175。其次,它论证了早期教育在人的一生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关键。《袁氏世范》认为,幼儿就像一张白纸,白纸可以绘画也可以写字;同理,相对成人来说,幼儿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观念,关键看家长的教育和引导。“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教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所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3]20孩子小时候如受到了父母的良好教育和正确引导,他们长大后就会是一个懂谦让、懂礼貌守规矩的人。反之,如“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无争!少或犯长,而长或陵少,初不训责,何以保其他日不悖”[3]20。孩子长大后之所以喜欢争夺,不尊重长辈,混淆是非,甚至做坏事,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因此,袁氏强调必须重视孩子幼儿时期的教育,从小培养其明辨是非、尊老爱幼、谦让互爱的能力和性格,为孩子日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爱子贵均:公平的教育理念
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0],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也就成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子女众多,管教也就成了难题,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9]170。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诸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父母在管教孩子时不公平所引起的。因此,在多子女家庭,父母如何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既是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重点,也是家庭教育的难点。
《颜氏家训》是较早关注父母应该公平关爱孩子的著作。该书指出,由于家庭中的子女既有“贤俊者”也有“顽鲁者”,这就导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8]18。父母往往会更爱“贤俊者”而忽视“顽鲁者”,对前者愿意付出更多的心血,对后者有时可能不管不问。颜之推主张无论孩子是聪明乖巧还是愚钝调皮,父母都应该公平对待,不然就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自古及今,此弊多矣”[8]18。子女之间不和是父母偏私管教最易引起的一个不良后果,“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虐妇,则姊妹之馋行焉”[8]49,子女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到整个家族成员间关系,所谓“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8]26。在这种情况下,家道必然衰败,且无重整家道的可能,因为“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8]26。
《袁氏世范》中明确指出,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必须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一视同仁,不能有偏私,“人有数子,饮食、衣服之爱不可不均一”[3]20。在袁氏看来,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就好比士卒与将帅、下属与上司、奴仆婢女与雇主的关系,“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3]10,所以父母应当像将帅、领导、老板一样,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不能有所偏爱。对于现实生活中父母不公平对待孩子的情形,袁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是爱幼憎长。“同母之子而长者或为父母所憎,幼者或为父母所爱”[3]23。关于父母为什么会爱幼憎长,袁采认为可能与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的生理特征有很大的关系,他说:“盖人生一二岁,举动笑语自得人怜,虽他人犹爱之,况父母乎?”[3]23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讲,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天真呆萌,人见人爱,何况孩子的父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生理特征也有所变化:“才三四岁至五六岁,恣性啼号,多端乖劣,或损动器用,冒犯危险,凡举动言语皆人之所恶。又多痴顽,不受训诫,故虽父母亦深恶之。”[3]23三岁至六岁的小孩子调皮捣蛋,不太招人喜欢,有时还会惹父母生气,故父母会憎长爱幼。至于在孩子已成年的情况下,父母为什么还会憎长爱幼?《袁氏世范》认为那是因为父母已经养成了习惯,就算幼子过了天真可爱的年龄,相比其他孩子而言,父母还是会更爱自己的幼子,“方其长者可恶之时,正值幼者可爱之日,父母移其爱长者之心而更爱幼者,其憎爱之心从此而分,遂成迤逦。最幼者当可恶之时,下无可爱之者,父母爱无所移,遂终爱之,其势或如此”[3]23。第二是念贫忘富。该书指出,在一个家庭里,父母一般比较宠爱穷困一点的孩子,这是父母为了防止孩子之间贫困悬殊过大而采取的措施,“父母见诸子中有独贫者,往往念之,常加怜恤,饮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献,则转以与之”[3]21,但较富裕孩子却认为这样做不公平,进而产生怨恨,“子之富者或以为怨”[3]21。对于这种情况,袁采认为这是“子之富者”没有换位思考所致,“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贫,父母必移此心于我矣”[3]21。如果“子之富者”站在“子之穷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会认为父母是“均一之心”[3]21。
袁采对“念贫忘富”的作法是否合理的论述有待进一步讨论,但他对父母偏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的论述有一定道理。他指出,偏私对待子女的第一个不良后果是易引起家庭矛盾,“人之兄弟不和”,“或由于父母憎爱之偏,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3]21,“贤者或见恶,而不肖者或见爱,初不允当,何以保其他日不为恶”[3]20。在不公平的家庭环境中生活,被宠爱的小孩会变得日益骄横,目无他人;不被待见的子女则忿忿不平,久而久之,孩子之间便产生了仇恨。第二个不良后果是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因为偏私对待孩子,会“使长者怀怨而幼者纵欲”[3]23,使“爱者意气日横,憎者心不能平”[3]21,这种情况长时间发展下去,孩子的身心健康必然会受到影响,成为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家道衰败是为第三个不良后果。在《袁氏世范》看来,偏宠会导致子女之间不和谐、不团结,进而引起孩子之间的怨恨,最终“以至破家”[3]23。因此,他主张天下的父母都应该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子女,“苟父母均其所爱,兄弟自相和睦,可以两全,岂不甚善”[3]21。 父母均爱,子女之间“长者总持大纲,幼者分干细务,长必幼谋,幼必长听,各尽公心,自然无争”[3]26。孩子之间没有矛盾,家庭就会团结,没有争吵,“既无争讼”,最终使家道“必至兴隆”[3]29。《袁氏世范》在公平对待子女的问题上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主张立遗嘱也须公平。财产继承是家庭伦理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处理不当会引起很多家庭问题,因财产问题而导致“兴讼破家者”“不可胜数”[3]61。因此该书指出,立遗嘱是有智慧有远见的人为避免子孙在继承财产时出现矛盾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即“遗嘱之文,皆贤明之人为身后之虑”[3]61。同时它还强调立遗嘱必须公平,因为“亦须公平,乃可以保家”[3]61。
三、 严慈互补:中庸式的教育方式
“严慈互补”是指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既不能过分溺爱孩子,即无原则地满足孩子的各种无理要求,也不能对孩子过于严厉进而缺少该有的血缘亲情,而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走极端,在严与慈中寻找平衡点。
中国古代有不少主张“严慈互补”教育方式的思想家,但最早作系统论述的是北齐颜之推。他认为,教育孩子首先要有慈爱之心,没有慈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伦理亲情就无法确立,“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8]14;但如果只是慈爱而缺少严厉的教育,其后果则是孩子成了不孝子孙,正如他所说:“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8]39同时颜之推还指出,由于舐犊之情的缘故,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虽然知道应采取严厉的教育方式,但终因溺爱之故而施之过宽,“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8]12。针对这样的家长,颜之推认为,教育孩子就好比治疗疾病,必须对症下药。有些疾病只需调理就行,有些疾病则必须忍受汤药之苦针艾之痛才能治愈。“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8]12教育孩子也是一样,有时通过说理的方式,有时则必须得采取严厉手段才有效果。他进一步指出,对孩子严厉并不是父母憎恨自己的孩子,虐待他们,“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8]12,而是“诚不得已也”。所以,颜之推认为正确教育孩子的方式必须严慈互补,“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8]8。
《袁氏世范》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严慈互补的教育思想。它首先指出,人世间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最深也最亲,“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3]8。既然父子兄弟之间最亲,因此就得相互关爱,所谓“父慈爱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3]8。作为父母就应该多反思自己有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要学会换位思考,“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子”[3]7。同时,父母的一言一行,孩子既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并以此为榜样作为自己今后教育孩子的标准,“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吾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3]7。其次,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对其进行鼓励,因为父母的欣赏是对孩子最大的关爱。袁氏认为,赞美优点是对孩子的爱,合理地包容孩子的不足也是对孩子的爱。父母不能因为孩子有过错而过分地指责,进而疏远他们,因为每个孩子都有缺点,故“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3]8,要多看看自己孩子的长处与优点。
《袁氏世范》提倡关爱孩子,但也反对溺爱。书中指出,“遇强则避,遇弱则肆”[3]8是人之普遍性格。同理,“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父宽则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3]8,父亲严厉,孩子就有所畏惧,父亲宽容,孩子就恣意妄为,于是他得出“慈父多败子”的结论。该书还进一步指出,父母溺爱孩子主要表现为无原则地满足孩子的各种无理要求,“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号,不知禁止”[3]16。对孩子错误的行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怪罪别人,“陵轹同辈,不知戒约,而以咎他人”[3]16,当孩子有过错的时候,以孩子年龄太小而不加以训斥,“或言其不然,则曰小未可责”[3]16。这样下去,“日渐月渍,养成其恶”[3]16,孩子最终成了一个道德败坏之人。袁采指出,孩子并非天生就是品德不好之人,长大之后之所以会这样,在于“父母曲爱之过”[3]16。
《袁氏世范》反对溺爱,但也不主张对孩子过于严厉。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对其特别溺爱,“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3]16,而当孩子长大以后又对其非常严厉,“遂成憎怒”,甚至“以大不孝之名加之”[3]17,这都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3]17,不走极端,在严与慈中寻求一种平衡。就严慈互补的教育方式来说,与袁采同时代的司马光对此作了这样的论述:“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11]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过分溺爱孩子而不加训斥,父母就失去了作为长辈的大义;反之,如果只对孩子进行训斥而忽视了慈爱,则有损骨肉之情,因此,唯有严慈互补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方式。
四、 不可废学:必要的成人途径
《袁氏世范》之所以重视子女的读书问题,除了受传统儒家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外,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宋立国以来文人(文官)地位的抬升。宋初发生了两件与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有关的重要的事,即“杯酒释兵权”与“太祖誓碑”。前者的直接后果是文官地位的上升,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进一步巩固;后者是指太祖立国不久,即订立誓约三条,核心内容为“不杀士大夫”,并把誓约刻于石碑,藏于密室[12]。二是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始于隋的科举制,从宋开始,变成了寒门学子晋升的重要通道,故“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进一步巩固。于是,鼓励子女读书就成了当时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科举出身的袁采自然也很重视子女的读书问题。他认为,通过读书而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是成人的最高标准,他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3]19。当然,袁采也清楚每个人的机遇和天赋是不一样的,“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3]19,学子们不可能都科举高中走向仕途或者成为大儒。但他同时也指出,绝不能因为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放弃读书,“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3]19。因为读书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更难能可贵的是,袁采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局限,指出科举高中或成为大儒并非成人的唯一标准,故而要求子弟不能只读科举考试所规定的那些书籍,而是要读对个人修养、能力提升有帮助的所有的书。“史传载故事,文集妙词章”固然可喜,但其它诸如“阴阳、卜筮、方技、小说”之类的书籍文章,读读也“自有资益”[3]19。况且“子弟朝夕于其间”,把时间都放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也就“不暇他务”,不至于无事可做“而与小人为非”[3]19。
《袁氏世范》鼓励孩子读书,主张在周济穷人子弟时,不仅给予其物质上的救济,还应该给他们提供读书的机会。如果只从物质上救济他们,“不肖子弟得之不以济饥寒。或为一醉之适,或为一掷之娱”[3]62,有些被救济的人在获得财物后,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是生活必需品而备加珍惜,反而随意挥霍,那就达不到救济的目的。如果所得财物充足,他们则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扰暴乡曲,紊烦官司”[3]62,由此可见,只是进行物质周济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袁氏世范》中提倡给予贫穷子弟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周济,“不若以其田置义学……能为儒者择师训之,既为之食,且有以周其乏”[3]62,既填饱了肚子,又能教育其为人之道,这样,贫穷子弟就“不至失所狼狈,辱其先德,亦不至生事扰人,紊烦官司也”[3]62,其成人后就算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不会危害他人与社会。
五、 固定有业:务实的教育归宿
《袁氏世范》吸收了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10]254思想,主张子弟必须有固定的职业。它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3]18不管是富家子弟,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成人之后,必须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工作。当然,在袁采这里,穷、富两类子弟从事职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寒门子弟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3]18。富家子弟家境殷实,无生计之忧,他们工作并非为了改善生活,“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3]18,而是有了正当的职业后,他们就不会去做坏事。袁采进一步解释说,富裕家庭的孩子如无职业,因无生活之忧,就会“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甚至“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这并“非其本心之不肖”,而是“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3]18。因为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才有为非之心,进而走向败家破业之道。
儒家认为,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樊迟向其师孔子请教“稼穑之学”,孔子却说“小人哉,樊须也”[9]142,樊须即樊迟。孟子就曾把职业分为劳心与劳力两种,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0]258,从事稼穑,从事体力劳动,为末业[13]。到宋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有所改变,这在《袁氏世范》里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袁采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出身各不相同,从事的职业也应多种多样,职业只不过是使家庭殷实不衰和社会稳定的手段而已[14]。他还认为,因人的智力天赋不同,故在职业的选择上也应该有所区别。对于“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而言,选择职业“莫如为儒”[3]112,因为“习儒”“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即通过金榜题名获得财富;“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3]112,即差一点也可以通过开私塾、教学生获得相应的报酬。对“不能习进士业者”而言,“习儒”“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3]112,即依靠帮别人写文章书信过日子;“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3]112-113,再不济做儿童的启蒙老师也可以维持生活。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习儒”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建议子弟可学习“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使术”等各种技能,只要“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3]113,也就是说,从事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能养活自己且不辱没先人就行。对于那些既不能“为儒者”,又“不肯为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使术”的子弟,“深可诛也”[3]113,即应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在《袁氏世范》中,袁采进一步指出,子弟如无业,则会到处流荡,甚至“为乞丐、盗窃”[3]113,而这是最辱没先人的事,也是家庭教育最大的失败。
结 论
综上所述,作为“《颜氏家训》第二”的《袁氏世范》,其家庭教育思想,无论是在教育时机、还是教育方法、抑或是教育内容上,既继承了《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又凸显了袁氏家庭教育思想的一些新内容。如在教育子女读书的目的方面,颜之推强调的子孙后代能够“学以致仕”,而袁采认为除了实现“学以致仕”理想外,更多的是基于“学以致用”的考虑。在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这种家庭教育思想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该书诞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这一时期是封建专制集权进一步加深、礼教纲常进一步严苛的时期,故其家庭教育思想中“父为子纲”的陈旧观念更加明显。此外,《袁氏世范》中的因果报应、歧视下人、鄙视仆人的思想也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地位没有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2]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家庭的教育功能无可替代,家风家训的教化功能不能忽视。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以《袁氏世范》为代表的家训文化时,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5],为构建新时代的家风家训提供合理的养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从而有效地为当代的家庭教育服务。
注 释:①美国中国历史研究者、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著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一书,对《袁氏世范》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