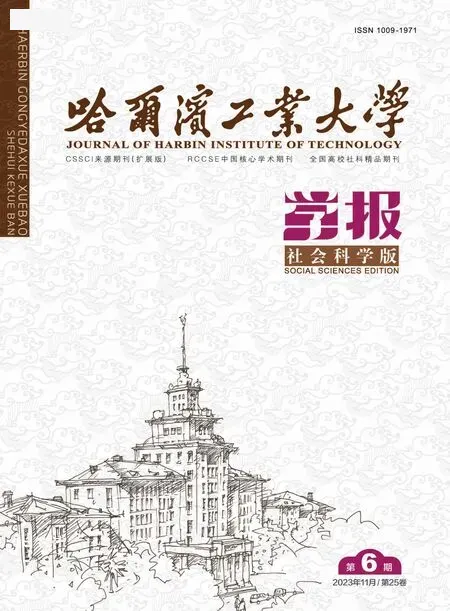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王洪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曹魏、蜀汉、孙吴是从大一统的汉代母体里滋生发展而来的,尽管东汉的学风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东汉末叶,官学制度废弛,出现了处士横议的政治以及社会现象,但士人接受教育而形成的自身的知识学养还是较高。 经学知识储备一直是士人最基本的才情基础,尽管表现出不尽相同的个体风格。 《文心雕龙·宗经》云:“百家腾跃,终入环内。”[1]23此就文体与六经的关系而言。 综观魏晋时代文人与文学,虽然百家腾跃,沐浴玄风,思想旨趣固有不同,大体还在儒家的知识范畴之内,这就为我们探讨汉末魏晋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想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
一、文质相复:历史循环论的文学理论向度
刘勰历叙十代,总结了从夏禹到齐梁“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变化规律,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观点,由此历史循环理论介入文学批评范畴,这是刘勰的理论贡献。我们知道,阴阳是中国古代先民观察自然变化而总结出构成世界或现象本源的要素,先民又根据天文以化成人文的思想,从阴阳往复循环的客观规律中提炼出了社会循环的历史规律,这样的历史演化进程孔子称之为“文”“质”的交替,经学家总结出“三统论”,阴阳家推演出“五德终始说”。而这样一种建立在自然、天道基础上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无疑指引了秦汉魏晋的历史发展。
《礼记·表记》载:孔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2]2532以“质”与“文”来论述历史上的朝代,这是儒家先师的一种发明。 虽然孔子关注和评价的焦点是历史,但是在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中带有明显的文学因素。 孔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质胜文”“文胜质”,无疑为睿智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路径。 孔子批评夏、商、西周的政治特点时也有过相关的论述: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 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2]2528-2530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太史公继承并且发展了这一观点。 《平准书》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4]1442《高祖本纪》又云:“夏之政忠。 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 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4]393-394汉兴得之于天统,这是董仲舒的观点,也就是著名的历史循环的三统论。根据三代兴亡的历史规律,董仲舒认为“逆数三而复”,这就是革命。 周革殷命,殷黜夏命。 夏承天统,其色黑,又称黑统。 殷得地统,色尚白,为白统。 周得其人统,色尚赤,为赤统。 《春秋元命包》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5]622夏商周之后的汉代,天统色黑,汉代人是不承认短祚的秦王朝的,认为汉朝直接承周而来。
与历史发展的文质说、三统论不同的是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这一理论界说见《吕氏春秋》的《应同》篇,其云:“黄帝土德,色尚黄;夏禹德,色尚青;商汤金德,色尚白;文王火德,色尚赤。”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 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6]
在邹衍看来,从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王,经历了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的一个历史演变规律,根据五行相胜的历史逻辑,战胜周朝的,即“代火者必将水”,水德则色尚黑。 所以,秦朝建立,以为水德尚黑。 刘汉政权无视秦朝的历史存在,直接继承周,所以刘汉政权也认为是水德尚黑。 从阴阳学说演变出来的两种历史发展观的理论自洽性在汉初是趋于一致的。 但是,西汉人自动进行了两场颜色革命,首先是承认秦的历史存在,秦水德尚黑,汉则为土德尚黄。 而土德尚黄,含有返本之义。 如《风俗通》论“五伯”所云:“盖三统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纲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兴,德以五成。 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 至道不远,三五复反;譬若循连镮,顺鼎耳,穷则反本,终则复始也。”[7]以阴阳相胜总结出的历史循环律,终于完成了自身的循环,“三五反复”“穷则反本”,无疑是阴阳学、经学双重维度的胜利;其次是利用五行相生,刘向、刘歆父子延长并且补充了历史统序,创立新的五德终始说,汉由土德尚黄变成了火德尚赤。 而火生土,为新莽的土德尚黄创造了足够的思想以及理论准备,于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禅让,开启了政权鼎革的新模式。 东汉光武帝重新确定了火德尚赤的政治理念,汉魏禅让就是以曹魏的土德尚黄代替了刘汉的火德尚赤。 汉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曹丕劝进有言:“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8]70所以曹魏以土德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改年号为黄初。 《献帝传》记载:曹丕封禅诏书曰:“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8]75曹丕等一班君臣们或许以为这就是大汉历史的终结,开启了国运昌盛的大魏,岂不知禅让的政治魔盒才刚刚打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历数已经在晋,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如汉魏故事。 魏太保郑冲奉策曰:“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 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 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 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9]50“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虽然魏晋禅代,但是,晋人显然是不承认曹魏政权的,所以晋史是从司马懿开篇的。
董仲舒又说:“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 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 者主人。”[10]《说苑·修文》解释说:“商者,常也。 常者,质。 质主天。 夏者,大也。 大者,文也。 文主地。 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 正色,三而复者也。”[11]《春秋元命包》说得尤为明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5]622于是,根据质文代变的规律:夏主地(文),商主天(质),周主地(文),汉主天(质),魏主地(文)。 恰如《白虎通·三教》所述:“王者设三教者何? 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 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12]文质之间的穷则返本,曹魏政权的建立就是在返本,即主“文”,文也是在救汉“质”之所失。 刘逢禄《论语述何》曰:“文质相复,犹寒暑也。 殷革夏,救文以质,其敝也野。 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13]从“文质相复”的历史规律来讲,曹魏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主文的时代,而在刘勰这里“质文代变”则转换成一个文学理论的命题。 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刘勰的质文何谓? 在《情采》篇有了解释:“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 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1]537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无论是“文附质”,还是“质待文”,都是受到了孔子文质历史观的影响。 而刘勰又将文与质纳入文学视野,文质也就和辞采与文章息息相关了。 根据文质的变化,也就是辞采的变化,刘勰写了最早的一篇文学史,认为魏晋文学发生了“梗概而多气”“篇体轻淡”到“结藻清英”的“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的审美变化,文学出现了个性张扬、才华四溢、文采飞扬的繁盛局面。
二、“诗人之赋丽以则”与“诗赋欲丽”:文学理论的隔空接应
据《华阳国志》记载:“蜀国北与秦分,其精则井络。”又引《河图括地象》说:“岷山之下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14]26实际上,《河图括地象》记载的是“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5]1100,《易纬乾凿度》也说“岷山上为井络”[5]61,这是具有占星术性质的星土分野说的内容,意即岷山的天文分星是井星,也就是井络。
《华阳国志》又云:“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 其辰值未,故尚滋味。 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 与秦同分,故多悍勇。 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14]26《坤》卦六三曰“含章”,六五曰“黄裳”,都有文章、文采的意味,这就是上文所谓“文主地”“夏文者主地”的真实内涵。 所以,《说卦》曰:《坤》为地,为文。 在后天八卦的方位图中,《坤》主西南,所以常璩才有文章多彩斑斓之说。 同时其地又合《诗经·大雅·江汉》诗旨,所以说有夏声。
《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15]1642秦国掠地攻城,国土急剧扩张,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 秦地的分野就成为东井、舆鬼。 东井之星,对于汉高祖刘邦有重要的天命内涵。 汉中是刘邦被封为汉王的封地,刘邦进入关中,恰逢五星聚东井,于是被占星家看成刘邦的受命之符,这也是汉代人的共识。
蜀地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文翁开教之后,“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岳立,林翁孺训诰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14]32班固为文翁作传,云“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是说到京师求学的蜀人数量之多和齐鲁来京师为学的数量相埒。 但是常璩却认为,蜀地的人才既可比鲁之洙泗,又能比齐之稷下,一再强调“汉征八士,蜀有四焉”。 蜀地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蜀人的文化传承无奈是中断了的,文翁兴学才使蜀地蜀学中原化、儒学化,但是,巴蜀的山水格局孕育出的巴蜀人的精神乃至涵括的思想空间是中原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张行成《华阳县学记》就说:“华阳,古梁州之境,卦直《坤》,故俗尚文;星属鬼,故君子通敏,其人任。 武王伐纣,始见于经。 自文翁立学官,得张宽、司马相如辈,厥后王褒、何武、扬雄、庄遵之流继出,汉之英才,蜀最为富。”[16]庄遵字君平,为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成严遵,专精《周易》,著《老子指归》,扬雄少师事之。 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三诗以颂汉德,令人演唱歌舞,何武时年十四五,亦在歌舞者中,被汉宣帝赐以锦帛。 何武诣博士受业,屡迁官至御史大夫、前将军。 东汉班固说:“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5]1645这是对于西汉文章的总体评价,显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文学地位是称尊于西汉的。
《西京杂记》“相如作赋”条记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 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17]
我们可以把此文看作一篇赋论,“意思萧散”“忽然如睡”已经进入了庄子超然物外的神思状态,妙然心会,寄情成篇。 “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就大赋的体势和内容而言,他已经超出了中原辞赋略显拘谨而又絮繁古板的构思模式以及创作程式,是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宇宙同轨,与天地精神往来,与万物妙合。 将人物立体化而又超越人物的表象,直指内心,清灵而又渺远,从而构成心与意、情与境“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玄远而又奇妙的空灵境界,恰如刘勰所说:“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这是中原辞赋无法望其项背的精神远游。而这一精神境界又与蜀地“不与华同”之高山大川含蕴的峻峭奇秀精神相契合,神秘与幽远的古蜀文化与儒家的文化教养成就了司马相如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也开启了汉大赋铺张扬厉的先河。史载,司马相如等东受七经,也就是说,司马相如是站在儒家文化圈外,或者说中原文化圈外,去看待辞赋去创作辞赋去品物流形。 司马相如的赋使用了儒家经学赋予的辞采华章,又受个体深蕴巴蜀文化精神以及场域的控引,成就了一股清新飘逸带有异域风格的大赋,这也是汉武帝发出恨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又“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蜀人有“斑彩文章”,细数西汉最著名的赋家,无论如何都不能越过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而且均为令人仰望的高峰。 王褒是辩士,作赋颇多颂圣誉世之意,其所作,《中和》《乐职》《宣布》三诗,即便汉宣帝都以为过之:“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15]2822又作《圣主得贤臣颂》,已经不是近谀,而是面谀了,失去了赋之所以为赋的讽谏之旨,以至沦落到为太子戏弄,以倡优比之,此乃辞赋作为文饰政治而成为风雅附庸的具体表现。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王褒能够成为宣帝朝辞赋家之首,其身上所独具的蜀地精神文化气质,即文采斐然与玄远境界相结合的特点。
来自巴蜀的扬雄之辈是以司马相如为矩式的,“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15]3515无论蜀人如何拉近与诸夏文化的距离,如大禹出西羌,武王伐纣同盟有巴蜀之族,秦人据黔、蜀、巴、汉,汉王王巴蜀,但是由于山川险阻,巴蜀始终带有异域文化的色彩。 扬雄对于司马相如、屈原的认同,更有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而地域文化以及地域空间所形成的思想空间与精神张力,潜移默化地共存于本土本民之中,从而形成特定的无法忽视的浸入血脉的文化因子。
扬雄先后师事道家严遵、大儒林闾,博览群书,会通儒道之学;其赋宗屈原、司马相如,又与当时大儒桓谭、刘歆友善;与王莽、董贤、刘歆同官黄门侍郎,所以,扬雄的学问先黄老而后六经,博为通儒,人称“西道孔子”,也是成、哀间辞赋创作的高峰。 但是,扬雄的学问和中原大儒的学问有着本质的区别,玄远的思想境界与空灵的精神空间是诸夏之儒所不具备的。 班固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15]3575这就是扬雄贤于众儒而颇显高明的地方,虽然崇拜司马相如,但能够置身于世外进行积极的思考。 扬雄儒道兼综的学养,在蜀学与儒学之间,进退之处,作为一个辞赋作家,是对于西汉的辞赋,也是对于自己侍从之臣做出的文学活动进行了冷静客观的批评,并且辍笔而不为。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 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18]45坦然而又坦率地面对曾经的自己,这也是一份襟怀。 虽然依然站在文学实用主义立场上来看待问题,无疑,扬雄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一个,终于走出了“灵均”“司马长卿”的精神阴影,同时他又是最特立独行的个体,《太玄》《法言》的创作彰显了作者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
正因为一个辞赋家有着一份学者的清醒,并且是儒道兼宗的学者,那份冷峻和深刻就不是一般儒者或者文学家所具备的,尤其是其所持有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审美距离,也是当时所谓批评家无法比肩的。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如其不用何?”[18]49-50
扬雄首开用“丽”来评价辞赋的先河,无论是诗人之赋,还是辞人之赋,只是“丽”的程度不同而已。 扬雄“诗人”之云,是古人认为赋为古诗之流裔,所以作赋者即为诗人,这是对于具有儒学知识与背景的士人而言的,即孔门之赋,如贾谊、司马相如等人作赋,有止乎礼仪的准则,所以有讽谏的旨趣在焉。 汉代的辞赋基本上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所谓辞人之赋是指景差、唐勒、宋玉、枚乘等一派人物,喜欢用辞赋去抒发感情,表达自己的沉思,毫无节制地展示才华,玩弄词藻,有辞采泛滥的弊端。 而讽谏则无从谈起,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汉书·艺文志》总结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5]1756扬雄用“丽”来批评辞赋,是就辞赋的作者身份而言。 而“丽则”与“丽淫”的分类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一生谨慎,作过《太玄》的扬雄,不会如此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回答或问“君子尚辞乎”时,扬雄说:“君子事之为尚。 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 事、辞相称,乃合经典。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18]60意思是说:君子言辞要讲求实事求是。 事繁盛而辞少,则显得刚硬。 表达之辞胜于其所云之事,这是作赋颂虚枉的表现。 事与辞相当,即表达得恰切,这是合乎经典规范的。 无论说话还是做事,不亢直不藻饰,恰切允当才是德之文。 反观扬雄的一生行事,少年清静寡欲,作赋模仿屈原、司马相如,读屈骚未尝不流涕,作骚体赋,感情真挚而充沛,作赋亦有吞吐天地之气象,辞采斑斓,可谓辞人之赋;当扬雄待诏金马门,成为御用戏弄之文人,只是用赋颂装饰帝王的门面,又需要尽臣子的责任,这就有了符合赋体讽谏的要求,由是变成了有节度的诗人之赋。 扬雄认为,这两者都是有不足的,实事求是,辞事相当,才是真正的好文章。 其后,西汉末叶,社会、政事包括人文动荡,扬雄已经脱离了用文章以文采自雄自壮的人生阶段,认为作赋乃雕虫小技弃而不为,而是进入了儒学走进了经典躲入内心,开启了自我的防御和保护,然而最终依然未能幸免于难。
无论是诗人之赋的丽,还是辞人之赋的丽,都是站在汉代经学立场上的审美审视。 在六经皆文的视野里,诗人之赋的丽是有儒家博大精深的知识基础作为支撑的,是文章的自然表现。 然而,辞人之赋的丽胜之在才情,是人的个性的体现,是情感不受约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其辞虽然靡丽,其精神境界自然不是诗人之赋所能比拟的。 到了建安末期,“唯才是举”的选人标准,无疑剥去了儒家士人刻意打造的彬彬君子人格的虚饰、哪怕是作伪也要温文尔雅的生命样态。 在标举才情的时代,文学回归自身,不需要讽谏,只看锦绣文章,才有了“诗赋欲丽”属于文学范畴的审美批评。 曹丕已经无视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更不用去考察文人的人性,“丽则”与“丽淫”更不在文学审美的观察之列,而是就文体本身而言,“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的特点和要求已经总结出来,文章的优劣只能靠作者的才华来衡定了。 也就是说,个性和辞采成为裁量文章品质的决定性因素。 鲁迅称之为文学自觉,他说:“(《典论·论文》)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9]虽然现在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而文学脱离儒家教化的羁绊,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丽的特质确实已经在汉魏的门槛上提出来了,这是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五百年后,刘勰读懂了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文学批评,洞见了曹丕“诗赋欲丽”的审美内涵,从情采的角度来看待儒家文学或者说中原地区文学的流变,他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何以明其然?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1]538在不否认儒家士人真性情的文学情感抒发的情况下,不仅诸子辞赋,“为文而造情”恰恰也是文学侍从之臣辞赋的最大弊端。 在某种程度上说,刘勰精准地阐释了扬雄的文学洞见。 但是,刘勰另辟了一个批评领域,那就是《辩骚》。 因为刘勰已经注意到了“非经义所裁”“叙情怨”的骚体赋一派,才高而狷介,尤其是在司马相如、王褒的辞赋中看到了屈骚的影响,而这二人恰恰是蜀产,亦在儒家思想钳控的地域边缘,有不与中原同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空间,同时也包括儒道兼宗的扬雄。 从扬雄到曹丕到刘勰,诗赋欲丽的文学批评话语与文学批评方式,显然已经成为汉魏六朝无法逾越的理论问题,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讨论。
三、“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陆机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
当文学成为一种由上而下的兴趣和爱好,甚至引发了一股文学思潮并演变成为一场文学运动,整个时代的文人也就趋之若鹜了;一旦文学变成展示才华、驰骋辞藻的工具,文学就具有了私情性以及个性化的特征。 在魏晋这个开始重视文的时代的到来,邺下所形成的文学风气,不会因为三国分裂割据而孤独与寂寞。 不仅曹操、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在文学上光彩夺目,曹丕也是文学家,亦是文学批评家。 曹丕《典论》自序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8]90亲见疾疫引起文学之士的凋零,曹丕深自感伤,恐难自免。 《魏书》记载:“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8]88魏黄初三年(222),即吴黄武元年,孙吴大破刘备,胡冲《吴历》记载:“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 文帝报使,致鼲子裘、明光铠、騑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8]1125《魏书》裴松之注也引《吴历》记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8]89也就是说,曹丕自己抄写了两份《典论》并以皇家赐予的方式,分别送给孙权、张昭,彼时孙权是称臣于曹魏的。 曹丕既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个自负的文学家。 政治上希望孙权欣赏自己的才能,文学上希冀张昭看到一代帝君的风雅,所以带着不同的目的把《典论》赐予二人。 需要注意的是,在讨论《太玄》问题时,王永平说:“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尽管虞、陆不满宋注,但《太玄》是从荆州传入的,二人注释《太玄》也应宋注的传入而引起,仍然反映了荆州学术的影响。’而沟通这一联系的则是张昭。”[20]显然,张昭在当时士林中的学识与名望是非常高的。
张昭博览群书,与曹丕素所敬重的王朗相友善,被孙策称为管仲,有“仲父”之称。 吴中四姓,张姓是以文著称的,即便是桀骜难驯、文采四溢的祢衡也叹服其才华。 黄初二年,曹丕拜张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赐予《典论》也有酬文学知己的意味,或许也有曹丕自傲的炫耀成分在。 张昭是陆机二哥陆景的外祖父。 陆景字士仁,“以尙公主拜骑都尉,封毗陵侯,既领抗兵,拜偏将军、中夏督,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8]1360,裴松之注:“景弟机,字士衡,云字士龙。”[8]1360陆抗生有六子,从这一注释我们可以看出,陆景、陆机、陆云是同母兄弟,都是张昭的曾外孙。 与王浚之战中,三十一岁的陆景殉国。 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陆云六岁能属文,有才理,与兄陆机齐名,虽文章不及陆机,而持论过之,人称之为“二陆”。而此陆氏兄弟三人,有才华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日本人林田慎之助说:“从陆机的血统看,他卓越的文学天才,与其说继承了父、祖‘忠’的传统,还不如说承袭了母家张氏家族‘文’的传统。”[21]这一观点是成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陆机接触过《典论》。 《吊魏武帝文》自序曰:“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郞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 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22]625著作郎的职责是修史,可以阅览宫廷藏书,既然能见到曹操的临终诏书,就能见到宫廷中所藏曹丕的《典论》,而《典论》此时尚存乎石经之中。 杜甫所谓“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是不现实的。 凤凰三年(274)陆抗病逝,史载陆机为牙门将,此时十四岁,或许在成年之后领父兵。 陆机二十岁吴亡,两位兄长殉国,其尚能驰骋才藻而作《文赋》? 陆侃如认为《文赋》作于永康元年(300)[23],逯钦立认为作于陆机四十岁, 即在晋惠帝永康元年(300)[24],杨明《陆机年表》认为作于太安元年(302)[22]1078,然而,无论是哪一年,都是在陆机任著作郎之后。
《文心雕龙·时序》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1]672又《声律》云:“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 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1]553由此可以判断,陆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远祧屈骚,近师子桓。 陆机诗文祖屈骚已有定论,且陆氏兄弟书信中尚讨论《楚辞》,陆云与兄书说:“尝闻汤仲叹《九歌》。 昔读《楚词》,意不大爱之。 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屯为宗矣。 ……思兄常欲其作诗文,独未作此曹语。 若消息小往,愿兄可试作之。 兄复不作者,恐此文独单行千载,间常谓此曹语不好,视《九歌》, 正 自 可 叹 息。 王 褒 作《 九 怀》, 亦 极佳。”[25]147-148显然,陆机早有作《九歌》一类赋作的想法,但是,迟迟未见写作。 陆云劝兄长,如果再不作《九歌》,《九歌》便是无可匹敌而独行千载。 于此可见陆云对于陆机的评价与期许是非常高的。 在陆机没有回复的情况下,陆云自己创作了《九愍》,并在序中说:“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 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 而 表 意 焉。 遂 厕 作 者 之 末, 而 述《 九愍》。”[25]127文雅之士,当然也包括其兄陆机。 陆云对此文自视甚高,要自立一家之说,对于《九愍》,陆机的评价也很高。 “至兄唯以此为快,不知云论文何以当与兄意作如此异。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颇能作泛说耳。 又见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说。 唯兄说与《渔父》相见,又不大委曲尽其意。 云以原流放,唯见此一人,当为致其义,深自谓佳。 愿兄可试更视。 与《渔父》相见时语,亦无他异,附情而言,恐此故胜渊弦。 兄意所谓不善,愿疏敕其处绪,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惑如恶所在。”[25]154陆氏兄弟为三楚之人,修习并且模拟楚骚类作品而进行创作,对于他们来说是掌握最基本的文学知识,也是写作的必要训练。
说陆机近师子桓,有些勉为其难,从陆氏兄弟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兄弟二人都有与其他文人包括建安文人一比高下的自傲,陆云作《九愍》即有“厕作者之末”的深意在。 永宁二年(302)六月,陆云作《愁霖赋》,序云:“邺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穑沉湮,生民愁瘁。 时文雅之士焕然并作,同僚见命,乃作赋。”[25]11《喜霁赋》序云:“余既作《愁霖赋》,雨亦霁。 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霁赋》,聊厕作者之末,而作是赋焉。”[25]13屡次言说“聊厕作者之末”,其逞才斗志、一比高下跃跃欲试的心态表露无遗。
陆云与兄书云:
仲宣文如兄言,实得张公力,如子桓书,亦自不乃重之。 兄诗多胜其思亲耳。 《登楼赋》无乃烦。 《感丘》吊夷齐,辞不为伟。 兄二吊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当以此言为高文耳。 ……往曾以兄《七羡》“回烦手而沉哀结”上两句为孤,今更视定。[25]146-147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然自复能作文。云唯见其《登台赋》及诗颂,作《愁霖赋》极佳,颇仿云。 云所如多恐,故当在二人后,然未究见其文。 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25]165
特别是张华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的肯定和积极推荐,只能助长陆机的骄傲,甚至是狂傲的心理,且又有一个赞美多于批评的迷弟,或云“省兄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或云“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或云“兄文章已显一世”。 我们借用时为太子的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之语曰:“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 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搉。”[26]可以,为陆云拟之曰:“文章未坠,领袖之者,非吾兄而谁?”非陆氏兄弟自视甚高,而是世人皆以为其甚高。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27]分八体于四科,用“雅”“理”“实”“丽”来概括四科的写作特点,从此关注辞采雅丽便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的审美范畴。 陆机《文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的观点,去掉了曹丕所论书、议,增加了碑、箴、颂、说四种文体。 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22]21《初学记》将《典论·论文》与《文赋》并称,谓之“比四科,若五色”[28]。 罗宗强先生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分析说:“绮靡是华美,缘情而且华美,近于曹丕的‘诗赋欲丽’。 浏亮,清明之状,指风貌言。 被文相质,黄侃谓:‘文其表而质存乎里。’缠绵,指情思之婉恋;凄怆以言悲感。 缠绵凄怆,指感情格调与感情表达方式,都是艺术风貌问题。 温润、清壮、优游、朗畅、闲雅、炜晔,也都指文章风貌。 他描绘的是这十种文体所应具备的风貌类型。”[29]罗宗强先生的精彩分析恰恰是钱基博“扬榷文体,发凡起例,实刘勰《文心雕龙》之前导,而为中国文学批评之初祖也”[30]最好的注解,此就曹丕、陆机文学理论本身而言。 但是,从断代文学发展来看,还是有人看到了二者的差异性。
明人皇甫汸《解颐新语》:“《典论》‘诗赋欲丽’,建安以前之体也;《文赋》‘缘情绮靡’,泰始以后之体也。”而胡应麟又指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 ‘赋体物而浏亮’,六朝之赋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31]文学批评的基础是文学作品,也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样态,更多地具有时代性。建安文学是东汉文学的高峰,而太康文学是两晋文学的高峰。 曹丕在总结,陆机也在批评。 《文赋》实有与曹丕《论文》相抗衡的意味,亦有不朽之意在焉。 朱东润批评陆机说:“机之为人,急于功名,进取太甚。”[32]无论文才如何之高,辞采如何之华茂,情商微于智商,盛世堪危,乱世如何能苟全性命?
实际上,陆机是聪明的,也是清醒的,他已经意识到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他曾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文赋》),这是魏晋时代的症结——奢华、奢靡,而且是自上而下的。 青龙三年,魏明帝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奢华之盛屡见诸正史记载。 无论何朝何代,太过奢华还是有诤臣来谏阻的,太子舍人张茂就以吴、蜀未平,诸将出征在外,而皇帝盛修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予无度,致使帑藏空竭;又剥夺那些士女即已嫁为人妻者,还以配士卒,又简选其中有姿色者纳之掖庭,乃上书谏曰:“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雠之心矣。”[8]104-105这样的谏诤显然没有起到作用。 景初元年(237),“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 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 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 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河东董寻上书谏曰:“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参倍于殿舍。”[8]110从历史的记载可以看出,自魏明帝始,政治上开始进入崇尚奢华追求物欲的时代,文学上崇尚富艳的辞藻是生活的余味。
魏明帝时,何曾历任员外散骑侍郎、典农中郎将、黄门郎,“性奢豪,务在华侈。 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 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 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9]998其子何劭亦好奢华,“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世说新语·俭啬》载:“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 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33]1025通过禅让获得国柄的晋武帝,早期也是励精图治的,然而,并没有能抵挡得住整个社会的奢华之风浸染而走向了风花雪月。 泰始九年(273)七月,下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太康二年(281)三月,下诏选孙晧妓妾五千人入宫,晋武帝后宫妃嫔人数已达万人。奢华的生活享受,是从下而上的。
《世说新语·汰侈》载: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瑠璃器。 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烝肥美,异于常味。 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33]1029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 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 时人号曰“金沟”。[33]1035-1036
王武子即王浑之子王济,尚晋文帝之女常山公主。 常山公主与晋武帝乃是兄妹或姐弟的关系。 而奢华程度比王济犹有过之的是石崇。 《晋书》本传载:
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恺以澳釜,崇以蜡代薪。 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 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崇、恺争豪如此。 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 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 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 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9]1007
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舅舅,二人毫无节制的斗奢比富,晋武帝不但不阻止,而是暗中襄助,这样只会助长攀比奢华者的气焰。 而石崇、王恺的奢华无度,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所以,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疑问,不是矫情,而是生活。《晋书·五行志》评论说:“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 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 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 崇 既 诛 死, 天 下 寻 亦 沦 丧。 僭 踰 之 咎也。”[9]837大臣的靡丽奢华是不至于亡国的,君主的奢华才是最可怕的。
魏晋时代,不仅崇尚生活的绮罗俊彩、珍玩馐馔,就是在容貌上,宠爱俊美、关注人物神采也是在历史上出了名的。 《世说新语·容止》载: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裴令公有儁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 时人以为“玉人”。
卫玠号为“玉人”,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晋书》载:“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9]1235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晋书》又载:王劭、庾亮、刘胤、嵇绍、吴隐之、杜乂、王蒙都是“美姿容”,容貌似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特性、才华的时代标准,潘安是历代公认的美男子,并且是才华横溢的美男子,于是潘安就变成一种镜像,一个意象,品德已经不在世俗考察的范围之内了。
周秦汉人曾以文质论述历史朝代的更迭,魏晋进入了文的时代,而这个文又发生了内涵的扩张,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绮靡”。 一个过度重视生活的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那么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文采表现华美。 能从众多文采飞扬的为世人称颂夸喻的文人中脱颖而出,必有奇情和奇彩。 作为吴楚之人的陆机选择追慕祧祖屈骚,既有地利又有天时。 他以自己的异才以及异采,以“出自敌国”的身份,去闯荡深辞丽藻的中原,希冀在中原文人中立住足,且能独领风骚,不是靠父祖庇荫。 洛阳“伧头”的鄙视,首先打掉的就是“亡国之余”来自父祖辈的骄傲和自信,而陆机凭依屈骚以来的文学积累,冷静审视洛阳文人们的人情才情以及文情,他有着超然的自信,“二陆入洛,三张减价”,陆机成功地抢夺了洛阳文人的风采。 所以,胡应麟说:“‘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这是时代的共色,生活奢华,生活中色彩华美,人物也以俊美为荣,如此,“心术既形,英华乃赡。”(《文心雕龙·情采》)诗文崇尚奇采、繁缛、富艳而彰显个性,这是时代的文学特色。此为陆机《文赋》生成的内在机理,或者说是这样的创作心理支撑起陆机的文学创作。
既是自恃才情,陆氏兄弟也是在和曹植、曹丕兄弟比才华,与建安文人比文采。 曹丕是站在汉与魏、旧与新时代的门槛上,对于当时的文学现象,尤其是产生在身边的文学作品进行高屋建瓴的评价,同时还受皇权思维定式所影响。 当然,也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儒家诗学观念的束缚,这是自觉不自觉烙印在思想深处的文化因子。 而陆机虽然“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家传《易》《玄》之学的传统还是存在的,这在西晋这个时代更能引起士林的共鸣,所以陆机能够与审美批评的作品之间保持距离,通透地进行文学批评。 但是这种批评主动依傍儒家的文教观,这是身在局中不得不为之的,他与曹丕最大的区别是,曹丕在儒学的道统之内,陆机在儒学的道统之上,所以审美的距离是有区别的。 同时,时代又发生了变化,文学思想的转型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