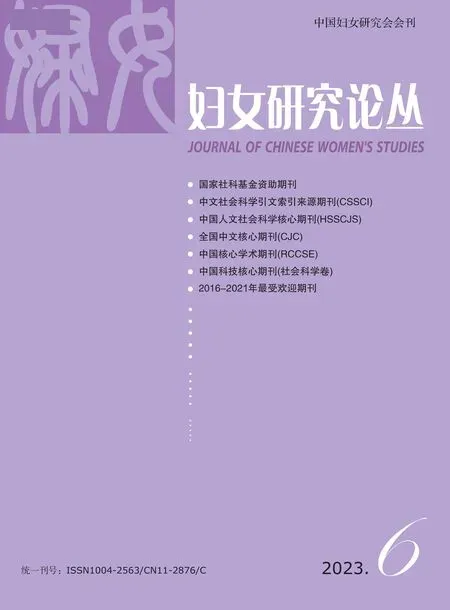作为“统筹者”的女工: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女工新身份*
——以华北Z县自雇装修工为例
杜 博 王 欧
(1.2.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便以农民工群体的城乡迁移为主,城乡结构与农民工家庭形态的关系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农民工家庭长期处于“拆分”的状态[1],即生产(劳动)与家庭再生产(照护)过程的分离以及家庭成员的离散[2](PP122-149)。“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为拆分型家庭形态增添了性别维度,相关研究发现,拆分型再生产体制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严格限制往往把女工置于“进城务工—返乡照料”的二元框架内[3],女工若要维系打工劳动者身份则必须牺牲对子女的陪伴和照料[4]。女工这一相对单一的打工劳动者身份的形成,不仅是城乡结构在空间上对农民工家庭进行拆分的结果,更与制造业、建筑业等生产体制对女工劳动的榨取和规制相关,两方面共同挤压了女工在打工地兼顾再生产劳动的可能[5]。正因如此,近年来以“离土不离乡”为核心特征的县域城镇化被寄予了打破拆分型再生产体制的期望[6],就近、就地就业使得本地女工回到劳动力市场不必以完全牺牲家庭为代价,空间距离的压缩与交通便利的增加也为拆分家庭的缝合提供了条件[7]。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工的生产劳动与家庭再生产劳动会自动整合起来,相关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本地女工往往要在承担家庭主要再生产责任的基础上从事生产劳动,面临工作与家庭“双重再生产”的时间挤压困境[8],甚至因家庭照料牺牲劳动参与。
上述两类对女工身份的研究都忽视了女工能够统筹双重劳动的生产条件与微观机制,特别是忽视了女工对劳动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的需求。前者聚焦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家庭的拆分,女工打工劳动者身份的获得以牺牲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代价[9];后者所强调的本地就业形态弱化了女工所面临的空间冲突,但对有助于女工协调双重劳动的具体生产条件缺乏关注。事实上,返乡女工通常受雇于制造业、农副业或从事分散加工等工作[10],生产的效率要求与资本化的管理体制压制了女工的自主性,女工难以获得协调双重劳动的时间机会。
沿着上述思路,本文以华北Z县(1)根据研究惯例,本文对经验材料中的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的自雇装修女工的案例为研究对象,研究县域内自雇的产业组织形态如何促成女工统筹装修工作的劳动与经营环节,揭示自雇劳动体制的灵活性和空间临近性怎样为装修女工提供统筹生产和家庭再生产劳动的条件。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可以丰富对女工工作身份的理解,女工不仅是参与装修的劳动者,更承担起经营者的角色,这对装修工作的开展、维系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本文提供了女工协调劳动与照料身份所需生产条件的一种可能,阐释了在自雇劳动体制下女工既可以担任装修工作的重要角色,又能够部分协调家庭照料责任,成为双重劳动的“统筹者”。
二、文献回顾
(一)女工的城乡迁移与打工劳动者身份的建构、延续
自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兴起就有大量研究关注了城乡迁移对女工劳动者身份的塑造。沿海城市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吸纳了大量女工就业,其资本化的生产过程敏锐识别了女工的年龄特征,没有家庭再生产负担的“打工妹”契合了制造业生产的效率要求[11](PP67-89)。这一过程使得未婚女工的打工劳动者身份得以构建,经济上的独立也为女工的婚恋自主奠定了基础,未婚女工得以暂时“脱域”于父权制的安排[12]。然而,在城乡结构的严格限制下,她们很难实现向上流动,也很难以定居的方式融入城市,她们大多要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成家,从而进入家庭的轨道[12]。早期打工生涯未曾从根本上动摇父权制家庭传统(即父系、从夫居、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性别劳动分工),使得女工成为家庭照料的主要责任人,并陷入照料者与劳动者相矛盾的双重身份之中。
内嵌于城乡结构的身份制度加剧了女工双重身份的紧张,甚至造成女工某一身份缺失的后果。户籍制度促成的身份区隔使农民工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资源,农民工家庭因此处于拆分、碎片化的状态[1][13](PP159-189)。城市福利系统的待完善使得已婚女工直面生育、抚育等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女工往往要借助乡土资源来实现家庭的绵续[14]。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女工要返回老家留守,女工若要恢复劳动者身份重启打工历程,很大程度上要以牺牲家庭生活、孩子陪伴为代价[15](PP93-95)。女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不仅以祖辈的协助照料为基础,其对子女的照料也无奈妥协为远程看顾,物质补偿、远程关注子女的学习生活等成为维系代际关系的纽带[16]。
在户籍制度之外,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劳动管理体制也倾向于将承担双重劳动的女工简化为单一的打工劳动者。一方面,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把农民工导向建筑业、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等领域,使得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和生存资源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实现家庭团聚与劳动力再生产[17],农民工特别是女工只能以阶段性返乡、多地分居打工来维系家庭的运转[18];另一方面,前述工作的专制生产管理和集中用工的宿舍体制也在女工与家庭生活间制造了割裂,与工作时长挂钩的工资体系进一步挤压了女工实践照料者身份的可能[5][19]。
还有少量研究注意到,相比于上述严苛的劳动管理体制,家庭手工业和服务业等非正规就业形态增加了农民工家庭共同生活的可能[20]。在城中村租房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庭居住、照料的需求,其中女工的双重身份得以在空间上聚合[21]。不过,伴随着城市的正规化过程(包括城中村改造、大规模人口调控、产业升级、文创活动下的执法运动等),农民工家庭以灵活的就业、廉价的居住在城市实现家庭团聚的可能性正在缩小,甚至已在城市实现扎根的流动家庭也面临着脱根危机[22]。在此趋势下,女工重新回到“进城务工—返乡照料”的二元框架内,其打工劳动者身份的获得、延续仍然以不同程度的放弃家庭照料为前提。
上述研究脉络以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排斥与公共服务资源缺位、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控制的结构性视角来理解农民工进城务工而无法留居、将家庭拆分在城乡之间的现象,女工由此陷入生产与家庭再生产劳动相矛盾的身份紧张之中,甚至被简化为相对单一的打工劳动者。尽管少量研究注意到非正规的家庭经营、城中村居住等有利于农民工家庭在打工地聚居,但随着近年来城市正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家庭得以在打工地聚居的产业和空间基础正大幅萎缩,女工也很难据此弥合双重劳动的身份矛盾。不过,这些研究都未曾注意到,近年来县域城镇化的迅猛推进特别是县域产业的发展可能对流动女工的身份建构产生深刻影响。
(二)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产业形态与女工身份
21世纪以来,随着县域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县域产业(包括房地产业、从沿海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地方特色产业等)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关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和就业机会被研究者寄予缝合农民工家庭拆分形态和化解女工矛盾身份的期望。
大量研究指出,县域城镇化尽管历经长期的演变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地方政府始终是关键推动主体,近年来由其大力推进的“土地城镇化”不仅对城镇空间也对地方产业发展和农民工家庭流动产生了复杂影响[23][24][25]。一方面,有研究指出,在县域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到城镇化的过程中,空间距离的压缩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拆分家庭的聚合提供了条件[7][26];另一方面,关注农民工性别议题的研究却发现,即使农民工家庭在县域购房特别是返乡女工实现了本地化就业,她们通常还是家庭再生产责任的主要承担者[26],因而再次面临双重劳动的身份矛盾[8]。事实上,不少研究已发现,返乡女工中的绝大部分受雇于资本化的制造业、农副业等工作,以资本逐利驱动的生产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榨取了女工的劳动时间[27],劳动过程中自主性、时间协调的缺失使得女工缺乏协调双重劳动身份的能力[28];而把生产劳动内嵌于家庭再生产的资本化的家庭代工制和以政策扶持为导向的“就业扶贫”模式尽管为女工提供了弹性劳动参与的可能,却边缘化了女工的劳动角色、减少了女工的劳动报酬,其劳动甚至成为家庭生计的补充,这不仅弱化了女工的劳动者身份,还使女工劳动参与的可持续性面临问题[29](PP57-59)[30]。
这些研究表明,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县域资本化、政策性的产业形态和就近就业机会仍然让返乡女工的双重身份(劳动者、照料者)承担呈现为时间挤压和身份矛盾,或造成劳动者、照料者某一身份的残缺,特别是女工劳动角色的偏废。这指向一个关键问题:何种县域产业形态与劳动体制能够为女工提供整合双重劳动身份的条件,并且不形成女工劳动角色的边缘化?
与上述资本化、政策性的产业形态和雇佣劳动有所不同,县域内茶叶、烟草、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农副业或手工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开展,自主性的劳动空间由此延展。然而,对这些产业形态的相关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了深度挖掘家庭经营方式的独特性与伦理文化上,尤其是注意到作为劳动力主体的父辈以“拿命来拼”的精神伦理来展开家庭经营[31],托举下一代实现县域城镇化[32]。这些研究忽视了该类产业形态和劳动体制中的性别维度,未能挖掘自雇的、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产业和非正式就业形态可能为女工实现双重劳动身份的整合打开了空间。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在上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雇经营的县域传统产业之外,新兴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也可能以与之类似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为家庭合作特别是返乡女工的劳动空间和身份建构创造出新的可能。相关统计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城区面积和商品房建设规模均不断膨胀,商品房销售额在2021年达到了181929.9亿元的高位,商品房建设浪潮已从大中型城市延伸到了县域乃至于相对发达的乡镇(2)参见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22,https://cnki.nbsti.net/CSYDMirror/yearbook/single/N2023010149。。一方面县域商品房建设带动了建筑、建材、装修等相关产业的持续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外出农民工提供了返乡就近、就地就业的机会,吸引大量拥有相关技能和从业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县域城镇化带动的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房屋装修、建材运转与销售等产业,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自雇组织劳动过程和经营业务,为工作于其中的返乡女工身份的拓展和协调提供了可能。
三、田野地点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华北Z县为田野地点,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2022年的户籍人口为57.2万人,常住人口48.2万人(3)参考Z县2022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此公报由Z县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是典型的粮食产出、劳动力输出大县。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权强县”和“土地城镇化”浪潮中,该县的发展自主权不断扩大,城镇建成区面积从2010年的16.9平方公里扩张到2021年的22.3平方公里(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22,https://cnki.nbsti.net/CSYDMirror/Trade/yearbook/single/N2023010064?z=Z005。。在新建成区面积扩张的同时,原有建成区(老旧小区、市政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在县域城镇空间扩张的背景下,近年来该县的农民家庭进入县城购买房产,县城近郊、老旧城区的居民也凭借土地的置换获得了新商品房小区的居住资格,商品房的销售额被不断推高。以该县的房地产投资额为例(见图1),当地的房地产投资额从2010年的1.8亿元攀升到了2019年的19亿元,增长了11倍。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也从2014年的14.57万平方米扩增至2019年的36.49万平方米(5)参考W市2021年统计年鉴,W市为Z县所在的地级市,此统计年鉴由W市统计年鉴委员会编纂。。县域城镇化的推进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吸引装修农民工回到县城从事装修工作的基础。
笔者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并进行了追踪调查。2021年7月,笔者通过熟人介绍结识了一对Z县的返乡装修工夫妇,并认识了他们在附近小区干装修活儿的工友以及包揽装修活儿的小老板。以此为基础,笔者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对他们的劳动、交易和生活等场景进行了参与观察。2023年2-3月,笔者回到调查地点进行追踪调查,补充和完善了以往调查过程中的遗漏或模糊信息。(6)参考W市2021年统计年鉴。

图1 Z县房地产投资金额 单位:万元⑥
如表1所示,笔者访谈的装修工大多为35-55岁的中年人,以一人制的装修男工和二人制的装修工夫妇为主,其中夫妻合作式的装修工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他们主要做的是贴砖(包括地砖、浴室与厨房的墙砖、防水等)的活计,既可以向小老板那里接活儿,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直接从商品房住户那里得到装修工作。笔者共访谈了10对装修工夫妇、3名一人制的装修男工,并对揽活儿老板、住户和建材商进行了一定的非正式访谈。通过访谈、观察和劳动参与,笔者了解了女工的工作和生活,对夫妻二人的工作分工、家庭安排、女工对劳动环节的参与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在返乡从事装修工作前,装修女工与丈夫几乎都有过在大城市装修工地打工的经历,尤其是丈夫曾经担任技术工的岗位,并且与当前的贴砖工作有关,这构成了他们能够从事自雇装修工作的技术基础。

表1 受访装修女工的基本信息
四、“多重统筹”:县域装修女工的身份呈现
县域新兴商品房住户买到的房子多是毛坯房,尚未经过改造和精装修。一套房子从毛坯状态到可以入住要经过复杂的装修步骤,主要包括主体拆改、水电改造、包立管、贴砖、刷墙面漆等程序,最后还要购买和组装家具。笔者所调查的装修工是其中负责贴砖的泥瓦工,他们所从事的贴砖工作是室内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7)为称呼的方便,后文把做贴砖工作的夫妻统称为装修工。。
笔者发现,装修工夫妇进行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男工主要负责技术性的重体力劳动,为了加快装修进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贴砖,劳动空间被限定在毛坯房内;与男工相对单一的劳动内容和较为受限的劳动空间不同,身为妻子的女工劳动内容广泛且涉及交易和经营环节,劳动空间也时常处于移动的状态。首先,在自雇的装修体制下,女工要通过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来结识有装修需要的住户,还要负责后续与住户沟通装修细节、结算工钱等经营性工作;其次,贴砖劳动可以被细分为上料、剥包装、刷胶、拌水泥、贴地砖与墙砖、打扫等内容,女工不仅要做许多辅助性工作,而且在与住户、同行沟通的过程中知晓了更多的装修细节与新技术,因而在干“杂活儿”的同时还有能力推动丈夫改良装修技术;最后,在装修劳动之外,女工在装修场地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以实现自己和丈夫的简单再生产,同时还要协商劳动时间,以流动的方式返家照看尚在乡村的老人和孩子。
基于此,本文认为装修女工有经营者、劳动参与者、家庭照料者三重身份,三重身份之间存在主次之分,相比之下,经营者、劳动者身份占据了女工绝大多数时间与精力,家庭照料者身份主要指向自己与丈夫的体力恢复与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但也尽量兼顾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照料。装修女工在这三种身份中穿梭、协商并实现统筹:一方面,女工要统筹装修工作的劳动环节和经营环节,她要把握总体上的装修进度与具体的劳动细节,既要保证时时有活儿干,又要与多位住户协商得宜不出现装修活儿的挤占,而且装修技术也在不断更新,装修女工要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的改进,以及与住户沟通后落实住户的装修要求;另一方面,装修女工要统筹装修劳动与家庭再生产责任,她们要在装修工作与照料劳动中不断协调,在安排好装修活儿的基础上,忙中偷闲返乡照看留守家庭。
(一)经营与劳动环节的统筹:女工双重劳动身份的呈现
与大中型城市的装修市场被几个大型的装修公司包揽不同,县城里很少有大型装修公司,这一非正式产业特征为返乡的装修工以自雇方式进入装修行业提供了条件[33]。装修工夫妻不仅要承担起体力劳动的部分,揽活儿、与住户沟通、结算工钱等经营性工作也被纳入劳动范畴。与建筑工地工人受到来自包工头借助乡缘关系而实施的“霸权支配”[34](P223)[35](PP11-12)的劳动体制不同,装修工夫妻的劳动有更强的自主性与灵活性,能够自主安排、协调所揽到的装修活儿,并且依托自己熟稔的装修技术与经营水平而有一定的与住户议价的能力。与此同时,近年来流行的精装修导向、住户对装修品质的要求以及来自住户的监督对装修劳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要求,装修技术和工艺也变得更为复杂。
笔者观察到,装修女工承担起多重劳动:一方面是经营性工作,包括通过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来结识有装修需要的人、与住户沟通协商装修细节并应对住户的监督、结算工钱等;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参与到装修劳动的过程中,监督送料工人上料、为男工备料、刷胶、拌水泥等,并且需要完成自己与丈夫的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由于每更换一户人家就要重新做准备工作,并且要保证每两户的装修活儿能够顺利衔接,这极为考验女工的统筹能力。
女工是如何开展上述工作并实现多重劳动统筹的呢?笔者通过观察与追溯性访谈发现,揽装修活儿的工作并不是一开始就和装修女工结合起来,两者的结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开始做装修工作时,男工作为贴砖的“主力”,手上的活儿不能停,所以揽活儿这项工作被推向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女工。以装修女工娟子为例,如果说初期她出去揽活儿是因为丈夫劳动时间紧凑,少有精力出去揽活儿,那么随着她能揽到合适的活计尤其是价钱更高的活儿,揽活儿就逐渐成了娟子的优势。笔者在2023年2月再次见到娟子夫妇时,发现揽活儿、与住户谈价钱等经营性工作已经几乎由娟子独立承担了。成功揽活儿的关键是要能够结识需要装修的住户或者知晓装修信息的人。小丽夫妇告诉笔者,他们是通过瓷砖商介绍进入县城装修市场的。小丽说:“有一年过完年包工头迟迟不给俺们打电话干活儿,我和他爸(丈夫)就只能在家待着。这时候原来认识的一个卖瓷砖的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有客户想找人给家里装修。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试试干。”小丽夫妇便通过瓷砖商的介绍开始进入家乡周边的县城做装修,在干完几户的装修活儿后,他们又结识了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大爷,他因为长居本地而对街坊邻居的情况熟识,便在之后为小丽夫妇介绍活儿,这让小丽夫妇逐步打开了局面。据笔者调查,装修工揽活儿主要通过以下几大渠道:瓷砖商、承包较多装修活儿的小老板、住户及其亲朋好友、工友等。对于装修工来说,能揽到活儿借助的是拥有信息资源的弱关系,需要拓展人际关系网络以结识有装修需求的住户。
能够结识这些人员是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维系长期合作关系并且借此延伸关系网,这需要有较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以及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按照娟子的话来说:“这些业主(住户)和老板们,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你该哄着一点就得哄着一点人家,人和人之间不就讲究交往么。”与话少木讷的丈夫比起来,娟子明显要活泛很多。对于经常给自己介绍活儿的瓷砖商老吕,娟子总是很亲切地叫他“老哥”,并在逢年过节时根据老吕的喜好挑选礼物赠送,既出自感谢之情又希望借此加强关系纽带。
揽活儿之外,娟子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应对住户对装修过程的监督并且及时结算工钱。这既需要和住户介绍各项装修细节以打消住户的疑虑,又要落实住户个性化的装修要求,还要协商装修过程产生的矛盾。有一次娟子遇到了一位刁钻的住户,不仅对他们有各种苛刻要求,还提出要降低工钱。娟子的丈夫气不过眼看就要和对方吵起来,甚至决定放弃这一家装修活儿。娟子劝住了性急的丈夫,并对住户耐心解释:“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们要的工钱是同行里价格公道的,好多人也认识我们两口子,知道我们干的活儿不出差错,你再考虑考虑。”这个住户在娟子夫妇装修的十几天,时常来看装修进度,娟子就主动和住户讲解一些装修的技术,并通过话家常的方式拉近双方的距离。一来二去,看到娟子夫妇装修技艺扎实,完成装修后这位住户就把他们推荐给自己同样需要装修的姐姐家。显然,娟子夫妇二人在面对刁钻的住户时,应对策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娟子的“讲好话”、耐心解释,他们大概很难继续做这家的装修,自然也就没有通过这位住户再结识新客户的机会了。与住户沟通融洽不仅有利于做好当下的装修工作,减少住户为难自己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住户不是孤立的,他们大多是周边村的村民或者因老城改造搬迁至商品房小区的居民,与其他购房者有着亲缘、地缘等紧密联系,住户的关系网络往往隐藏着新的装修机会。
到了结算工钱的阶段,女工更具有独特的“性别优势”。装修工遇到难缠住户或小老板克扣、拖欠工钱是常事,此时按照传统的性别观念,装修女工作为女性是可以去计较这些“小钱”的,男工若是计较被克扣的几百块工钱会被当作不够大方,有损其“男性气概”。装修工结算工钱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承揽装修活儿的小老板或直接与住户接洽。两相比较,小老板往往因为“资金周转”等缘由拖欠工钱。在向拖欠工资的老板要回工钱时,女工往往采取诉苦、纠缠等方式去和老板交涉。晓红说:“有次到了年终,老板还欠我们两三万,我那时候一天去一趟他家,去找他老婆要钱。再之后从他手里接活儿,我就让他(老板)给完工钱再干,太气人了。”与不好“磨开面子”的丈夫相比,女性的身份方便装修女工为了结算工钱而与老板不断周旋,且相对不易发生肢体上的冲突。
在具体的装修劳动中,女工也担负起重要的劳动者角色。她们不仅参与到装修劳动的各个环节,包括筛沙子、准备物料、协助男工贴砖等等,并且由于女工在揽活儿时与住户、瓷砖商、工友等各色人等有所交流,她们对装修细节、风格的变更以及住户的要求也更为敏感,因而也推动着丈夫改善自己的装修手艺。
男工加快装修进度以女工的劳动为前提,女工的准备工作要“供得上”男工的速度,女工常常还要在贴砖时协助男工。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装修工夫妇承揽到的活儿有时极为繁重,瓷砖的大小达到了1.8米×0.9米,且每一块瓷砖都有七八十斤重,瓷砖的挪动与运送往往需要两个人的共同配合,要咬着牙、舍着劲上。据笔者观察,一般情况下,一户120平方米的装修活儿差不多能给到5000元左右,工价同时根据瓷砖的大小、装修工艺的繁杂程度、住房面积等上下浮动。如果夫妻二人想平均每天有400元左右的收入,那么就要尽可能在十天之内把这户活儿干完。这样繁重的劳动需要两人密切配合且少有停歇。按照老孙的话说:“想多赚一点得加班加点地干,天不亮就走,天黑才回家,嗐,累啊……”装修劳动既琐碎又极为繁重,不断磨损着装修工特别是体力能力居于弱势的装修女工的身体。尽管女工干的杂活儿相比于丈夫的贴砖工作来说是相对次要的,但这些杂活儿却是贴砖工作的前提与装修进度的保障。
此外,由于贴砖的技术细节一直在变更,装修女工负责的劳动超越了“干杂活儿”的范畴。女工要根据住户的需求、瓷砖样式的更新迭代不断改进自己与丈夫的劳动。女工在与瓷砖商、工友的交往过程中更容易了解到瓷砖样式的变化和装修技术的改进,装修对象中的瓷砖刷胶、踢脚线切边、包装下水管道、做卫生间防水等技术都在不断更新。比如美玲夫妇在之前的装修劳动中未曾知晓一种近来流行的特制胶,这会让墙砖贴合得更为牢固,且不容易掉落。美玲正是通过询问熟识的工友才得知这类新型胶水,这为她和丈夫补某户人家掉落的墙砖时提供了便利。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常发生在装修步骤的各个环节。据此,以装修为核心的人际圈子不仅是装修女工揽活儿的重要渠道,还以提供、传递相关技术知识的方式影响了装修工的劳动过程。尽管这些技术不一定都由女工操作实施,但女工借助与住户、瓷砖商、工友的密切关系能够率先感知到装修技术的调整,并推动着男工改良装修技术。
县域内的乡村、乡镇与县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由于县城里聚集了县域内主要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无论是村里的年轻一代还是当地社会的精英,都会优先考虑在家乡的县城购买房产[36][37];另一方面,县城常住人口的流动程度较低,有较强的稳定性,这构成了装修工夫妻能够以自雇的方式从事装修劳动的社会基础。装修工可借助弱关系来不断延伸、维系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必因人口流动而造成原有关系断裂,这保障着装修劳动持续运转。笔者所调查的10位装修女工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经营性工作,其中有4-5位女工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揽活儿、与住户沟通、结算工钱等各个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保障着装修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与沟通、协商、关系扩展和维系相关的经营性劳动,不仅需要装修工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圆融周到,还需要耐心细致、能够容忍刁钻住户。在丈夫的多数时间被繁重的贴砖劳动占据时,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有较强沟通能力、能够容忍苛刻住户或上级小老板的女工便有机会在上述经营性工作中凸显出来,成为“经营者”。“经营者”角色使得女工的身份超越了干体力活儿的劳动者,推动着女工在劳动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并把控整体的劳动过程,整体统筹装修的生产劳动与经营环节。
(二)照料者与劳动者身份的统筹:双重劳动的再协商
在装修劳动之外,女工还承担了大量的家庭照料责任,不断协调着生计劳动与家庭照料。与男工绝大多数时间都要固定在“工位”上赶装修进度相比,装修女工需要不断切换劳动场景,在繁杂劳动之余照料两人的衣食住行,维系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出于节约时间和生活开支的考虑,装修工夫妇把本应是劳动场所的毛坯房转化为生活空间,以便中午稍事歇息,或者在工期要求紧张时夜宿。以小丽夫妇为例,他们“每到一户,先让孩子爸贴上(砖)一个屋,我就把锅碗搁这个干净屋,再铺上一点纸箱,方便做饭休息”。尽管装修地点多在县城新城区,他们却极少去外面吃饭,大多是提前预备食材自己做饭。小丽往往在清晨就计划好一整天的吃食,这样就可以不用再额外下楼去买菜了。装修女工穿梭于买菜做饭、盥洗衣物与切割瓷砖、刷胶、拌水泥之间,她们所从事的再生产劳动颇为细碎,却对装修劳动的运转不可或缺,保障着二人的营养水平与有限的休憩空间。
尽管事实上女工承担了更多的再生产劳动与照料责任,但繁重的装修劳动还是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性别分工。由于装修劳动经常要相互配合,为了能够压缩休息时间而便于竭力赶工,阿敏夫妇形成了她早起做饭、丈夫志辉洗衣的分工,到了晚上,志辉会承担起剩下的再生产劳动,让阿敏早一点休息。值得注意的是,当场景由私人转向公共、“后台”转向“前台”,向着平等化方向发展的性别分工可能会被扭转,女工会重新回到传统性别分工的身份框架中。笔者曾观察到这样的场景:当志辉的工友来做客时,志辉一改以往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角色,反而不断催促妻子做饭时多添几道菜、把零碎的物品收拾好,通过支使妻子做事来构建自己“霸权型”的性别气质。男性在性别分工方面“现实妥协”,或又在其他场景返回到传统的性别分工框架,男性气质调整嵌入其个人处境乃至微观的生活和劳动情景[15]。
女工不仅在打工地承担了较多的再生产劳动,更是利用工作临近的便利,尽可能地照顾县域内的子女以及不时回村看顾仍在村中的老人。装修工夫妻的年龄一般在35-55岁,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多已度过了需要随时照看的年纪,子女们大多出村求学或被“托管”给年迈的祖辈,女工则把重心放在了装修劳动上。只有在子女升学等关键时期,女工才会完全放下工作回到家中陪读一段时间,投入较多时间陪伴、照顾子女。不过,由于打工地的临近与中小城市对户籍管制的放松,笔者发现部分年轻女工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在县城里继续读书。此类装修工夫妇特别是女工利用劳动时间的灵活性,在工期不太紧张、外出揽活儿或其他工作的间隙,抽出时间尽可能做到对子女的照料、陪伴以及学习功课上的监督。以娟子为例,娟子夫妇送儿子读了当地县城的高中,为了方便装修工具的存放与照顾儿子的便利,她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平日里儿子读寄宿学校,娟子夫妇便在往返方便的情况下晚上从装修地回来休息。“小帅的学校几个星期放一次假,放假的那几天我就少干会儿活儿,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什么的,要是活儿紧(工期紧张),我就提前在冰箱里预备好吃的,他回来自己煮着吃。”(娟子)部分装修工夫妇则仍然让孩子在离家较近的乡镇读书,在寒暑假的时候再把子女接来团聚。还有一些装修工夫妇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读大学或也已开启了自己的打工生涯,他们则设法参与照顾子女留在县域内的小家庭的生活。
与子女受到较多关注相比,留守老人的照料需求被一再压缩。小丽无奈地向笔者倾诉:“真的既没有时间又没有能力再管他们(老人),活儿这么忙,能逢年过节的回去看看他们就已经很好了。”笔者对来县城办事的留守老人孙爷爷(某装修工小强的父亲)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孙爷爷所言:“孩子们大多时候几个月也不回来一趟,这几年我种不动地了,他们也只是打电话说请人收拾吧,没再说别的。”孙爷爷的语气中尽显落寞,既期望儿子儿媳能够多陪伴自己,又因心疼他们干装修活儿过于劳累而不愿再麻烦他们。不过,由于装修劳动的地点在县域之内,倘若留守老人在家突然有急事,装修工夫妻还是可以及时赶回。小强曾对笔者说:“有次我爹得了胃病,晚上痛得睡不了觉,这里的活儿赶得太紧,我回不去,让孩子妈回去了几天,带老人挂号、住院啊啥的。听孩子妈说,才几天啊,人都瘦佝偻了。”能够在父亲急病时侍候在侧,也稍稍弥补了打工夫妻内心对老人日常照顾不足的歉疚。
因此,自雇的装修体制使得装修工夫妇有一定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空间去协调装修劳动与再生产劳动,打工地的性别劳动分工也呈现出一定的“去传统化”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可能出于装修劳动的实际考量,男工对家务劳动的承担往往是为了节约时间以及在妻子忙不过来的时候搭把手。把视角转向装修工在县域内读书和生活的子女以及仍在村中留守的老人后,相对灵活的装修劳动和拉近、重合的打工地与家乡距离,为装修工夫妇尤其是装修女工兼顾家庭的照料需求提供了可能。但装修工对家庭照料的兼顾仍较为有限并性别化为女工的劳动,主要投向承载了家庭未来希望的孩子身上,农村留守老人的照料、情感需求则相对被忽视。
五、县域城镇化与家庭发展:装修女工“统筹者”身份的建构
(一)家庭发展责任:女工劳动参与的内在动力与打工者身份延续
笔者对装修女工进行访谈时尝试追溯她们的生命历程,以理解其身份建构过程和背后的原因。这些装修女工大都有因生育和抚育压力而留守的经历,之后在面临家庭发展压力时跟随丈夫外出打工,并且在县域兴起装修产业的背景下回到家乡从事装修劳动。她们的流动历程呈现出阶段性的复杂特征,显示出已婚女工在家庭生计和照顾之间的双重身份紧张,但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发展需求最终确立起装修女工作为打工劳动者的身份定位。
结婚成家的确把女工导入家庭轨道,并且女工需要承担生育、抚育等家庭责任,甚至还会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依赖丈夫收入。被访装修女工的初婚、初育年龄均不超过25岁,且绝大多数的女工不止生育了一个小孩,生育多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也较短,意味着她们早早地承担起了以家庭照顾为主的身份角色,并居于丈夫外出务工、自己在家留守的性别劳动分工之内。一些被访女工在这一时期也从事过就近打零工、种地等生计劳动,但家庭支出的大头仍主要由丈夫承担,她们的收入仅仅被当作家庭生活的补贴,打工劳动者身份被边缘化。
然而农民工家庭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需求。家庭照料需求主要集中于女工生育与随之而来的幼儿照料、孩子升学的关键时期以及部分祖辈的身体状况弱化无法再照看孙辈或自身也需要照顾的阶段。当度过这一时期,随着子女的成长,特别是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推进,子女教育、婚姻成本的日益增长,巨大的家庭绵续与发展需求越过照料责任成为更为迫切的压力,促使女工艰难地进行身份切换。
对于身处中年时期的装修女工而言,近在眼前的家庭发展压力使得她们外出打工成为“必需”。蕾蕾表示:“我在两个孩子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孩子爸出来打工了,又想盖房子又得供学生,光孩子爸一个人的工资不够。”为了生育、抚养两个孩子,蕾蕾的留守生活长达十年。丈夫的收入在减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外,能够用来储蓄的部分实在有限。为了能够更快地建起楼房,为儿子未来结婚做准备并供两个孩子继续读书,蕾蕾没办法更久地陪伴孩子成长。这让她产生了巨大的愧疚感,但外出打工也同样是建立在“为了孩子”的基础上,为孩子准备发展条件成为女工这一时期重要且艰巨的任务。这些发展条件不仅包括让子女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更要为儿子将来的结婚成家“打基础”。据笔者观察,在村里盖新房、准备彩礼以及在县城购房已经成为当地青年进入婚姻的门槛,并转化为父辈的沉重负担。以装修女工成霞为例,她生育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纪,女儿还在读大学。成霞曾不止一次向笔者提及身上肩负的责任:“现在孩子们的大事都还没办,我得继续干下去,能赚一点是一点,多赚点就少发一点愁。”不断加大的代际投入压力使得女工的外出务工变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女工推向收入更高的装修行业。
由此可见,家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与发展需求,当家庭从生养进入子女教育和婚育阶段,家庭照顾压力便逐步让位于发展压力,特别是在县域城镇化推高了家庭发展压力的背景下,女工也在进行着身份切换,从“持家者”转化为“养家者”,以绝对主导的打工者身份为子代的发展做积累。
(二)县域自雇装修劳动体制:女工劳动参与的自主空间与经营者身份建构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县域商品房市场的兴起为装修工返乡提供了产业条件,该产业独特的自雇装修劳动体制则为女工提供了劳动参与的自主空间和身份建构基础。县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在短期内兴建了大量商品住宅,使得装修工作激增,不仅吸引着装修工返乡,而且让装修工在县域的长期就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晚近兴起的县域商品房市场与装修产业并未被大型装修公司垄断,而是呈现出较强的非正式特征,装修工夫妇能够以自雇的方式进入装修行业,在与住户、小承包商、建材商等主体的经营互动中开展装修劳动,为装修女工经营者身份的生产提供了条件。笔者将首先说明自雇劳动体制为何倾向于选择以装修工夫妻为劳动单位,接着解释夫妻制的自雇劳动体制如何帮助女工拓展经营者身份,并在装修工作中实现劳动和经营身份的统筹。
笔者发现,装修工的夫妻式劳动单位在以下三个方面高度契合自雇形态下的装修劳动。第一,自雇装修劳动需要一人贴砖、一人备料,适合夫妻间的性别分工。如果是两个男工,在备料工作上花时间会拖慢贴砖速度,并且有限的装修空间有时不支持两个男工同时贴砖,容易出现劳动力闲置的情况。若一个男工另加一个打杂“小工”,则由于备料工作不需时刻展开,小工的时间利用也未能充分。相比之下,装修女工则可以在备料、贴砖以及揽活儿、与住户沟通的多重劳动中灵活穿梭,最大限度地保证在工期内完成装修。第二,夫妻制装修工极少会面临监督与工钱分配的困境。为家庭积累的共同目标把二人置于紧密连接的共同体中,装修工夫妇不分你我地为家庭目标努力,很少需要进行薪资分配与劳动监督。而且除住户或承揽装修活儿的老板会对工期提出要求外,装修工夫妇为了尽可能地为家庭积累财富,自身也有极强的动力卷入这场赶工劳动中,在每户装修工钱一定的基础上极力压缩工期,以便尽快开启下一户的装修劳动。第三,由于进行装修的空间也部分承载着装修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做饭、休憩等私领域的活动更适宜在家庭的单位下开展。默契合作、情感纽带、极高的稳定性是装修工夫妇从事装修劳动的根本社会力量。在配合得当的情况下二人甚至能同时干两户装修活儿,比如男工在某一户贴砖时,女工则会去另外一户监督上料、准备装修工具。部分装修工夫妇还会筹备两套装修工具,在节约工时的同时也占住了两户装修活儿,从而减少无装修活儿可干的情况,这些优势是双男工或一个男工再加雇用他人做帮手的劳动单位所难以企及的。
夫妻制的自雇装修体制在为装修劳动提供效率的同时,也通过劳动分工特别是揽活儿和与住户沟通等经营环节及其要求的经营意识、沟通协调、关系维护等业务能力,扩展了女工的劳动和经营空间。对于装修工而言,如果干完一户活儿没能及时找到下家,就只能干等甚至要降低工钱才有活儿干。因此当装修女工承担了揽活儿这项劳动时,那些有经营意识的女工便通过拓展人际网络、“经营”住户关系来结识更多有装修需求的人,并把丈夫过硬的装修手艺推销出去,以此逐渐积攒口碑,承揽到价格较高的活计。蕾蕾的话清晰地表达了“经营”住户关系的重要性:“这些业主们(住户)都有亲戚朋友,连带的特别多(指给自己家做完活儿,又把装修工介绍给同样需要装修的亲戚朋友等住户),有一个老板让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干了四户,这样我们俩月的活儿就有着落了。”那些能说会道的“经营者”们的关系网络有瓷砖商、包装修活儿的小老板、住户、卖装修料的老板等,她们的经营劳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夫妻二人一直有装修活儿干。
在女工经营的关系网络中,与住户的沟通互动和关系维护不仅影响了装修工夫妻能否以及何时接到装修工作,还直接影响着装修劳动的进展和后续工钱的结算。与大中城市工地上的装修劳动不同,县域装修中住户作为“第三方”也介入劳动之中,频繁地提出装修要求的同时还监督劳动进程。因此与住户沟通以满足其个性化装修需求成为自雇装修劳动的重要一环,并直接影响到了住户验收装修成果、结算工钱是否爽快和顺利。能够“将心比心”、理解用户诉求、耐心解释装修原理与细节、把话题转移到生活场景中以拉近双方距离等,就构成了装修女工的独有优势。从装修劳动的整套过程来看,如果说男工是勤恳、专一的劳动者,那么女工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劳动“营销”出去,以获得住户的认可与满意。
以上分析表明,夫妻式自雇劳动体制不仅为装修劳动提供了极高的效率,还为女工的身份扩展与统筹打开了自主的空间。我们看到,装修女工不仅参与到装修劳动的各个环节,与男工一同进行家庭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承担了自雇装修劳动中极为重要的经营环节,她们利用自身的性别优势扩展了“经营者”身份。这一身份建构和扩展超越了以往研究对建筑行业女工从属身份的定位,新的“经营者”身份并非可被男工轻易兼顾,她们不仅统筹了自身的劳动者和经营者身份,还在一定程度上调配和统筹了男工的劳动。
(三)空间压缩与灵活劳动:女工家庭照料的时空基础与照顾者身份修复
在县域城镇化带动房地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夫妻装修工的返乡拉近了打工地点与家庭的距离,自雇装修劳动体制也给予了一定的时间弹性,让装修女工得以从繁重的劳动中抽身兼顾家庭照料。
笔者发现,县域房地产业兴起之后,装修工的工作范围集中在家乡及周边几个县城,他们大都购置了车辆。部分装修工哪怕资金欠缺,也优先购买二手车。装修工买车主要出于工作目的,却也有帮助农民工夫妻特别是女工兼顾家庭照料的考虑。有一辆车有助于承揽到距离更远的装修活儿,既方便劳动工具的运送,又便于在出租房和装修地的往返。与此同时,装修地点的临近和车辆的便利还可以让他们能够及时回家照看老人、孩子。小丽讲述了购车的便利性:“光一个县城哪够这么多人干活儿呀,我们去过西边那个乡镇干活儿,这里没活儿的时候就去那干,有时候那给的价钱还更高。而且有车多方便,想去哪去哪,没活儿干就回家,说走就走,不用去挤大车了(大巴车)。”如果工期不是很紧张,拥有车辆的装修工返回家中可以说是“说走就走”。装修工能够选择下午早些下班再驱车两三个小时赶回农村老家,第二天一早再开车返回县城劳动。空间距离的拉近与交通工具的便利使得装修工时时返家成为可能,为其兼顾家庭照料需求提供了条件。
不过,与返乡前的远距离、长时间务工相比,尽管上述时空条件为装修工兼顾家庭照料提供了便利,但多数装修工夫妇回老家的次数并不频繁,表明他们当前的主要目标是为家庭积累财富,家庭照料通常局限在对子女的关照、乡村的人情往来以及其他突发的紧急事件。笔者看到,子女放假回家、秋收、乡邻亲属的红白喜事是装修工返回家中的主要原因。当忙完这些事件之后,他们再匆匆赶回县城继续从事装修劳动。如果子女的寒暑假较长,装修工夫妇便把孩子接到县城,在出租房以及装修场地获得一段时间的家庭团聚,女工也得以再次承担照顾子女的家务劳动和责任。
因此我们看到,县域房地产业的兴起拉近了装修工工作地点与家庭的空间距离,夫妻式自雇装修劳动体制则给予劳动者一定的时间弹性,在就近装修的必备工具——车辆的帮助下,装修工夫妻能够在前后装修工作的间歇、子女放假在家的假期以及家乡发生紧急事件之际快速返乡,兼顾家庭照料和参与家乡人情往来,女工的照顾者身份由此得到修复和延续。
六、结论与讨论
自20世纪末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以来,流动女工的身份建构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已有大量研究在“进城务工—返乡留守”的二元分析框架下,揭示了流动女工所面临的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相互挤压的矛盾,呈现了女工在打工劳动者身份和家庭照顾者身份之间的尖锐冲突。事实上,外出女工通常为了延续打工劳动者身份而牺牲对家庭的照料,返乡女工则因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而边缘化劳动者身份。流动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循环迁移,令其身份在二元框架下不断摇摆,身份紧张、特别是身份切换过程中的张力和代价成为难解的问题。近年来县域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化解流动女工的身份统合难题开辟了可能空间。一些研究对就近、就地城镇化和相关就业机会缝合农民工家庭的拆分形态以及化解女工的身份紧张问题寄予厚望。但由于县域产业的资本化运作、对劳动过程的刚性管理以及政策性产业的低报酬和难持续等问题,返乡女工仍然陷入双重劳动的紧张和困境之中,甚至造成了部分女工打工劳动者身份边缘化的后果。另一些研究虽然注意到某些县域产业以非资本化特别是以家庭化的方式进行组织,却由于缺乏性别分析视野,并未考察该类产业形态对返乡女工身份建构的深刻影响。
本文基于对华北Z县自雇装修工的实地调查,发现县域城镇化带动的房地产装修业因其夫妻式自雇体制的产业组织形态,让装修女工建构起“统筹者”身份。自雇装修体制以夫妻为劳动单位,劳动和经营环节相对分割,经营环节强调与本地住户、建材商、分包商等主体的沟通协商、关系维护等业务能力,极大地扩展了女工劳动的经营面向,让她们得以统筹劳动者和经营者身份;与此同时,自雇装修体制的劳动时间相对灵活、工作地点与家乡临近,让女工得以兼顾家庭照料和人情往来,实现了家庭生计和照料的统筹。
装修女工的“统筹者”新身份不仅让前述二元框架下的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紧张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更在传统的打工劳动者身份之外发展出经营面向,凸显了流动女工参与体力劳动之外的技术性、互动性、高回报劳动的巨大潜力。正如上文所言,装修女工“统筹者”新身份的出现,来自县域内装修产业的夫妻式自雇组织形态的劳动灵活性和空间临近性。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推进了学界对流动女工身份建构的既有理解,还为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产业发展与女工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借鉴。
事实上,本文的案例表明,县域产业形态的自雇组织特点和空间临近布局,有利于女工拓展劳动参与的经营面向以及统筹多重身份。从本文的案例出发,可以看到,产业的组织形态及其空间布局对流动女工的身份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正如大量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城市产业(如工厂流水线、建筑包工队、平台家政工)因其资本化的劳动体制对劳动过程的刚性规制以及远离农民工家庭的空间布局,不仅倾向于将流动女工去技能化为简单劳动者,还压制了女工统筹家庭日常照料的可能。这种产业组织形态和空间布局方式成为流动女工持续面临双重身份紧张的结构根源。在城市产业之外,近年来县域城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为返乡女工缝合家庭拆分形态以及化解双重身份紧张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仅改变产业的空间布局不足以解决女工的身份张力。因为县域内产业的资本化运作仍然限制了绝大多数女工的时间灵活性和劳动自主性,让她们陷入就地版的“务工—照顾”二元框架的双重矛盾之内。因此,在县域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同时重构产业的组织形态和空间布局,让女工在简单打工劳动者身份之外具有劳动自主性特别是能够从事技术性和经营性等劳动,让她们在参与劳动的同时也能统筹家庭照顾,应成为后续探讨女工身份建构的焦点,也应成为具有性别意识的产业政策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