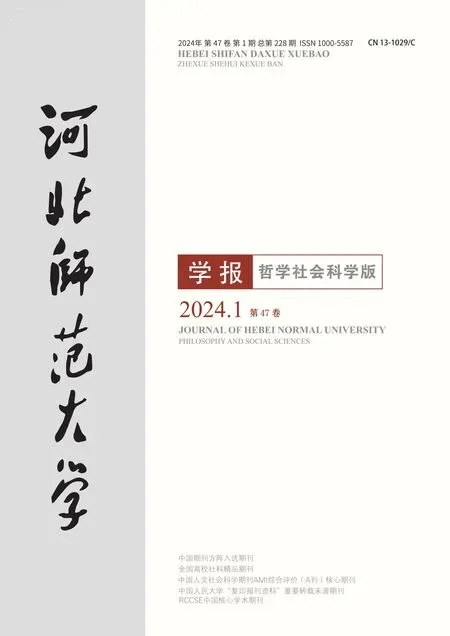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
——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孟庆雷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动荡的时期,当时的战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然而在艺术上,这一时期却充满了生机。宗白华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大一统政权瓦解之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使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心,也形成了南北方文化的鲜明差异。《北史·文苑传》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2)李延寿:《北史》卷8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44页。事实上,不仅文学如此,在艺术领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南北方差异。而且,即使同在北方地区,由于长时间的割据,各地的艺术也都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河北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在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中也逐渐表现出自己的艺术风格。
一、民族冲突与融合中的艺术变革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打破了两汉四百年的统治秩序,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动荡时期的序幕。这期间尽管也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旋即又陷入到更残酷的动荡之中。自西晋八王之乱起,中国北方先是经历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接着又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的更替。持续不断的动乱不仅极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陷入困顿,也彻底打断了两汉艺术的雅化进程,两汉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与宏大强劲的艺术风貌也成为岁月中的绝响。
稳定统一秩序的崩溃对艺术发展来说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持续混战也带来了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艺术开始与汉族艺术融合在一起。尽管持续的动乱导致整个北方地区一片萧条,文化水平整体上落后于南朝,然而地方艺术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相对于南方士族阶层刻意创造出来的典雅艺术风范,北方地区的艺术家则更多地依靠其自然的生命本色创作,那是一种真正源自生命的纯真艺术,它用粗犷豪气的笔触诠释了真正的自然精神。
在长期动乱之中,河北地区的汉族地方豪族势力纷纷结寨自保,同时又积极参与进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互相利用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是士族政治的巅峰时期,无论南北方都涌现出大量的士族世家,它们垄断了上层政治权力。然而士族世家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们源于汉末的豪族。“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3)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页。由于豪族本身具有非常强的经济、政治实力,当统一的政治秩序被打破之后,它们往往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河北地区逐渐形成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这些汉人世家对于传承汉代的文化艺术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清河崔氏的代表人物崔玄伯、崔浩父子,范阳卢氏的卢玄、卢渊祖孙,都以书法著称于当世。崔氏父子擅篆、草、隶、行书,卢氏继承钟繇的书法风格,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4)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章程书即后世之楷书,行押书即行书,因而卢氏工于铭石书、楷书、行书。
由于世族子弟往往担任朝廷高官,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提升自己的文化艺术水平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崔玄伯、崔浩父子长期担任北魏高官,诸多诏书草令出自他们之手。“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魏书·太祖纪》)(5)魏收:《魏书》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页。崔玄伯父子在北魏典章制度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北魏的汉化。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往往也注意吸收汉族文化以提升本民族的素质,并进而加强民族融合。在这方面即使以残暴著称的石勒也非常推崇儒家文化,在位期间提拔张宾、程遐、续咸等人予以重用。前秦雄主苻坚则重用汉臣王猛,通过王猛等人推行汉化改革,促进文教发展与民族融合。北魏太祖拓跋珪亦在创制之初倚靠崔玄伯父子建立各种制度。最著名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排除鲜卑守旧贵族的干扰,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后又通过强力措施推行汉制,极大地推进了境内各民族的融合速度。在汉化运动中,汉民族的典章制度逐渐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接受,汉族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也被统治者所青睐。相对而言,文化程度较低的内迁胡人,对于汉族艺术的接受更为迅速。
民族艺术的融合不仅体现在上层贵族中,在下层百姓中同样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状态。各少数民族内迁后,本民族的艺术被带进河北地区,如舞蹈艺术中就有大量胡舞传入并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成为当时流行的乐舞。而流行于汉地的一些民间艺术也开始被其他民族接受,有些甚至流入宫廷。例如傀儡戏本是民间木偶滑稽表演,早在汉代就作为百戏的一种流行于民间。进入北朝之后,这一戏剧表演仍然深受当时人们喜爱。郭茂倩《乐府诗集》在《邯郸郭公歌》序中引《乐府广题》记载:“北齐后主高纬,雅好傀儡,谓之郭公。”(6)郭茂倩:《乐府诗集》卷8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0-1221页。尽管后主高纬以行事荒唐闻名,但傀儡戏能进入宫廷说明其影响力不小。
总之,尽管这一时期一直处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但也带来了各民族的迅速融合。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纷纷将各自的艺术特色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新艺术创作局面。由于战乱经常造成局部地区只能内部交通的状况,河北地处游牧与农耕文明交界线的地理位置再次体现出其独特价值,因而在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河北地区的地方艺术特色也不断成长。
二、尚侠精神的张扬
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游侠就已经成为当时非常受关注的文化现象,《韩非子·五蠹》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19,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9页。,把儒、侠对举显示出游侠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上一股重要的力量。之后游侠一直活跃于秦汉的历史舞台上,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概括了游侠的主要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8)司马迁:《史记》卷12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13页。游侠的主旨是扶危救困,这一点与舍身取义匡扶人国的刺客相似,有时候二者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因而荆轲有时也被视作侠义精神的代表。
游侠的兴盛不仅需要特殊的政治空间,同时也需要合适的地理空间。游侠以“游”命名,突出了其存在的基本方式,他们依靠自身的武力过着四处游荡、变动不居的生活,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也只有在到处游走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游侠对于社会规范而言,始终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他们以自己狂放的生命冲动冲撞着森严的社会秩序。游侠的兴盛与发展受制于社会秩序与地理环境:在大一统的社会中游侠的力量被中央权力所压制,往往无法得到释放;在分裂割据的年代,游侠则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能够迅速发展成重要的社会势力。在地理环境方面,由于游侠经常进行大范围、长距离流动,因而越是环境复杂、面积广阔的地域越有利于游侠的生存。
游侠文化很早就在河北地区广泛传播。两汉时期尚侠就已成为河北文化的重要特征,得益于荆轲刺秦王等故事的大量传播,河北初步建立了尚侠的文化传统。魏晋北朝时期的动乱时代进一步释放了世人心中的强力意识,河北地区倚山抱河的地理环境则为游侠活动提供了自在的空间,因而河北地区的游侠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游侠尽管在汉代非常活跃,却一直受到官方的打击,如景帝就大量诛杀游侠,武帝则将著名游侠郭解族诛。然而当汉末纲纪松弛之后,游侠再度活跃起来,甚至有些地方豪族和官方人士也加入到游侠行列。如《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记载刘备少年时“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9)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9页。;《世说新语·假谲》中则记载了一起曹操与袁绍同为游侠的故事:“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10)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9页。刘备生长于河北,袁绍则后来成为河北的实际掌控者,曹魏政权同样建基于河北,显然河北盛行游侠风气并非偶然。
从曹操、袁绍的轶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游侠除了扶危救困的仗义之外还有少年意气的一面,很多时候做事情只凭自己的兴致,而不过问善恶。“游侠的人格既是那么的复杂,它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难以一言评说;游侠的行为既是那么的爽朗、放达,以至流于乖张,然而它们却能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千载之下,几乎不待理智的消解和知性的过滤。”(11)汪涌豪:《中国游侠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游侠的强悍生命力与恣意任性的行为方式,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动荡时代之中得到极大的释放,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了河北地区的文化艺术,使该时期的河北艺术呈现出强劲的原始生命冲创力。
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使个体充分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如游侠一样来去自如,行侠仗义甚至扶助危国;另一方面陷入困境时,他们往往幻想有游侠来解救自己于危难之中,这一点即使上层贵族有时也会流露出来。如曹植在《白马篇》中热烈称颂游侠儿的为国捐躯:“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野田黄雀行》中,曹植则幻想有人来解救陷入罗网的黄雀:“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12)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13、308页。曹植诗中列举游侠儿首推幽、并,由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并州并入幽州,因而所谓幽、并其实本是一州。曹植曾长期生活于邺城,对当时的游侠人物及事迹并不陌生,少年时亦曾经梦想仗剑策马游侠赴义。《三国志》记载了他初次与邯郸淳交往时的情形:“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1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21,第449页。胡舞、跳丸、击剑,这正是当时游侠儿常从事的活动,作为王府贵公子的曹植当然不可能真的去仗剑出游,但是却不妨碍他心中的游侠梦想。因而,当他后来陷入困境时,自然也幻想有跟少年时自己一样急公好义的游侠来救自身于罗网之中。
如果说曹植的游侠观念还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倾向,更侧重于游侠对正义的张扬,那么随着时局越发艰危,个体对道义的坚持就越来越难;对于游侠儿来说,本来就非遵纪守法之辈,乱世之中更容易发泄其内心暴力的一面,意气用事、快意恩仇开始成为游侠的主调。故《北齐书·高乾传》中记载,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高乾所结交的朋友亦是类似,如孟和同样“少好弓马,率性豪侠”。(14)李百药:《北齐书》卷2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7、203页。少年游侠往往以违法犯禁为趣事,追求一时之快感,因而更多的是在任意张扬自己旺盛的生命意志。
有时候游侠的强悍意志也会转为负面作用,他们会成为横行乡里、劫掠百姓的法外之徒。“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檦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檦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15)魏收:《魏书》卷53,第793页。李波恃宗族强力成为法外之徒,引得乡里“公私成患”,由游侠转换为地方豪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流传的民歌《李波小妹歌》则提供了不同于官方史书的视角:“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16)魏收:《魏书》卷53,第793页。民歌热情地歌颂了李波小妹的高超武艺,女游侠的英姿跃然纸上。当然,在这首民歌中只称颂了李波小妹的武技,并没有涉及她是否正义的问题。或许这正是当时游侠的特点,人们推崇游侠更偏重于游侠强悍的武力与自在自由的生活方式。
游侠的来去无踪、任意而行与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极为相似,来自草原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一直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游荡生活,因而游侠的行为方式很容易在不同民族之中获得认同感,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的游侠文化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地刚健强劲的性格特点,这种追求强健力量的文化精神深入到艺术领域,使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有浓厚的强力色彩。
三、胡风与胡乐的兴盛
魏晋北朝时期,无论文化还是艺术都深受战乱的影响,战争改变了汉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两汉长时间的稳定统治使来自游牧民族的艺术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艺术逐渐融合,两汉艺术的雄浑、强健、壮丽在河北地区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中山王等诸侯王墓的出土器物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中央皇室典雅的审美文化趣味体现了河北地区的贵族艺术品味。然而,汉末以来的政治动荡与战争打断了这一统一化的进程,河北地区的艺术再次回到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融合的状态。漫长的战乱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沿幽燕地区南下,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化,以塞外民族乐舞为代表的胡乐开始进入河北地区并广泛传播,因而在这一时期胡风与胡乐得以兴盛起来。
在曹魏时期,曹氏父子曾经一度重新建立雅乐文化制度。“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尝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哥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17)沈约:《宋书》卷1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0页。汉末动乱使得中央音乐机构遭到破坏,曹操只能从民间搜寻曾经在乐府机构任职的音乐人才。杜夔等人所重新编撰的先代古乐大致仍为汉代乐府旧题,但是也吸纳了一部分当代的作品。雅乐本身历代皆有沿革,不唯曹魏时代,汉初的宗庙雅乐创制亦多采楚地民歌,杜夔亦是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有所损益。
曹魏正式建国之后,曹丕重新厘定了宗庙雅乐的范围。“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宋书·乐志一》)(18)沈约:《宋书》卷19,第360页。由此可知,曹丕只是将大多数汉代雅乐改换名称,并没有特别创制新的曲调,对于部分陈旧的歌词则让王粲进行了重新谱写。
曹魏对雅乐的重新整理使汉代雅乐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然而随着新战乱的到来,这一成果最终也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烟消云散。南渡的东晋王朝雅乐丧尽,祭祀时礼乐不全,以至于尚书在询问太常以何种音乐祭祀时,贺循回应:“魏氏增损汉代,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19)房玄龄等:《晋书》卷2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9页。曹魏所整理的雅乐在东晋已经荡然无存,无人能晓,直到淝水之战后才辗转从北方收集到部分乐师而重建东晋之雅乐。在北方,雅乐同样难逃浩劫:“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20)房玄龄等:《晋书》卷23,第449页。永嘉之乱时乐官与乐器都被刘渊、石勒所虏获,然而刘、石亦没有好好保存下这些乐师及相应的歌舞,以至于乐师们四处流散。
尽管后赵石勒收留了部分雅乐乐师使雅乐得以保存,但石虎上台之后大肆扩张乐师队伍,大量夹杂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及其他百戏表演都被纳入进来。据东晋初年陆翙之《邺中记》记载:“虎大会,礼乐既陈,虎缴西阁上窗幌,宫人数千陪列看坐,悉服饰金银熠熠。又于阁上作女伎数百,衣皆络以珠玑,鼓舞连倒。琴瑟细伎毕备。”(21)陆翙:《邺中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0页。石虎所谓的礼乐在很多时候就是乐舞大会,纯粹为娱乐而作,并不具有雅乐的政治意义。不仅如此,石虎还别出心裁地设置女乐官部属,女乐的设置更不具有任何政治功能,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享受欲望。
在正会中,石虎的乐礼表演同样是各种形式的混杂。“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縆、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橦,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橦著口齿上,亦如之。设马车立木橦,其车上长二丈,橦头安横木,两伎儿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22)陆翙:《邺中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63册,第309-310页。与前代正会的庄严肃穆相比,石虎的正会就是大型娱乐表演现场,这固然显示了石虎政权的荒唐滑稽,但如果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却又是一种历史必然。后赵是羯族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上层统治者的文化素质并不高,有学者考证:“羯人不是被康居人所征服的南部农业居民——索格底亚那人,而是康居(羌渠)游牧人。西汉时期,康居‘东羁事匈奴’,因而可能有一部分康居人随匈奴人东来,转战于蒙古草原,以后又随之南迁,分布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一带。”(23)童超:《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羯人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时间并不长,还没有建立起高雅的文化品味,他们对于雅乐并无太多兴趣,而更喜好各种世俗的艺术表演。因而,民间百戏就成为石虎政权所青睐的对象。
后赵统治者对乐舞的态度昭示了后继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审美风尚,他们更倾向于当时的民间艺术,并对各民族艺术兼收并蓄。而且,很多少数民族民风比较开放,对于歌舞有着天然的兴趣。例如,《魏书·高车传》中对高车的记载:“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24)魏收:《魏书》卷103,第1561页。高车一族经常举行歌舞集会,在歌舞集会上无论男女老少都参与进来。这一情形或许并不局限于高车,举凡羯族、鲜卑、氐族、羌族等各少数民族可能都有类似集会。这种歌舞集会的传统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喜欢喧嚣热闹的场面,因而对于各民族奇歌艳舞更加感兴趣,于是远自西域的胡腾舞、龟兹舞等都纷纷传入。“于隋唐时期逐步盛行起来的《九部伎》《十部伎》中,绝大部分乐舞都已经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并且,所有外国传入的乐舞、我国少数民族乐舞、传入乐舞与中原乐舞融合而成的乐舞,除《扶南乐》之外,其余如《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高昌乐》的多部乐舞‘都是在北魏、北齐、北周三朝传入内地。’”(25)周大明:《河北舞蹈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胡风胡乐的传入已经相当普遍,而统治者的个人爱好则更进一步带动了这一风气,在这方面河北地区的统治者石虎、北齐后主高纬都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胡风胡乐的传入并不仅仅在音乐舞蹈领域起到重要影响,它对于其他艺术种类也有潜在的影响。在绘画、雕塑、陶瓷等领域,大量关于胡乐胡舞题材的作品显示了其跨领域的影响力,也显示其深刻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路径。不过,胡风胡乐也存在不断雅化的问题,大量异域乐舞在流传过程中逐渐雅化,成为后来统治者建构雅乐文化的直接素材。
四、佛教带来的新审美文化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佛教在东汉就传入中国,但是它的快速发展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迅速传播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使当时的人们在茫茫乱世中获得了一份心灵的皈依。“西晋天下骚动,士人承汉末谈论之风,三国旷达之习,何晏、王弼之《老》《庄》,阮籍、嵇康之荒放,均为世所乐尚。约言析理,发明奇趣,此释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祖尚浮虚,佯狂遁世,此僧徒出家之所以日众也。……至若贵人达官,浮沉乱世,或结名士以自炫,或礼佛陀以自慰,则尤古今之所同。”(2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4页。动荡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心灵的慰藉,佛教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信仰的支撑。而魏晋以来玄学的发展又给予佛教传播以思想契机,使其能够在世族名士之间流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吸收了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中的部分元素,形成了有异于印度本地佛教的汉化佛教,并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文化的因子。佛教建筑也在这个‘消化’‘营养’的过程中,渐渐改变了其在印度和中亚地区的面貌,成为具有‘中国个性’的建筑形式,和佛教本身一起,经历了一个外来建筑形式为主到本土建筑形式相一致的本土化过程。”(27)汪小洋:《中国佛教美术本土化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事实上,不仅佛教建筑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本土化,佛教艺术同样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而魏晋南北朝正是这一本土化的关键时期。在河北大地上留下的大量该时期佛教艺术珍品,向我们诉说着它们东传之后生根、发芽、开花的灿烂过程。
魏晋北朝时期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普通百姓往往都笃信佛教,河北地区的统治者亦多信奉佛教。从后赵石勒开始,佛教就为统治者推崇,当时著名高僧佛图澄即深受石氏叔侄敬重,被奉为国之大宝,而佛图澄也是深度参与了后赵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深刻影响了后赵国家政策的制定。如石虎即位后为显示对他的尊崇:“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28)房玄龄等:《晋书》卷95,第1660页。由于佛图澄在后赵的显赫地位以及对佛学思想的玄妙解读,在其传法的三十余年间发展了大量信众,不仅门徒上万,还培养了道安、法雅、法汰等著名佛教弟子,进一步弘扬佛法。
之后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同样礼敬佛教,将其视作笼络人心的重要工具。自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就信奉佛教,并以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管理全国僧人。佛教因此开始在北魏都城平城发展,法果赴都城任职也说明在北魏时期河北地方的僧人领袖逐渐进入中央政权。之后尽管有太武帝的灭佛活动,但文成帝即位之后佛教旋即重新兴盛。纵观北魏一朝,除了短时间的挫折之外,佛教一直在不断发展。到北魏末年,全国僧尼之众已多达二百余万,各地寺庙亦多至三万有余。仅洛阳地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29)杨衒之著,尚荣译注:《洛阳伽蓝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8页。在方圆二百多里的地方就有寺庙1367所,可见当时佛教的兴盛。首都洛阳地区由于处于权力中枢的地位,也集中了全国最多的佛教寺庙及最有名望的高僧大德。
这一时期由于河北地区的佛教不如平城、洛阳这些地方兴盛,但由于地理位置临近洛阳这一权力中心,河北地区的佛教发展仍然相当活跃。天平元年权臣高欢挟孝静帝迁都入邺,结束北魏历史的同时也使邺城再次成为东魏北齐的统治中心。当邺城成为东魏北齐首都之后,洛阳的地位迅速下降,仅寺庙就由原来的1367所减至421所,其中固然有战争带来的破坏,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大量僧人北迁邺城。
东魏的实际掌权者高欢同样信奉佛教,他在晋阳开凿了著名的蒙山大佛。其继承人兼北齐的开创者高洋则在邺城开凿了响堂山石窟,成为河北地区最负盛名的北朝石窟。高洋不仅开凿佛窟,还从全国各地延请高僧入驻讲法,使邺城地区成为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例如,天保二年(551年)高洋宣诏僧稠赴邺城讲法并亲自出迎至郊外,在听了僧稠讲法之后大受震动。“因说三界本空,国土亦尔,荣华世相,不可常保。广说四念处法。帝闻之,毛竖流汗,即受禅道。学周不久,便证深定。尔后弥承清诲,笃敬殷重,因从受菩萨戒法,断酒禁肉,放舍鹰鹞,去官畋渔,郁成仁国。又断天下屠杀,月六年三,敕民斋戒。”(30)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6,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76页。在释灵裕的传记中亦记载高洋建寺延请名僧的事情:“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召德望并处其中,国俸所资,隆重相架。裕时郁为称首,令住官寺。”(31)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9,第312页。纵观高洋在位十年间,曾数次下令禁止杀生并广延名僧,这对北齐时期佛教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佛教的兴盛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思想进程,还带来了大量印度及西域的艺术创作元素。佛教在印度及西域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出现诸多如石窟、寺庙、佛塔、经幢之类的独特宗教建筑,还借助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佛教思想,由此带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印度及西域佛教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音乐、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它们的传入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路径。其中,以雕塑为代表的造型艺术尤为后人称颂。这些具有异域风格的造型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原地区,信徒们为了传播佛教创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佛教造像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雕像艺术的进步。佛教雕塑艺术迥异于两汉雕塑的古朴稚拙,以犍陀罗、芨多为代表的佛教造型艺术通过优雅端庄的艺术形象吸引着信众的膜拜,在传入中国之后迅速掀起了造型艺术的高潮。
不仅如此,佛教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被本民族所接受并与本土艺术相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中国人对于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3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5页。佛教艺术的传入即是如此,在进入中国之后作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为当时的艺术家借鉴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笔才一二,像已应焉”(33)何志明、潘运告编:《唐五代画论/历代名画记》,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的张家样与“曹衣出水”(34)郭若虚著,俞剑华注释:《图画见闻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的曹家样,分别代表了南、北朝佛教造型艺术的成就。
此时期的佛教并不仅仅只提供了宗教慰藉,它还带来了哲学思辨,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佛教的性空理论与当时玄学流行的贵无思想相结合,完成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支脉。对于河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而言,佛教的传播还具有另一重意义,即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烈冲突的过程中,佛家的慈悲与空灵思想中和了力量冲撞而带来的暴烈感,在河北文艺精神中加入了宗教的宁静与哲学的深邃。从传世及出土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佛教的思想精神不仅体现在大量寺庙建筑及雕刻陶塑中,在许多墓画中也有佛教因子,而世俗的器物中同样也有佛教文化的渗透。显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已经成为塑造河北艺术精神的重要元素。
乱世是武力张扬的时代,在一次次的战争搏杀中人类的暴力因子被不断释放;乱世同时也是悲剧的时代,战乱中的生命卑微如草芥,力量碰撞的壮烈与生命所承受的痛苦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一层更深的理解,它用宗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这种“力”与“悲”的张力同样在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明显的审美风格。
结 语
对于河北艺术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时期,原本正常的艺术演进路径因为外力作用被强行中断。大动荡时代不断涌入的外来艺术改变了中原传统艺术的发展势态,也使这一时期的河北艺术染上了更多的异域风情。大动荡的特殊环境也彻底激发了潜藏在民族文化深处的生命强力,在尚侠风气推动下,河北艺术充满对力量的渴望与表达,来自异域的佛教则为这种强悍的力量笼罩了一层慈悲的面纱,使其不至于转化为不可遏止的暴力宣泄。这些外在文化因素最终凝聚为河北艺术的内在精神意蕴,它让我们感受到河北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在遭受外来艺术挤压的同时能迅速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不断吸收融合外来艺术的优秀因子,最终在乱世即将结束的北齐时期初步形成新的艺术特色,为后来隋唐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