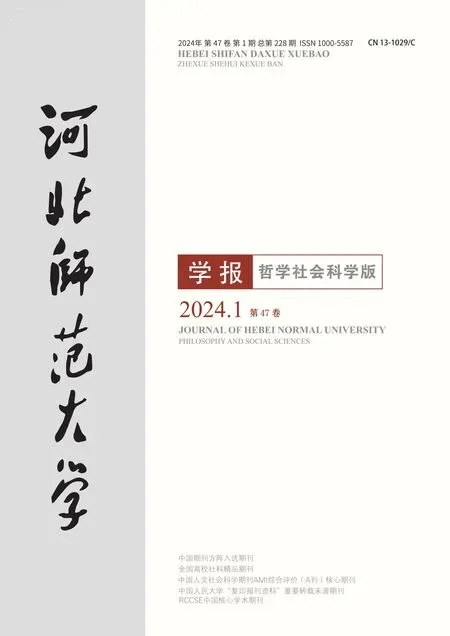民国时期梅兰芳、杜威与中美跨文化交流
洪朝辉,董存发
(1.福坦莫大学,美国 纽约 10458;2.复旦大学 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民国时期,一位中国艺人梅兰芳于1930年访美,一位美国学人杜威于1919年访华,这是一个值得比较的跨文化课题。如果说,杜威访华象征西学东渐的努力,那么,梅兰芳和他团队的访美演出,则开创了中学西传的先河。双向互动、取长补短是中美文化和跨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杜威与梅兰芳推动跨文化交流的主题不同,但他们所从事的国际交流的影响,则能够见证东西方交流的许多核心内涵。
首先,跨文化交流的一大要素是通过“他者”了解和认知自己,知人易、知己难,而且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梅兰芳与杜威就是通过与美国和中国社会大众的交流和反馈,有效提升了各自艺术与学术的能力。同时,跨文化研究注重文化本土化(inculturation)的成效,旨在探讨A文化如何在进入B文化的境遇中,得到顺应、适应和融合。最后,跨文化交流存在外交的功能,毕竟,外交的本质是人与人之交,梅兰芳与杜威通过各自文化故事的叙述,帮助两国民众增进了解,减少误会,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世界的和平。
一、梅兰芳与杜威的交往
梅兰芳与杜威并不是各自走在中美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平行道上,互不交集,而是存在许多直接的交往。
首先,当1930年2月梅兰芳访问纽约之时,杜威介入很深,因为负责出面邀请梅兰芳访美的美方单位是华美协进社,这是由杜威及其学生胡适等中美学者于1926年发起成立的。华美协进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杜威还担任欢迎梅兰芳筹委会的核心成员,主席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夫人。(1)“Famous Chinese Actor Makes Debut in ton Before Distinguished Invited Audience.”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6,1930.而且,杜威积极参与募款和组织,因为他是纽约首批219位捐款人之一。(2)纽约后援会(The First American Tour of Mei Lan Fang Sponsors of New York),参见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2,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1-24页。
梅兰芳弟子兼秘书李斐叔在日记中提到,1930年2月24日下午4时,梅兰芳应邀出席美国演员权益协会(又称万国俱乐部)组织的有500多位纽约著名艺术表演家参加的聚会,“杜威博士亦在座首”(3)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第492页。选自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戏剧出版社联合出版,2016年版,第335-513页。日记是李斐叔专门为梅兰芳访美所作,包括附录一原始稿,附录二整理稿。原始稿内容更丰富,整理稿内容简略,故本文在选取原始稿内容的基础上,适当选取整理稿中的部分内容作为补充。以下简称《李斐叔日记》。;3月2日下午4时,梅兰芳一行参加在卡尔登酒店(Ritz-Carlton)举行的东西联合社茶会,300余人参加,杜威博士再次出席(4)“To Honor Mei Lan-Fang.Better Films Group to Entertain for Him and Miss Cornell.”New York Times,March 3,1930.;3月7日下午5点30分,以杜威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举行招待茶会,欢迎梅兰芳一行,到会一百多位(5)“缀玉轩游美杂录”,《申报》1930年4月17日,第17页。,梅兰芳致谢词:“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吸收新大陆的新文化,是求学的性质,完全是学生的资格。希望各位教授不吝教诲!”(6)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3,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6-37页。3月14日午后,梅兰芳与张彭春一起参加杜威博士宴会,到会二三十人,都是各大学名教师,杜威对于“梅先生之艺术极为嘉许,各大学教授亦皆称可,咸谓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一旦于舞台上表现出之,深足资吾辈之研究”(7)李斐叔:《李斐叔日记》,第504页。。杜威还表示自己“瞻仰东方文化”,但只能用“笔来写写,嘴来说说,此外更没有别的好法子。现在竟得梅君亲来表演,实在是件最痛快的事了!我不但为梅君成功庆贺,我实是为东方文化庆贺,借梅君之力,得以把它的美点宣传表现出来;又为美国人庆贺,借梅君之力他们得以瞻仰最高尚的东方艺术。那么梅君沟通两国文化,联络两国的感情,其力量真是大极了,佩服佩服!”(8)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3,《日记》,第42页。另,在齐如山游美记中,误为“杜威博士等请吃晚饭”,根据李叔斐当天日记,应为午餐。3月15日,梅兰芳一天连演日场与夜场,杜威亲临夜场,观众多为学界人士,演出后,杜威还到演出后台问询(9)李斐叔:《李斐叔日记》,第505页。;3月22日,梅兰芳在大使饭店(the Hotel Ambassador)特别设宴招待美国前总统夫人、杜威博士等几十位知名人士组成的访美赞助团成员,并邀请他们在国家剧院观看最后演出,以表诚挚谢意!(10)New York Times,March 22,1930.所以,在梅兰芳逗留纽约的54天(2月16日-4月2日)里,杜威至少直接参与六次与梅兰芳的见面或观看演出。
那么,杜威是如何认识梅兰芳的?梅兰芳儿子梅绍武的回忆录中提到,梅兰芳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接待过英国作家毛姆、美国威尔逊总统夫人、泰戈尔、杜威、罗素等;还强调,1919年胡适邀请杜威访华,“便是胡适陪着到梅宅的。邀请梅兰芳赴美的,正是由杜威、胡适、张伯苓等中美学者创办的华美协进社”(11)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续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同时,根据梅绍武翻译、胡适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LanfangandtheChineseDrama)英文一文,可以推断出,杜威与罗素等重要人物一样,曾经看过梅剧、拜访过梅兰芳。胡适的这篇文章,选自梅其驹(Ernest K.Moy)(12)梅其驹是梅兰芳访美期间非常关键的人物之一,具体详情参见洪朝辉、董存发:《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新亮点——从边缘视角观察梅兰芳访美》,《南国学术》2023年第1期,第104-106页。编写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PacificCoastTourofMeiLanfang)的英文专集,胡适的文章居首,书中称胡适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13)Hu Shih.“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 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compiled and edited by Ernest K.Moy.San Francisco.The Pacific Chinese Dramatic Club,1930:1.梅绍武认为,“胡博士当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力主废弃旧剧,而《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这篇英文文章却写得相当客观”(14)胡适:《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参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5、216-218页。。梅绍武曾说:“上世纪廿年代,父亲经常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家中接待仰慕他的外宾。”所以,梅绍武推论:“杜威博士当年来华讲学时,我料想必定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陪同他观看梅剧、拜访梅寓的。父亲后来计划访美演出,想必也请教过胡博士。”(15)胡适:《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参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第219、220页。
另外,尽管杜威的日记中(16)Larry Hickman,Barbara Levin,Anne Sharpe and Harriet Furst Simon.Ed.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Electronic edition,Charlottesville,VA:InteLex Corporation,1999-2004.文章中引用杜威日记均出自此日记,以下只标出日记的具体日期、写信人和收信人等简略信息。,没有明确提及他是如何认识梅兰芳的,但根据一些线索推断,杜威了解梅兰芳也许早于1919年4月27日之前的杜威访华。梅兰芳于1919年4月25日至5月27日第一次到日本演出,东京和日本各地的大小报刊纷纷刊登新闻与评论。(17)谢思进、孙利华编著:《1894-1961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0页。而杜威夫妇则在1919年2月9日到达日本横滨,4月27日离开日本前往上海(18)杜威在日本的时间记载略有差异,据英文版《杜威日记》记载:2月9日,杜威夫妇抵达日本横滨港,4月27日离开日本神户港前往上海,参见:1919.02.10(10735):Alice Chipma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1919.04.22(03892):John Dewey to Sabino Dewey.据杜威女儿伊凡琳·杜威编写的《杜威家书》记载,杜威夫妇2月9日到达日本,4月28日离开日本赴上海,参见: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伊凡琳·杜威编:《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9页。,所以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存在交集(4月25日到4月27日)。同时,梅兰芳的演出地点是杜威夫妇经常光顾的东京帝国剧场(the Imperial Theater),杜威对曾经在纽约演出的日本著名艺术家雁治郎的传统剧目《武士道》,兴致盎然且前往观看(19)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伊凡琳·杜威编:《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第18、87、101页。;而且,杜威到达日本第一周,住在日本唯一的顶级酒店——东京帝国酒店(20)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伊凡琳·杜威编:《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第11-12页。,梅兰芳也曾下榻该酒店。杜威曾在1919年1月9日的日记里表示,“我们对中国越来越痴迷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人似乎已经打败了世界”。(21)1919.01.09(04082):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
另外,杜威很关注中国戏曲,但也许他的兴趣点是中国的戏曲教育,而不是戏曲本身。1920年6月5日至8日,著名的实业家、梅兰芳的忘年之交、戏剧改革的倡导者张謇邀请杜威前往南通演讲,并参观张謇在南通创办的最早的正规戏剧学校伶工学社,还观看了梅兰芳的特派代表欧阳予倩在更俗剧场的演出。(22)张绪武、梅绍武主编:《张謇与梅兰芳》,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同时参见杜威日记:1920.06.14(03928):Lucy Dewey to Dewey family.还有,1919年9月15日,杜威搬进自己的寓所——莫瑞森大街135号(135 Morrison St.)(23)1919.09.15(04103):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这条大街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而比邻的无量大人胡同就是梅宅,可谓“胡同邻里”。
另一个可能的佐证是胡适的日记。据胡适的日记记载,1920年3月11日晚9点,胡适与杜威到无量大人胡同;(24)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5月2日晚8点,胡适再次到无量大人胡同。(2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161页。无量大人胡同5号是梅兰芳的旧居,曾接待许多外国名人。1949年后,改名为红星胡同;改革开放后,无量大人胡同被拆除。根据出生在这一地点的梅绍武回忆,以及齐如山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载,梅宅应该是在无量大人胡同东头的5号院,(26)梅兰芳纪念馆编:《梅兰芳珍藏老像册》,外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参见梁燕主编:《齐如山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其他说法参见: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8/12-22/1496455.s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16日。民国图片资料库也保存了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照片,并表明梅兰芳是于1920年购买这座三进院子,1943年出售。(27)1920年梅兰芳为感激祖母的养育之恩,购置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寓所,它由两个四合院连为一体,内中还建有一座在当时颇显新式的洋楼。1943年因迫于生计将此宅卖出。参见:http://www.minguotupia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9&id=12319,访问日期:2023年5月16日。
了解了梅兰芳与杜威在中美日三地长达11年(1919-1930年)的交往,有助于理解与比较他们对中美学术和艺术交流所贡献的形式、内容和意义。
二、他者与自我的重构
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的背景、目的和内容各异,但他们在促进中美两国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则存在许多值得比较的视角。
首先,跨文化研究的一大要素是促使交流双方或多方,“通过他者重构自我”(r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by other)。(1)高洋:《“真”“假”歌舞伎》,《戏剧》2021年第5期,第94页。也就是说,通过美国戏剧界对梅兰芳和中国学术界对杜威的反馈,是否能够帮助两位大师完善和修正自己的艺术与学术。
梅兰芳1930年访美非常有助于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本人的自我改良。以梅兰芳为核心的梅剧团通过自1905年以来,对来访北京的外国各界人士的咨询、了解和调查,为访美做了充分且持续的准备,特别是在访美期间,针对传统京剧的优势与弊端,以及美国大众对京剧不适应的六大领域,进行了主动且有针对性的改良。(2)洪朝辉、董存发:《中学西传的杰作——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与文化在地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7-19页。同时,梅兰芳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通过对话美国戏剧专家司达克·杨、跟踪美国剧评家的书面评论、倾听美国观众的现场反馈,及时调整和修正剧目,在保持传统戏剧精髓不变的前提下,对具体的表演形式、表现方法和剧目选择,进行了有的放矢地自我完善。
其中主要的改良举措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首先是调整演出的形式。为了适应美国民众的口味,梅剧团适当减少歌词的“唱念”,避免重锣响鼓的伴奏,增加“做打”形体动作和舞蹈语言,严格控制演出时间与节奏,并在访美前对服装道具进行了图形化介绍,请专业人员采用国际通行的五线谱,对戏剧乐章重新谱写,并采用美国观众易于理解的名称翻译,如将《汾河湾》译为“A Suspected Slipper”。
其次是适度调整演出内容,选取东西方观众都能产生共鸣的艺术主题和审美情趣的戏码,如《刺虎》《汾河湾》等,但同时坚持京戏程式化、美术感、非写实、象征性的传统艺术核心。(3)洪朝辉、董存发:《中学西传的杰作——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与文化在地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8页。而且,梅兰芳的京剧改良与时俱进、及时改变。例如华盛顿演出第一场后,发现观众尽管反应热烈,但似乎并未看懂,于是,在张彭春的建议下,临时改变剧目,连夜排练,第二天就在纽约上演。
另外,努力学习美国的现代化科技。梅兰芳在出行前就期待学习美国戏剧舞台的一些高科技元素,尤其是电影技术,包括灯光、录音等。梅兰芳在纽约拜访多位使用电光的导演,亲自感受现代光电技术在戏剧舞台布景和演出时的最新应用,如一分钟颜色变化几十种灯光等。光学大师威尔费得君(Mr.Wilfred)向梅兰芳展示最新发明的光线,旨在影响观众心理的设备;纽约的大导演阔罗尔君(Garleorrill)主动提出为梅剧团演出配设新式灯光。(4)《申报》1930 年 7 月 7 日,第 12 页。 参见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附录”,第 1-4 页。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梅兰芳第一次参加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台现场演讲,多家报纸报道了这条新闻。(5)“Chinese Actor Makes Only One Radio Talk.”North Platte Daily Telegraph. North Platte,Nebraska.May 15,1930:5.在美国期间,梅兰芳拍了一段有声电影《刺虎》,并在上海剧场播出。(6)《申报》1930年5月10日,第24页。
梅剧团在美国的演出,不同于北京天桥的茶馆式听戏,而是耦合了美国百老汇舞台元素的东方艺术,在美国6个城市、18间剧场,进行了96场演出,赢得了10.5万人次的观众之“叫好”(7)董存发、洪朝辉:《梅兰芳访美演出场次考证》,《戏曲艺术》2023年第1期,第10-20页。,以及30多万美元票房的“叫座”。(8)董存发、洪朝辉:《梅兰芳访美演出票房考》,《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23年第13期,第1-17页。通过美国专家的“评头论足”和观众的“喜乐偏好”,梅剧团有效地改良了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斥之为旧时代“遗存物”(Survivals or Rudinents)的传统戏剧(9)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期,第313页。,重塑出既保持传统戏剧精髓、又适合国际艺术发展的“新京剧”。
类似,在长达两年之久的访华经历中,杜威通过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和郭秉文等中国学界翘楚的互动,也学到很多。1919年4月底5月初的中国,恰逢五四运动,杜威通过学术讲座、专题演讲、游历观察、名流拜访、田野调查,加速了杜威由学院式教授逐步转型为关注宏观国家、中观社区、微观民生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杜威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9日),足迹所至,遍及沿海、沿江的12省和京兆地方这一特别区域,与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官员、革命家、军阀、士绅、古董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有所交往”,杜威自认为这是一种“交互经验”(10)彭姗姗:《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1页。,互动提高。
同时,置身于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中,杜威有幸在学生、工人和市民三大运动的大城市中心(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讲学报告,以及波及大半个中国的省市乡村探访演讲,促使他将所见所闻,融入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杜威讲学的核心建立在他于1916年出版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上,主题是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和教育(意先生),提出“教育是生命的必需品”(Education as a Necessity)(11)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Chapter One,Full Text Archive,https://www.fulltextarchive.com/book/Democracy-and-Education.访问日期:2023年5月16日。,而且强调“教育是一种社会功能”(Education as a Social Function),并认为人的生命需要不断更新,社区也需要“不断的自我更新”(continuous self-renewal)。(12)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Chapter Two,Full Text Archive,https://www.fulltextarchive.com/book/Democracy-and-Education.访问日期:2023年5月16日。
另外,杜威应邀在模范省、但又是军阀控制的山西,向全国教育工作者演讲,与省主席阎锡山会面,接受张学良邀请、赴东北考察演讲,还在湖南谭延闿的宴席中,与英国的大思想家罗素首次会面,并成为好友。尤其是,杜威访问了陈炯明主政的广东省,拜访了孙中山,而且,他在各省市的访学大多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于是,杜威“与中国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13)刘幸:《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杜威在华的角色转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4页。这样,杜威与中国社会成为两大变量:一方面,五四后的中国复杂多元,处在急速变化、大浪淘沙与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杜威通过自身的不断顺应、适应与开放式互动与融合,回应中国的新经验。(14)彭姗姗:《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2页。1919年7月17日,杜威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当我反思我们思想变化的一面,反思我们来到这里后逐渐习惯的事实时,我意识到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向你们解释,而现在在这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15)1919.07.17(10775):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杜威访华期间,还常给美国影响力很大的时政研究与社会评论杂志,甚至美国国务院,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题报告与时政论文,内容涉及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的学生运动、工业化、教育和文化发展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报道、分析和评论,总计约49篇(包括回函、书评、报告等)。(16)顾学亮:《杜威在华学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页。特别是在1920年12月1日,杜威根据一些中国“他者”的信息,为美国国务院撰写了关于苏联十月革命在中国影响的专题调查报告《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BolshevisminChina),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缀斯代尔(Colonel Alexander Drysdale)于12月2日收到,并提交给美国国务院。(17)缀斯代尔(Colonel Alexander Drysdale)在备忘录中写道:“杜威先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机会接触中国可以被认为是激进的元素。我不知道还有谁——无论何处——比杜威先生更具有条件报告这件重要的事情。”参见约翰·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王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转引自顾学亮:《杜威在华学谱》,第277页。杜威在该报告中写道:“我没有看到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在中国的直接证据。……我确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与那些有时被称作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教师、作家和学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的社会与经济观念事实上也的确是相当激进的……他们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者,有时也自称共产主义者。”作为国家机密文件,该报告在1960年7月22日由美国国务院解密。(18)顾学亮:《杜威在华学谱》,第276、277页。
很显然,杜威在中国的视角与作品大多涉及时事政治和社会变革,偏重于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领域,返美后的杜威,“显然更具有了一种公共知识人的气质,开始走出书斋,投身更多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杜威撰写了《公众及其问题》(ThePublicanditsProblems,1927年)一书,成为他从学院派教授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大转折,他还参加了类似审议托洛茨基案等重大社会公众事件。(19)刘幸、陈玥:《超越文化猎奇:杜威的中国之旅》,《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第92页。这就是杜威访华从“他者”所得到的反馈与动力。
梅兰芳与杜威的访问起到了双向交流的效用,而不是单方面居高临下的输出,两者都从双方民众的反馈中得到收益与提高。人具有社会性,他者的反馈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尽管存在片面与肤浅的可能,但这面镜子能够起到警醒自我、完善自我的功能,尤其是那些与自己的国籍、文化、种族、政见、地位不同的国际“镜像”,更值得重视与珍惜。
三、文化本土化的融合效应
除了通过他者的互动、取长补短之外,梅兰芳与杜威的跨文化交流也可以被文化本土化(inculturation)理论所支持。文化本土化理论的要旨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解决初期的顺应(accommodation)难题,然后面对适应(adaptation)的挑战,最后达到具有活力的融合(integration)。(1)G.A.Arbuckle.Culture,Inculturation,and Theologians:A Postmodern Critique.Collegeville,Minnesota:Liturgical Press,2010:7.先顺应、后适应,最后在开放的动态中进入良性发展并得到融合。换言之,在推动文化本土化过程中,首先是“交流”,旨在完善和促进自己的文化;然后是“演化”,将主体文化镶嵌在客体文化复杂而又庞大的现实社会和体制之中;最后是平衡,客体文化需要平衡稳定与变化的矛盾。(2)洪朝辉、董存发:《中学西传的杰作——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与文化在地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杜威也曾对文化的适应、调整(Adaptation)提出自己独到的理解,认为“生命的维持要求有机体对其环境进行调适,要求个人对他所被置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生活条件作出调适”,而能够提供“最完全和有效的调适”的工具就是教育。(3)约翰·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6卷),王路等译,第279页。转引自刘幸、李泽微:《杜威来华讲学与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奠基》,《教育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130页。
美国戏剧界在与梅兰芳互动中,在旁白、虚拟、布景和人物表演四方面受到梅兰芳的影响。例如,著名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就承认,京剧对他戏剧的旁白有影响;Peter Pan这部儿童剧作者Evala Gallsene也认为,京剧的虚拟和非现实主义的特性影响了美国儿童剧的想象力和“表意动作”,她至少现场观看梅剧十几次演出,而且总在后台看得真切,把自己的疑问向梅兰芳提出来,搞明白,吸收中国传统戏剧的组织方法(4)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4),第18页。;著名独角戏明星Ruth Draper观看了梅兰芳演出后,得到启发,找到抽象的意念与具体表现方式的“暗示”的连接点。(5)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4),第17页。这样,梅兰芳访美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效应,既从美国的“他者”中吸收了美国文化的精髓,也通过推广中国京剧,影响了美国剧作家和戏剧创作。
同样,杜威访华也克服了前期的文化水土不服,成功传播了实用主义思想,而且确实改变了许多中国精英的理念与理想。首先,杜威对五四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影响很大,动摇了陈独秀原有的民主信仰,因为杜威主张,“民主必须具有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必须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很快,陈独秀在当年(1919年)11月的《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中,“虔诚地接受了杜威教授更为宽泛的民主概念”。(6)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在杜威的影响下,“陈独秀特别提议建立以每个村庄为单位的遍及全国的工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人民将最终享有自己的发言权,民主将从这些组织扩大到政府的最高层。”(7)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第14页。
另外,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也影响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8)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Th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2:99.、“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理念,并促使胡适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予以嫁接与改进。1919年6月,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同年7月20日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先后撰写了“四论问题主义”系列文章。(9)彭姗姗:《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0页。正是在这样背景下,9月20号,胡适建议杜威在北京大学大礼堂,进行实验主义的政治哲学公开讲座,一直持续到1920年8月6日。(10)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年表(上)》(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93-94页。这些讲座的英文原稿,“完全是基于学理的推演,不失为学者的本分”,对此,为了接上中国社会的地气,胡适在翻译过程中,对杜威的英文讲稿进行了许多取舍。(11)彭姗姗:《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9、144、145页。这就是杜威思想中国化的典型反映。
还有,杜威另一弟子陶行知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杜威实验主义教育理论本土化,发展出一套中国式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他在江苏建立了晓庄师范学校,“翻了个筋斗”并付诸实践。1919年7月22日,陶行知提出所谓的新教育就是关于“教学生的法子”,先启发学生提问,然后查出疑难地方,启发学生解决问题,“再从这些方法之中,选出顶有成效的法子,去试试看对不对;如其不对,就换个法子,如其对了,再去研究一下”(12)顾学亮:《杜威在华学谱》,第94页。。在总结晓庄经验的时候,陶行知精辟地阐述了教育与生活关系的三个历史阶段:一是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两者分离;二是教育是生活,两者相互有了联系,由此诞生“学校即社会”的信条;三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变成了学校,它代表一种回归,直接回归到了古代,因为在那个时代,社会就是学校,“然而这最后一个阶段才是教育发展的最高阶段”。(13)苏智欣(Justine Zhixin Su):《陶行知的创新实践:杜威理论在中国师范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教育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第12页。费正清认为,“陶行知是杜威的追随者,在面对中国的问题时超越了杜威”,并认为“杜威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14)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2.陶行知的成果就是跨文化传播出现文化本土化的见证。
胡适总结到,杜威主要传授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两种方法。一是历史的方法,杜威“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胡适认为,这个方法的应用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岀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同时,胡适认为这种历史的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除了历史的方法,杜威还传授了实验的方法,其中涵盖三个要点:一是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是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强调,杜威的“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而他的方法的影响永永存在,将来效果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梦想也还推测不完呢!”(1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40页。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总而言之,现代的外国思想家都没有比约翰·杜威更多地向中国受教育的公众展示他的思想”(16)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1.,因为“中国的进步教育家主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教师学院找到灵感”(inspiration),“杜威的‘边做边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响起”(pragmatic learning-by-doing rang a bell in China)。(17)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197-198.
值得一提的是,杜威与梅兰芳存在一个有趣的共同点:相对而言,两位大多是墙外开花墙外香,但墙内却不一定像墙外一样香。梅兰芳在美国得到几乎一面倒的主流媒体的赞美,例如:2月18日,伊利诺斯州一家报纸刊登剧评家Gilbert Swan的文章,题为《“中国最伟大的演员在美国巡演中与“不知名男孩”分享荣誉》(“China Greatest Actor Shares Honors with Prop Boy on U.S.Tour”)。所谓的“Prop Boy”是指在西方戏曲舞台不知名但在东方戏剧绝对超值的演员,但是这位“不知名的男孩”,在百老汇日场女观众眼中“实在是太可爱了”,文章还特別介绍了梅兰芳在电影界拥有众多“梅粉”。(18)Gilbert Swan.“China’s Greatest Actor Spares Honors with Prop Boy On U.S.Tour.” Freeport Journal-Standard(Freeport Illinois).February 18,1930:5.1930年4月14日,《芝加哥论坛》报道也提到“梅粉”一词,并特別作了界定和说明,认为这是“专指热爱东方戏剧的西方崇拜者”。(19)Charles Collins:“Mei Lan-Fang.” Chicago Tribune.April 15,1930:35.类似,《洛杉矶时报》剧评家分析了梅兰芳表演艺术,认为他的节目新颖且具有吸引力,女性角色的创造达到完美境界,舞蹈节目显示了节奏的技巧。(20)Edwin Schallert.“Chinese Star’s Art Unique.” The Los Angeles Times.May 15,1930:43.美国观众对梅兰芳表演姿态和音乐艺术的“新鲜、好奇”,表达出人类共通的情感核心。(21)“The American Reception of Mei Lan-Fang.”The China Critic.April 17,1930:65、366.也许,美国人追捧梅兰芳还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是一种西方人对中国演员男扮女装、京剧表演的一种好奇和猎奇,是一种偏见式的追捧,甚至是羞辱,对此以萨伊德为首的学者对怀有文化霸权、“妖魔化东方”的东方主义做过深刻分析与批判。(22)爱德华·W·萨伊德:《东方主义》,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页。
而杜威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学界也是影响很大、很正面。我们值得追问,中国人当初肯定杜威,是否也存在西方主义的因素?东方人是否存在崇洋媚外、殖民心理、既卑又亢的双重标准?或者,是否无论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总是与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论联系在一起。(23)陈小眉:《西方主义》,冯雪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页。所以,这是否值得今天的学者反思:当面对中美各界正面评论的时候,需要保持清醒的定力,要区分好奇与好评的区别,赞美之笑与嘲讽之笑的区别。
同时,梅兰芳与杜威的各自访问,似乎都出现了墙外开花墙内不香的现象。梅兰芳访美遭到林语堂等中国学者的严厉批评。以林语堂1930年7月31日在英文周刊《中国评论周报》的文章为例。林语堂说,梅兰芳自吹自擂是中国的慈善大使,其实他不配,因为创造亲善不是梅兰芳访美的主要目的。而且,林语堂还提到:梅兰芳所有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使徒”的言论,“仅仅是垃圾或胡说八道”(bunkum),如果说梅兰芳京剧“征服”(conquest)了美国,那么,“麻将和杂碎”(ma-jong and chop-suey)则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林语堂的批评文章后来部分出现在他于1935年出版的英文名著《吾国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其中提到:梅兰芳在舞台上拿着鞭子假装骑马或玩划船的演技,比我五岁的女儿好不了多少。(24)Lin Yu-Tang(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年版,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255;参见洪朝辉、董存发:《美国地方媒体与中美民间外交:梅兰芳1930年访美案例研究》,《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39-150页。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对梅兰芳和京剧一贯颇有微词,尤其是梅兰芳访美归来之后,更是发表了许多负面评论。1933年2月17日,英国文学戏剧大师萧伯纳应宋庆龄的盛邀,闪电式地访问上海一天,宋庆龄设家宴款待萧伯纳,蔡元培、林语堂等陪同,鲁迅也赶来见面,当天下午的笔会,梅兰芳也在萧伯纳邀请之列。(25)赵瑜:《“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萧伯纳抵沪,鲁迅为何半顿饭相迎》,《中国美术报》2017年10月16日,参见:http://www.zgmsbweb.com/Mobile/Index/articleDetail/relaId/15907.事后,鲁迅在3月1日给台静农的信件中描述:“他(萧伯纳——作者注)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答愚,似乎不是不足艳称,不过中国多梅毒,其称之也无足怪。”(26)《鲁迅致台静农,三月一日》,参见《鲁迅手稿丛编》第6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页。其实,“梅毒”作为形容梅兰芳影响力一词,早在1930年就曾出现。梅兰芳前往美国访问演出前,文学界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严独鹤在《送梅》一文中说:“梅畹华的声色歌舞,早已名满天下,提起‘梅兰芳’三字,真个妇孺皆知他,其他倾倒梅、爱护梅、崇拜梅的,更不知多少。北方会害‘梅毒’的雅谑,并且不但是国人如此,连西方碧眼儿也会传染‘梅毒’。”(27)谷曙光编校:《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5),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0页。显然,1930年梅兰芳访美前,上海知识界文化界用“梅毒”来比喻梅兰芳的正面影响力,与梅兰芳访美成功后的1933年,鲁迅继续引用颇有歧义的“梅毒”,来评判梅兰芳的负面影响力,可谓同词异意、意味迥然。墙外的“梅粉”赞誉与墙内的“梅毒”恶评,形成鲜明对照。另外在 1934 年 11 月 15 日,鲁迅以张沛为笔名,在《中华日报》发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认为“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28)张沛:《“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参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 (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 638页。当鲁迅得知梅兰芳访美演出最成功也是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贵妃醉酒》,也要在 1935 年的苏联演出,鲁迅就用戏谑口吻揶揄道:“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29)张沛:《“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参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639、640 页。
类似,杜威的访华也遭到美方学者的负面批评,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尽管杜威访华对中国教育界存在影响,“但结果呢?仅仅流于表面”,杜威理论的实施需要太多的外部条件: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律对个人和私有权的保护,以及漫长时间的渐进改良,所以,中国有另外的优先选择,那就是列宁主义,替代了实验主义。(30)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1.还有史华兹也有类似言论,认为杜威对中国的理解实在肤浅、幼稚可笑,其实验方法和主义的“渐进的方案,难以解决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31)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第15、18页。
梅兰芳与杜威通过各自的努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方的戏剧表演和学术思想,通过有效的文化磨合,两国民众与社会或多或少地接受和实践了中国京剧和美国教育的理念、形式和内涵,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精髓有机地浸润到对方社会的机理,镶嵌到各自民众的认知世界。
四、文化外交的效用
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在推动中美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的效用上,也存在异曲同工的绩效。民间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指民间或非政府组织所从事的以文化为主题的民众交流,旨在建立国际之间人与人的草根性(grass roots)联系(1)J.Gregory Payne.“Reflections on Public Diplomacy: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4)2009:579-580.,属于一种心与心(heart to heart)之间交流的外交。(2)Anne Turpeau.“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 World Affairs 123(4)Winter,1960:104.文化外交的一大重要内容是讲好各自国家的文化故事,而故事员的素质是讲好一个国家故事的最重要元素,故事员的素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令人信服的专业水平和无可争议的专业实力。梅兰芳的演技绝对得到世人的公认,四大名旦之首的地位也是世界认同,而杜威则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实践,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在美国和世界有口皆碑。
第二是超然的立场和独立的身份,其中一大检验标准是出国的经费来源。梅兰芳的访美经费完全自理,而且典押了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豪宅,经费常常入不敷出,当初还计划为了装点门面,先住豪华酒店,过几天再搬到廉价酒店,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3)梅葆玖等:《冯耿光信十一:给鹤弟(梅兰芳)》,见《梅兰芳往来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第142-143页。梅兰芳还随时准备如果演出没人看,就到美国各大学进行艺术交流,或者到工厂做几次慰问演出,只要大学和工厂能“赠送路费盘缠”、打道回府即可,权当一次旅行而矣。(4)梅葆玖等:《齐如山致冯耿光、赵叔雍、吴震修关于访美演出的书信》,见《梅兰芳往来书信集》,“附录”,第314页。类似,杜威访华的经费也没有事先落实中方预付的模式,相反,杜威一直担心讲课没有薪水,当时北大因为五四运动等因素,正在罢课罢教,欠薪是常态,而哥大只给他一年的没有工资的休假,“其在北京等城市的系列讲座教学,也是为了在中国生活,弥补其母校类似停薪留职式的经济需求”(5)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第1页。。
第三是民间组织成为主要接待单位。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从1922年开始就着手梅兰芳访美的布局与接洽,并委派其得力助手傅泾波具体落实接待演出宣传等细节(6)冯伟:《司徒雷登助力梅兰芳访美新考》,《戏剧》2023年第1期,第111-114页。;总部位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则起到邀请、联络、安排的穿针引线、搭台唱戏不可或缺的作用(7)孟治(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Sixty-Year Search.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ew York,1981:110.150.;梅剧团在上海启程前,全国各界民间代表举行欢送会;华侨联合会则通电美国华侨(8)《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5页;1930年1月11日,第15页。;到了纽约后,华美协进社主席郭秉文亲自到车站迎接,安排公关社交活动(9)参见李斐叔:《李斐叔日记》,第477-479页;“缀玉轩游美杂录”,《申报》1930年3月29日;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3),第4页,《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2),第5页。;而张彭春与齐如山所设计的演出时间,精确到以分钟为单位的120分钟内,全部都是戏曲主题,没有任何官方代表,如驻美大使、领事上台“讲话”等非戏剧内容(10)参见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2),第21-24页;“缀玉轩游美杂录”,《申报》,1930年3月29日。;纽约总领事熊崇智只在招待会上发言,甚至还为梅兰芳作英文翻译(11)参见《申报》1930年4月9日,第19页;李斐叔:《李斐叔日记》,第492-493页。。民间组织的接待为民间外交的顺利和有效的推动,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用。
杜威访华也主要由民间推动。1919年2月杜威出于事业、家庭和个人的身体原因,离开美国前往日本东京进行为期数月的访问讲学。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杜威的得意弟子郭秉文和陶行知,亲赴东京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如果说杜威在日本讲学,还做了一些准备,那么来中国讲学,则出于偶然邀请。而且,杜威访华与中国教育部没有直接关系,至少现在没有发现教育部的官方邀请函。当然,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较早介入了杜威访华一事(12)转引自彭姗姗:《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3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杜威在到达上海4天后的5月3日,还在希望得到中国教育部的正式邀请,因为根据5月3日杜威给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的信中表明,“我知道教育部长即将向你和哥伦比亚当局提出正式要求”(13)1919.05.03(04068):John Dewey to Nicholas Murray Butler.,而且,此信也说明哥大没有批准他访华,杜威是先斩后奏。
正因为梅兰芳与杜威讲述文化故事的实力、独立自主的经费和民间色彩的定位,不仅改善了自己国家在对方社会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帮助对方走向自己国家、走进自己文化。例如,梅兰芳推动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成功,可圈可点。当梅兰芳在百老汇演出仅一周后的1930年2月23日,《纽约时报》就刊登“艺术大使梅兰芳”的长篇报道,指出梅兰芳带来的传统中国戏剧是纯艺术(pure art),而且优美雅致的舞蹈、韵律以及一招一式等舞台艺术,带给观众的是赏心悦目,艺术的语言是相同的,梅兰芳就是传播艺术的大使。(14)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1930.梅兰芳在获得美国加州波摩那学院荣誉博士时答辞道:一切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渴望和平,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通过军备和战争所得,只能通过理解、宽容、同情、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破坏来实现,梅兰芳以一位世界公民的身份呼吁和平(15)“An Honor Deserved.” The Pasadena Post(Pasadena,CA),June 3,1930:4.,提升了中国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
同样,杜威的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成果,也十分显赫。首先体现在他所扮演的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之上。例如,杜威在1919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他给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和哥大写信,推荐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宝川为首的60位杰出教育家代表团访美,成员包括蔡元培、蒋梦麟等,杜威在私人推荐中强调:“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a greater opportunity)进行学校之间的合作和地方工业的发展”。(16)1919.11.12(05021):John Dewey to William A.Wirt.类似,1919年11月13日,杜威在给Wendell T.Bush的信中,也鼓励美国专家来中国访问,这是一种独特的桥梁作用,既介绍中国专家赴美,又鼓励美国专家访华。(17)1919.11.13(05022):John Dewey to Wendell T.Bush.这类同行间的推荐与鼓励,比官方的招才引智之效用往往更大。还有,杜威的外交作用还体现在用文章影响美国学界和社会各界。Scudder Klyce在给杜威的信中指出,拜读了杜威发表在亚洲杂志的两篇文章(18)John Dewey.“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 in Ratner,Characters and Events,1:286; “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 Middle Works,11:105-127.两篇文章名称出自杜威日记:1919.09.15(04103):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Notes 2.,非常同意杜威的深入观察与研究,加深了对中国人心理的理解,并表达“强烈喜欢中国人,这种喜欢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人”(19)1919.12.27(04612):Scudder Klyce to John Dewey.。1920年1月5日,杜威对中国的观感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女儿Evelyn,因为她在撰写杜威一家与美国家人的通信集前言中提到“中国正在进行的争取统一和独立民主的斗争的魅力”,并强调,杜威和夫人“努力将西方民主的一些故事带到一个古老的帝国,反过来,他们也在享受这种经历”。(20)1920.01.05(03900):Evelyn Dewey to whom it may concern.
杜威的观察也体现了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不是一味赞美,而是理性的批判,这有助于提升一个故事员的公信力。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和不可逾越之墙”(remains a massive blank and impenetrable wall),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通过“给年轻的自由主义分子面子”的方式(“giving face” to the younger liberal element)。他还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如此厚重和自我中心,以至于通过外国人呈现的外来影响都无法触及其表面”。但是,他也乐观地看到,“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其中我们的胡适就是一个明显的领导者,正在把事情搅动起来(keeping things stirred up)”。(21)1920.01.05(03900):Evelyn Dewey to to whom it may concern.当然,他还令人费解地提出,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比自由派的中国人更保守”(Most foreigners her[e] are more conservative here than the liberal Chinese)(22)1920.01.05(03900):Evelyn Dewey to to whom it may concern.。显然他被五四运动中激进青年的言行惊到了。
值得指出的是,梅兰芳在美国和杜威在中国的影响力,并不具有持续性。梅兰芳离开美国后的近百年,再也难以重现中国京剧在美国百老汇和好莱坞的辉煌,当年的轰动效应难以复制。同样,杜威对中国学界和社会的影响也不具备可持续性。当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一切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论等,如饥似渴,但是,随着更激进的罗素思想理论的宣讲,杜威的思想显得有些“过时、保守”。知识界的热度转向罗素,并开始接受由俄国输入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杜威成为“过气”的启蒙思想家。当杜威于1921年离开中国时,一批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此,费正清说道:“任何仍在近视地寻找美国‘失去中国’(loss of China)的人应该注意到,当约翰·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要在那里成立。”这样,代表美国自由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被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取代,美国最终“失去”了中国。(23)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2.
所以,正因为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存在民间性和偶然性,我们一方面不能过度拔高两者行为的外交功能,另一方面,也由此见证这种具有偶然性的民间外交效用往往是事半功倍。
结 语
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看似互不相关,但他们通过由浅入深的与“他者”交流、由表及里的文化磨合、由点到面的文化外交,殊途同归,为中美艺术与学术交流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首先,梅兰芳与杜威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了中美共享的文化价值(shared cultural values)的建构。中美两国始终存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很难寻找和发现两国的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但是,两国的价值观系统存在许多互相交集的共享价值,形成一定的重叠,而梅兰芳和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两国民众发现与感受了可以共享的文化价值。梅兰芳的京剧美学至少展示了三大共享的中美文化价值,得到美国观众的共鸣,它们包括善良、正义、同情,梅兰芳在美国表演的几十出京剧折子戏,大都展示了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仁义礼智信的情节,超越了西海与东海的地域界限。同样,杜威的思想也体现了中美文化之间的许多共享价值,包括教育、平等和科学,尽管杜威的实验主义与民主思想不一定是中美之间的最大共享价值,但其中的部分实验和民主的理念被许多左中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
其实,共享价值就是一个增量的概念,也许在交流初期,难以找到多数人所认同的共享价值,但假以时日全方位、多层次磨合,一定能够得到不断扩展和丰富。作为对比,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是一种存量的概念,它在双方合作之前就已存在,如果执着于双方既存的普世价值,那很可能失去启动交流的机会(1)洪朝辉:《两极之上 左右之间——适度经济学思想导论》,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2-85页。,也就没有了梅兰芳访美与杜威访华的可能。
同时,梅兰芳和杜威的跨文化交流提出了对等适度的新思路。亚当·斯密提出人际交往,不仅要对等、要适度,而且要对等适度(equal propriety)(2)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Notes,Marginal Summary,and Index by Edwin Cannan,with a new Preface by George J.Stigl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445.,由此帮助我们理解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和目的。一是以说服对方为主要动机的交流,类似教师爷的灌输与说教,最终促使对方接受他们的观点,甚至追随他们的信仰。二是以各自表达为目的的交流,旨在对等交流、理性分享、求同存异、共同提高。梅兰芳和杜威的跨文化交流属于后者的对等而又适度的交流,因为他们交流的背后没有国家的力量、没有军事的霸权,更没有强制要求两国民众去观看中国京剧或参加美国学术讲座,他们自身也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说教或自我膨胀的歧视。相反,他们两人都是温良恭俭让,谦卑低调,不耻下问,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各持己见,而是虚心接受对方长处,取舍适度地改变自己的不足,也耐心解释自己的演技与思想,避免对方误解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最后则由观众或听众自主而又自由地决定自己演出或演说的价值。
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往往存在四种倾向:一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强盗逻辑;二是己之所欲、不施于人的吝啬习性;三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传教心态;四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境界。跨文化交流中需要放弃执念与偏见,抵制强盗逻辑、减少吝啬习性、防止传教心态,多多提倡知己知彼、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恕道境界,推动对等而又适度的交流,而不是好心办坏事的说教。而且,梅兰芳与杜威讲述文化故事的形式非常值得提倡,他们各自通过合适的平台(剧场、课堂、酒会、聊天、访问等),讲述各自国家的文化故事,属于邀请式修辞(invitational rhetoric)(3)Sonja Foss and Cindy Griffin.Eds.Inviting Understanding:A Portrait of Invitational Rhetoric.New York: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20:17-32.,而不是运用强迫与变相强迫的方式,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艺术和学术。
最后,中美两国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需要去中心论。在一个多元世界里,刻意强调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中心论,无助于平等的艺术和学术交流。确实,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GDP领先世界各国,但经济领先不等于文化领先、学术第一,形而下的物质文明不能取代或等同形而上的精神文明。如果霸凌而又擅自判定儒、释、道、耶、伊、犹、印各自的绝对优势与中心,那么,不仅跨文化交流无法进行,而且可能引发宗教战争和世界大战。所以,当我们在反对一个中心的同时,不应主张另一个中心,更不能打着反中心的旗号拥戴中心,其结果有可能导致我们的价值判断左右摇摆、忽左忽右。
其实,提倡走中道、停中间的钟摆效应(Pendulum Effect)的要义之一(4)洪朝辉:《美中社会异象透视》,(纽约)博登书屋,2021年版,第31页。,就是促使自鸣钟失去动能、停止对发条的加力,并促使这个自鸣钟进入无为、适中、不极端、不称霸和韬光养晦的境界。今日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去中心的新世纪,区块链、比特币、人工智能、元宇宙和Chat GPT等高科技的核心思想,就是去国家、去中心、去核心。从庄子的思想出发,有中心是人,无中心是道,因为他的名言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5)庄子:《庄子·外篇》,《秋水》,见方勇、刘涛译注:《庄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63页。,无贵贱、无区别、无中心的大同世界,也许正是新世纪人类所需要共同追求的理想。
如果说,梅兰芳代表“东海”、杜威象征“西海”的话,那么,东海西海一定能够通过同情共理的交流,最后达到心同理同。(6)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着》。原文:“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参见《象山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