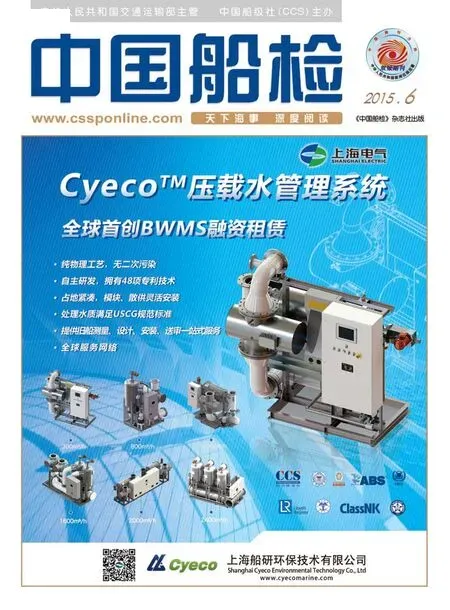海上搜救配套法规应完善细化
本刊记者 刘 萧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国内外与搜救相关的公约。
郭萍:目前专门涉及海上搜救的国际公约是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和救助公约》(以下简称《搜救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也有个别条款涉及国际合作进行海上搜救的内容。除此以外,还有涉及到海难救助民事权利义务方面的国际公约,主要包括《1910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规定公约》及修订该公约的1967年议定书以及《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以下简称1989年救助公约)。目前中国是《搜救公约》、《海洋法公约》以及《1989年救助公约》的成员国,有关搜寻救助内容在我国1983年《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已有所体现(该法面临修改),有关救助报酬等民事权利义务的规定,体现在《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中。
记者:近来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不少远海搜救案例。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搜救过程中的所谓“就近原则”,事故发生海域的临近国是否有义务第一时间进行救援?其是否存在弹性?
郭萍: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和救助公约》明确强调为了保护海上人命安全,以及能够在各国之间协调海上及海空安全活动的需要,各个公约成员国应当向海上遇险人员提供援助,沿海国应当为海岸值守、搜寻救助等方面提供适当而有效的安排。
但是,该公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公约成员国实质性以及具体权利、义务,只是在公约第2 条明确规定,不应损害《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不应损害各国在海洋法及沿海国、船旗国管辖权的形式和范围内提出的主张和法律意见。同时该《搜救公约》也不得与其他国际公约中规定的船舶义务或权利相抵触。
根据《搜救公约》附则的规定,各个成员国应当保证为在其海岸附近的海上遇险人员提供适当搜救服务,并且每一个搜救区域需要通过有关缔约国之间的订立协议予以建立,但是此种搜救区域的划分,不涉及也不得损害根据《海洋法公约》各个国家之间边界的划分。因此根据《搜救公约》,原则上各国应当在沿岸范围内从事搜救行为,即你所提及的“就近原则”。并且根据《搜救公约》,即使各缔约国在搜救区域的具体范围方面不能达成共识,也应当尽最大努力就该区域内提供搜救服务安排方面达成协议。对海上遇难人员的搜救,不考虑遇险人员的国籍或身份。
除另有协议外,每一缔约的沿岸国在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应当批准其他缔约国救助部门在沿岸国海域从事单纯为了搜寻海难地点和救助遇险人员进入或者穿越沿岸国领海或领土的行为。因此遇险人员的国籍所在国如果也是搜救公约的缔约国的话,可以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在《搜救公约》的沿岸国进行搜救活动。
记者:2005年我国制定发布了海上搜救预案。马航事件出现后,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在境外海域的搜救上还存在缺失。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在毗连区的救捞问题上,预案还需补充哪些内容?
郭萍:目前我国搜救工作是在《海洋法公约》及相关国内法规定的海域管辖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涉海行政主管部门,都有明确的海域管辖范围和事项。因此就沿海或近海搜救而言,问题不如远海或深海那么明显。对于我国领海以外专属经济区或毗连区范围内的海上搜救,由于受距离、人力、物力等限制,我国搜救预案还不能及时落实和实施。
去年马航事件后,我们注意到国家已经派遣军用船舶、海事行政执法船舶进行搜救,应当说这是落实海上搜救预案和体现我国政府对国民保护的原则。至于我国能否直接参与我国管辖海域以外的搜寻救助活动,一是要看我国与遇难地管辖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搜救协议或其他相关协议;二是在经过遇难地管辖国家搜救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有权为了确定海难发生地点和救助遇险人员的目的,在遇难地管辖国家的领海从事搜救工作。由于我国已经参加了与搜救、救助有关的国际公约,因此在国内立法方面,也初步搭建了有关海上搜寻、救助方面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海上搜寻救助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对外贸易和海上活动的需要,一些规定还不够细化,我国已经参加的与搜救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规定也相对比较原则化,特别是涉及国家间合作问题的,更是需要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予以完善。
记者:刚才您谈到国内搜救相关法律问题。听说我国海上搜救虽然由各级搜救中心全面负责,但在组织过程中搜救指挥关系比较复杂。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国家主管机关在海难救助中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救助报酬请求权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和误解,这些争议和误解有没有什么具体事例?
郭萍:海上搜救工作非常复杂,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同时也涉及到很多涉海的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必要时应得到军方的支持和援助。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各级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涉海管理部门之间的权限进行明确规定,即通常所说的“九龙治海”。近年来我国对涉海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一些机构改革,专门成立了海警局,但是就涉海管理机构而言,仍然存在多家机构并存的现象,还无法实现如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等类似的统一海上执法机构。目前在交通运输部直属的国家海事局之下,专门设立了国家海上搜救中心,负责协调各有关部门完成具体的海上搜救工作。举个例子,作为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各级海事局经常会参与或涉及海上搜救和救助工作。但对于国家主管机关是否能够主张救助报酬,确实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争议,也有相关的案例。
记者:能够具体谈一谈您所说的这一问题么?
郭萍:关于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问题,1989年救助公约第5条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即“不影响国内法或国际公约有关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救助作业的任何规定。从事救助作业的救助人有权根据公约规定获得救助报酬和补偿。负责进行救助作业的主管当局享有救助报酬或补偿的范围,应当依据该主管当局所在国的法律确定”。该公约明确规定了救助报酬、特别补偿等概念、相关计算标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国《海商法》第9章将该公约内容转化成国内法时,仅仅在第192条规定了“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本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而根据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了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国家主管机关有对海上遇难船舶和人员搜寻救助的义务。这样就可能出现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
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海上救助到底是义务,从而不得主张任何救助报酬,还是可以在救助成功后,依据海商法赋予的权利,主张救助报酬?对此,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主管机关不能主张任何救助报酬;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主张救助报酬。在后一种观点之下,又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其一,国家主管机构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享有完全的救助报酬请求权。其二,毕竟主管机关参与的救助不同于一般商业救助公司,因此其获得的救助报酬应当适当低于专业救助公司,即应当扣除国家财政拨款其用于海上交通安全行政执法的部分。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郭萍:鉴于国家财力、物力投入的限制,目前作为海事安全管理的各级海事局尚不具备完全从事海难搜寻和救助的力量,而往往需要动用专业救助公司或其他社会力量,或者紧急情况下调动遇险船舶周边的其他商船从事救助活动。如果完全剥夺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救助获得救助报酬权利的话,则间接地会剥夺海事局以外其他社会力量从事救助后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甚至会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海上遇难人员及时提供援助的问题。因此本人的意见是应当赋予国家主管机关主张救助报酬,但是应区别于从事商事活动的专业救助公司或人员。
拿马航事件举例,搜救过程中也有商事船舶受搜救中心指令前往疑似海域参与搜救工作。实际上即使该商船在未能成功救助遇难财产获得救助报酬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据船舶被征用的理由,获得部分国家补偿。同时如果商船上载有货物,那么因搜救造成货物损失等,承运人可以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免除对货损的赔偿责任。
记者:近几年,越来越多搜救任务都围绕中国南海进行。南海区域海况较其他地区复杂,且又是“敏感区域”。您认为,我国应该就该区域补充哪些搜救法律法规?同时需要哪些硬件配合?
郭萍:南海问题涉及国家主权,我国历来主张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权利。但是鉴于南海目前的状况,应该对我国有关搜救(主要是海上交通安全法)、有关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予以细化,以增强相关预案的合法性、操作性、合理性。鉴于南海是中国与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国家从事国际贸易海上运输的战略通道,为了保证中国商船及财产、人员安全,建议能够在海南设立专门的搜救机构,以更好地快速、有效提供海上搜寻救助服务。
记者:近些年国际海上救助公约有什么发展?如今公约更趋向往哪些方面拓展?
郭萍:就救助公约而言,近年来的热点问题是针对救助报酬或特别补偿方面的。因为《1989 年救助公约》首次提及特别补偿的概念,并且在救助报酬的考虑因素中涉及到救助人保护海洋环境所付出的技能和努力,因此目前公约的发展已经更多地考虑到环境保护因素或者称之为环境救助问题,不限于传统的财产救助。受当时公约各方面因素限制,公约规定的特别补偿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局限,计算本身也非常复杂,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针对公约这一问题,救助实践中,船东互保协会集团、国际救助联盟等国际组织共同起草制定了SCOPIC 条款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条款制订于1999 年,先后在2005、2007、2011 年进行修订。近二三年国际社会也在呼吁修改《1989 年救助公约》,希望能够真正从保护海洋环境的角度,提出“救助环境”的概念,并能够将SCOPIC 条款中的部分内容吸收到《1989 年救助公约》中。国际海事委员会(CMI)近年来的几次大会上,都专门设置有关修改《1989 年救助公约》的议题,但是鉴于救助报酬、特别补偿的最终负担方是保险公司和船东互保协会,因为涉及各方利益的妥协和协调,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预计在未来几年,如果《1989 年救助公约》进行修订的话,公约中很有可能会有专门涉及环境救助的相关规定及制度。
记者:以往的海上救助公约都是针对失事船舶搜救工作制定的。针对失事飞机,海上救助公约是否有相应的内容与之匹配?
郭萍:《1989年救助公约》针对的救助标是处于危险中的海上财产。虽然大多数针对遇险船舶,但是并没有限于船舶本身。这个海上财产,可以是海上任何遇险的财产,只要这些财产不是永久性,也不是有意地依附于岸线的任何类型的财产,因此也包括遇难坠海的飞机。如果救助人就遇难的飞机进行了成功的救助打捞,残骸还有部分价值的,救助人都可以向飞机的所有人主张救助报酬,当然救助报酬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救助报酬不得超过被救财产的价值。如果最终搜寻的结果是没有发现残骸,或者残害已经没有价值,则参与搜救的各国搜救费用如何分担,需要与遇难飞机的财产所有人及失事国政府进行协商解决,公约本身对此没有答案。
记者:最后还是要回到主线上来。综合我国搜救法律法规与国际上的救助公约,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优化?
郭萍:我认为在民事责任方面有待补充。其实《1989年救助公约》本身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没有规定对就位的从事勘探、开发的固定式或浮动式钻井平台的救助问题,例如2011年在渤海湾发生的美国康菲公司蓬莱19-3钻井平台溢油事故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必须通过国内法予以解决。因此建议将来我国在修改海商法第九章相关规定或者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能够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还有就是在海商法修改时,能够对一些条文以及用语的表述、国家主管机关从事或控制的救助问题、环境救助等问题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