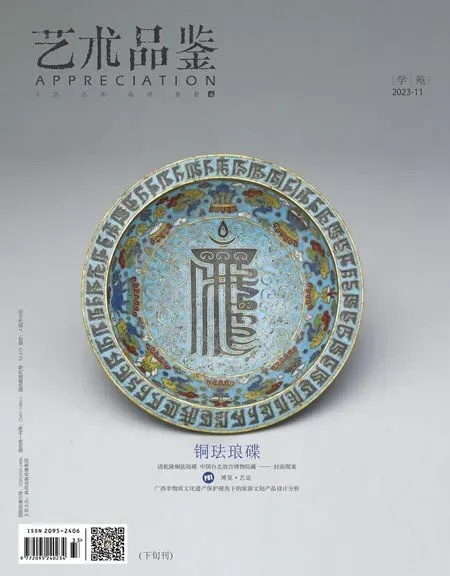人性美的诗化表达*
——论舞剧《边城》的创作特色
郭奕衡(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音乐舞蹈系)
沈从文先生于1931 年将小说《边城》成书发表,故事以20 世纪30 年代的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向读者展现独属于湘西世界的浪漫之情与人性之美。1994 年,为打造属于湖南人自己的文化精品,一部“中国舞剧里程碑”的巨作——舞剧《边城》就此出世。两年后,该剧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新颖的创作手法、高尚的艺术品位,在文化部第六届“文华奖”评选中荣获舞剧类作品唯一的“文华大奖”,除此之外,还获得文华创作奖、文华编导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设计奖和文华表演奖等多个奖项,成就了文华奖评选中的一段佳话。舞剧《边城》的诞生为当时的湖南舞剧创作扩宽思路,并树立起新的舞剧标杆,这都离不开原作的文学魅力与舞剧编导们独特的改编策略。
一、人文主义的结构筑建
小说到舞剧的转变,必须尊其基础、探其可议、掘其创新、议其共鸣。既是由小说改编而来,必然不能推翻原作的主要内容,然而,因形式有异,舞剧又不得不摒弃小说的细节化叙事,所以,改编过程一定是在保留原作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再加以舞蹈表演的优势,把故事内容与情感抒发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做到两者利益最大化。
舞剧剧本保留了小说主要情节顺序,这样既避免了观众的理解障碍,又使故事的发展理所当然。第一场次为交代故事背景,画面由小舟上相互依偎嬉戏的翠翠和爷爷引入,自然风光里长大的翠翠天真活泼的像一只小鹿,慈祥的爷爷则耐心的抚顺翠翠的头发,他们悠然自乐,似桃花源中的活神仙,顿时,惬意之感油然而生,观众仿佛置身其中,兴趣也随之被牵动;第二场次为情节发展,一阵唢呐声,把观众引入下一场景,映入眼帘的是群演们为赛龙舟欢呼雀跃的画面,他们用简单的双手起落动作形成的人浪向观众表达兴奋之意,紧接着,人潮涌动,翠翠与爷爷相继走散,就是在这儿,翠翠遇到了另两位主人公--傩送与天保;第三场次为情感迸发,三位主人公在爷爷的促就下关系更深一步,翠翠在两兄弟间左右为难,最后选择了傩送,两人通过大部分双人舞向观众诉说情意,天保以爱之名退出三人关系,独自下州,不曾想却随河流漩涡而去;第四场次为寥寥收场,傩送得知兄弟意外,在天真的翠翠面前还是选择了离去,他不愿让翠翠也置身痛苦之中,却未料想,爷爷将其中种种看在眼中,他为三人不得不遭受的悲惨命运而惋惜,悲痛欲绝,舞剧由此结束在翠翠拉船时无声的叹息之中。
关于小说到舞剧的人物舍离,小说可以为了丰富内容创造无数角色,但舞剧中对角色的容纳数量十分有限,舞台上短短的时间里,必须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由外展开其他人物线,这样才能简洁明了地向观众梳清故事中各个人物间的关系,由此方便观众理解故事内容。在不影响主要情节发展的前提下,舞剧的编导选择对原著中一些主、次要角色进行取舍,例如,原著中“看龙舟”片段,拿着火把寻找女主翠翠的人本是故事里一个无名小伙子,舞剧为了强调主要人物的纠葛关系,把“无名小伙子”替换成了男主人公“傩送”。由此,男女主人公从初遇到相恋的情感线便绝妙而又精密地串联在一起。这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烦琐的人物关系,加强了主人公之间的情感脉络,使观众更易看懂故事的发展;又如原著中饮酒作乐的是翠翠的爷爷与代管渡船的老人,舞剧中改为天保在看龙舟时,偶遇与翠翠走散的爷爷,热情邀他一同喝酒谈心,顺势之下向爷爷道明了自己对翠翠的爱意。一面是傩送和翠翠互生情愫,另一面是天保向长辈诉说心意,舞剧对人物的合理舍弃,使得两条感情线愈加清晰,极大程度上加深了舞剧的戏剧冲突。
二、纯净山民的舞蹈形象
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代表了舞剧的核心三观。舞剧《边城》在保证主演形象塑造鲜明的前提下,对各舞段群演的刻画亦均具备个性特色。善良质朴的翠翠,和蔼慈祥的爷爷,朴实重情的傩送,豪迈豁达的天保,四位主人公所代表的是人世间至纯至美至善的美好人性,这也间接反映出《边城》的人性力量,便是“真、善、美”。
翠翠的舞蹈风格轻快、灵巧。例如,序幕中与爷爷的调皮互动,整个活动范围仅限于一片扁舟,演员将翠翠无拘无束的性格尽显在灵动的眼神与轻巧的肢体中,只见她时而依偎在爷爷身侧,时而娇俏的与爷爷嬉闹,毫无掩饰的将翠翠的可爱与天真展示在观众面前。此外,翠翠在舞台上的大量动作是由小碎步、凌空跃、吸腿转等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以及芭蕾舞中的“开、绷、直”撩腿、踢腿构成的。这些技术技巧都讲究身体的轻盈与灵动,十分符合翠翠天真烂漫的人物形象;爷爷的舞蹈风格沉稳、细腻。剧中与翠翠的双人舞段,多以“包含”的身体状态接纳翠翠,例如,在扁舟上,爷爷的维度空间始终高过翠翠,营造一种“覆盖感”,翠翠变得格外小巧,爷爷的形象也高大起来。剧中爷爷的舞蹈形态总是屈膝弯腰,为的是构造老者之形,传年岁之意,这一形象一直持续到爷爷去世之前,一段激烈的独舞将爷爷内心深处的痛苦释放而出,虽加入了跳跃的动作以示情绪上的挣扎,却在落地造型的选择上,回归了老人的蹒跚步履;傩送的舞蹈风格大气、敞亮。在其举着火把与翠翠进行的双人舞部分,大男孩的羞涩与对心上人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敢看而又不敢动的细微神情牵动着观众的心。二人定情后的双人舞增加了许多托举动作,尽管手上动作因与翠翠的配合而不停变换,身体姿态却始终迎向翠翠,表情沉浸且甜蜜;天保的舞蹈风格豪迈、直接。在剧中,天保的动作干脆有力,基本上都是直出直回、不带拐弯,这也表现出他的性格之耿直。天保送粽子给翠翠时的直爽与坚持,试图吸引翠翠目光时的憨厚与率真,与傩送离别时的豁达与真实等,都充满了湘西山民的淳朴气质。
除了主演需要通过过硬功底来塑造形象,群演的形象塑造也需被重视,如看龙舟一幕中,画面由群舞演员们的嬉闹引入,他们时而作呐喊助威状,时而作分帮争论状,时而作勾肩搭背状,时而作模拟划船状……演员们动作简练干净,以跳跃与前后律动为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目光始终放至观众席,像是龙舟就在不远处进行着激烈的比赛,引得观众愈发想随着演员们张望,给人留以无限遐想,尾声一幕,舞台氛围悲凉而神秘,演员们的主题动作多为原地跳跃、转圈以及跪地俯首,似在模拟一种庄严的场景,让人心生敬畏,整体队形与调度在圆圈上进行,下身重复颤膝动律,上身重复俯仰形态……肢体的极限运用,情感的精确代入,群舞演员们总能轻易地将舞台氛围拉至高点,同时让观众身临其境般产生情感共振。
舞剧在舞蹈编排上,重视民族风格的多方位呈现。在剧中,不仅贯穿了多个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还采纳了芭蕾舞、现代舞的舞蹈元素,这些不同形式的舞蹈,在单双群舞段中被充分地展现出来。例如,为塑造天真烂漫的湘西女子形象与纯净朴实的舞台氛围,舞蹈编导为翠翠设计了大量“小碎步”“拔泥步”“悠摆步”等汉族民间舞蹈元素,极大程度得渲染了舞蹈环境,烘托了舞台氛围。除此之外,民族民间舞的自娱性也为舞台增色不少,最经典的“看龙船”场景中,应用的舞蹈形式是以“摆手舞”为代表的土家族民间舞蹈,这一舞蹈元素都源自土家人民极富地域特色的娱乐与表演,风格特征偏夸张化,音乐节奏偏明快化,以最大限度烘托“看龙船”时的喧闹及各种场景的激昂氛围。由此可以看出,民间舞为舞剧中舞蹈形象的塑造与舞蹈环境的营造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三、视觉与听觉的极致体验
(一)视觉上的赏心悦目
舞剧《边城》中的服装设计,蕴含着浓郁的民族文化之美,演员们的每一套服装都极具民族象征性与地域独特性。例如,翠翠的服饰具备典型的湖南民族民间特征,重点放在立颈、遮膀、收腰、直筒裤腿上,胸以上的位置还点缀了几朵栩栩如生的小黄花,以凸显其活泼的性格。三位男主人公的服饰集“质朴”与“美观”于一体,服装样式采用了民间男性日常穿着的“褂子” “阔腿裤”等,为增强民族韵味,在下身还加上了棉麻质地的裤腰带,这一小心思将湘西男子的不拘小节完美地呈现了出来。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又给予了观众审美享受。
舞剧中的道具设计,汲取了湘西民间的生活用品之特色。如“看龙船”时,群演拿着的纸伞,傩送寻翠翠回家时使用的“火把”,天保告别时给傩送护身符等等,使用这些日常可见的道具,可增强舞剧的风格特色,清晰定义情感氛围。其次,道具与舞蹈动作共同构成的动态造型,不仅增强了舞蹈的表演性质,而且使得舞蹈与内容互相呼应。
灯光作为舞台上的视觉焦点,具有营造舞台虚景的作用,每一束灯光的设定,都代表了不同人物的独特心境。例如,剧中将翠翠纯洁美好的内心展露得出神入化一幕,当属“黄葵花”,全幕主题色调为鹅黄色。鹅黄是仲春与童年的象征,是人生中最温暖、最充满生气的时光,同春天一般,让人心旷神怡。翠翠就像春天森林里的一只小鹿,在花丛中嬉戏玩闹,灯光的配合给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观感,仿佛空气中都带着几分微甜,让心也不自觉地宁静了下来;尾声时,灯光随着画面转场逐渐变暗,一开始使用的是范围极小的微弱白光,而后突然变成红色,演员们与灯光扩宽的步调一致,小范围的微红变为整场的大红,加之演员道具--白色布匹的点缀与悲壮乐声的响起,悲凉氛围顿时建立,一时舞台上悲声如歌,舞台下情绪涌动。不管是人山人海的热闹感,还是颓靡悲伤的神秘感,通过舞美的烘托,舞剧的舞台效果与故事内涵都得到了质的飞跃,《边城》形象由此坚固于众人之心。
(二)听觉上的心旷神怡
首先,舞剧《边城》运用了多种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其中十二音创作技法在各个篇章中大幅出现,创造出了既满足戏剧张力,又兼具风俗人文的音乐音响。这种从调性中抽离出来,摆脱了传统和声功能体系的方式,使作品兼具了时代性和先锋性。例如,第一部分,从人声的引子结束之后(00:03:49),长笛的动机开始引入,在音阶上形成一种冲突与对比,这种“不和谐”的感觉使人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湘西地域特有的朦胧和神秘感。包括接下来的钢片琴演奏的旋律与整个弦乐组之间一动一静的配合,弦乐一直维持长音,以大二度纯五度为主,钢琴的走动与弦乐组呼应过程,出现了大量的小二度和增四度的音程,和声的紧张度也在周而复始地发生变化。还有第二场中,赛龙舟也出现了这样的对比,比如(00:05:35)处的民族音乐元素动机,是一个很有记忆点的五声音阶民族调式,相对于后景略显嘈杂的伴奏,这一部分的主题会显得十分突出且具记忆点。在(00:07:04)女主角出来之前,整个和声的紧张度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状态,此时场景的喧闹与纷杂表现的分外生动。舞剧作曲家通过使用十二音创作技法将民族元素的主题极大程度地凸现了出来,听众在相对紧张的听感中,很容易抓住熟悉的民族音乐主题。从整个舞台画面层次上看,十二音技法的应用将这种层次丰富了起来,观众的听感也变得多样。这种听感分别对应了前景突出的部分演员以及后景呈现的群像感,舞台画面与音乐相得益彰。其次,湘西民间音乐元素的应用,是作曲家在使用现代作曲技法的基础上,为凸显作品民族特性与内核的灵魂作出的延伸。主要人物的音乐主题大多取材于湘西民间歌曲,作曲家通过对这些湘西民间歌曲的分析,提炼出整个音乐风格以及音阶调式,保证了在对其他动机的创作与主题的发展结果进行分析之上,做到与湘西民间音乐的风格特征类似。例如,开篇女主角的音乐主题,一个上行的四度音,发展到对四度音进行的扩展与反转,从而得到下一小节,再对这个小节作出完整的回应,进而得到第三小节。整个乐句的强调与落点都基于一个纯四度的关系。这种手法体现在许多湘西民间山歌中,十六分音符的小回转设计的格外灵动,与女主角的形象十分契合。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音乐主题出现在看龙舟这一幕,从(00:05:35)赛龙舟热闹场景的动机进入,整个主题只用了三个音,但是在节奏上层次变化丰富。伴随着中间一段颇具紧张的节奏,整个动机上移了一个纯四度。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动机出来对应的是男生的小组舞,上移之后对应的是女生的小组舞,这样的编排方式,让音乐动机和舞台画面相辅相成。由此可见,针对民间曲调的分析提炼,作曲家在动机创作上保证了风格的一致性,并高度地配合舞台的呈现,让舞台效果更上一层楼。以及舞剧作曲家别出心裁地由乐器特殊奏法创造出的独特音效,也下了功夫。他们通过使用乐器的特殊演奏技法以及编排,在传统管弦乐的编制上,创造出了不一样的音效,充裕了作品的音色形态,强化了对舞台环境与场面的描绘。在“看龙舟”场景中,作者大量使用了让演奏者自行处理任意音的技法,例如在弦乐组的长颤音后,木管铜管以及打击乐组演奏自由的任意音符。弦乐的滑音也在整部舞剧音乐中得到了大量的使用,不仅有泛音的滑音循环往复,也有弦乐组的滑音制造出的类似噪音感。乐器特殊奏法的应用是传统管弦乐乐器法以及编排的一种创新,在本剧中,作曲家通过这些技法的使用,表达出不协和的音效,从而突出了群像的喧闹,也通过这种细腻而虚无的滑音,表达出了湘西的神秘与缥缈。除此之外,民间音乐元素的提炼也在本剧中得到了大量应用,比如民族打击乐,这里的打击乐运用主要指土家族传统的打击乐曲牌:打镏子,又称为打挤钹。其起源于原始渔猎时代,打镏子被土家族人用于驱逐日食的现象。同样,它也被用于部落获得猎物而群聚助兴。打镏子形式多样,手法灵活,节奏明快,变化频繁,主要分为绘声类(模仿自然动物的声音)、绘形类(描绘动物神态)、绘意类(对于某一特定事件的描述)。在第一场戏(00:04:17)处,引子部分的山歌结束之后,第一次打镏子的曲牌出现在舞剧中。伴随着小锣,头钹,二钹与打锣交错的节奏设计,配合唢呐的旋律,很易将人代入送亲的喜乐氛围中。此处为绘意类的打镏子。同样的用法还出现在了最后篇章(01:01:00)处用以表现最后的悲凉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通过打镏子的曲牌连接了前后两段的音乐材料,能够让情节更流畅地过渡。且热闹的打击乐氛围能充分抓住观众的耳朵,能及时有效地让观众设身处地联系上湘西民间婚丧嫁娶的场面,由此可见,打镏子的使用让整个剧情的结构更加清晰明了。
四、结语
沈从文先生的湘西题材作品,挖掘的是真实达观的人性之美与人生态度。与此同时,诠释的是在湖南舞剧创作中,中华民族的生命美学与艺术价值。在现今的社会,人性之破裂和迷茫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弥补,我们却能从湘西世界中重新寻到人类最初的本真。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情结令我们及时找回了原有的真善美本性,《边城》中的湘西世界,涵盖着真实社会中人们对于生活所寄予的强大生命力。茶峒秀丽清新的山川美景与溪河堤岸满山遍野的枫林秋色,代表的不仅仅是《边城》中特定时代的湘西小镇背景,也是其他湖南舞剧创作在取景定调时的完美借鉴。为了对各民族的原始生态环境与质朴民俗文化有效的保护与继承,我们应以小说《边城》舞剧化为标杆,用现代文明的手段,将这种艺术文化传承于后代,湖南舞剧创作的立意就在于此。
舞剧《边城》的现世,引起湖南舞剧改编民间小说的浪潮,其中,极具湘西风情的湖南民族舞剧《凤凰》《马桑树下》《桃花源记》等脱颖而出,也创下了不同程度的辉煌。时至今日,湖南舞剧仍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在《边城》问世的几十年后,湖南再次创作出一部崭新并富有时代意义的民族舞剧--《热血当歌》。二十多年前,湖南舞剧用纯粹的湘西民族风情推出舞剧《边城》,自此打开湖南舞剧高速发展的大门,二十多年后,湖南通过回顾历史,以敬畏之心,致敬国歌,致敬中华民族的满腔热血。湖南舞剧在创作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承袭湖湘文化的传承要旨,将“自强不息”刻于心中,不论是诉说《边城》中湘西小镇的生机勃勃,还是诠释当代舞剧《热血当歌》中的家国情怀,湖南舞剧的创作都坚持并且做到了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薪火相传。精神文明是国家的灵魂,文化传承是民族力量的源泉,由发展地方舞剧的方式来发扬民族文化自信,为的是从“小”民族阔“大”视野,从个体情感升华至家国情怀,传承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