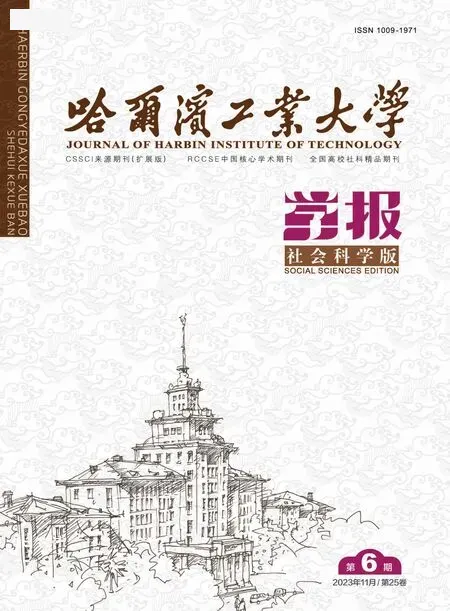《文心雕龙·神思》疑义新辨
段 宁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足可跻身于最重要的著作之列。 在这部宏著中,《神思》篇也许是最著名的篇章了。学界对《神思》篇的理解见仁见智,此篇也可谓多年来“龙学”研究中争议最大的篇章了。 比如“神思”的内涵、“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之解、“杼轴献功”说、“思表纤旨,文外曲致”之意,等等。 鉴于此,本文对《文心雕龙》中的《神思》篇进行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一、“神思”内涵之辨
对于“神思”的内涵,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莫衷一是。 王元化在《文心雕龙讲疏》中提出“艺术想象”说,李泽厚和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也赞同此观点。 张文勋主张“文思”说,牟世金则主张“艺术构思”说。 目前在“龙学”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认为“神思”是以艺术构思为主,并包括想象、灵感等因素,代表学者有张少康、周振甫、王运熙。 此外,还有王达津主张“形象思维说”,赵仲邑主张“精神活动说”。 尽管对“神思”的体认不一,但是这些观点大体上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借鉴了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点和术语。 这种方式自有其可称道之处,但是在还未厘清文本原意的情况下,就以今人之眼光去审视“神思”,很容易陷入以己意逆刘勰之志的歧路。 因此,研究“神思”的内涵既要立足于《文心雕龙》的具体语境,同时也要联系刘勰所处的文化背景,力求接近刘勰之原意。
在《文心雕龙》的20 篇文体史论中,既有有韵之文,也有无韵之笔;既有诗赋乐府等文学性较强的文体,也有奏表铭策等实用性较强的文体,刘勰统将它们通称之为“文”。 这种“文”“笔”皆称之为“文”的情况,似乎是三国魏晋之际的普遍认识。 在《文心雕龙》之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称为“文”;陆机的《文赋》在谈到“体有万殊”的情况时,则列举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文体为例;及至萧统在《文选序》中仍将诏诰教令等实用文体与诗赋等相提并论。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之“文学”因借鉴了西方的“四分法”,主要指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文学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由此可见,刘勰所处时代之“文”并非我们今日之所谓“文学”,二者内涵有很大差异。 如今,我们一般把刘勰当时之“文”称为“杂文学”,或名“泛文学”,以与今日之“文学”区分。 因此,若单从今日之文学观念入手,以今日之文学术语(如艺术想象、灵感、形象思维等)去阐释“杂文学”的概念、范畴,虽然在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方面功莫大焉,但也会失之偏颇,自有其局限。 就《神思》篇而言,刘勰在其中连举了12 位文思迟速不同的作家为例,但是,这12 位作家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家,他们的文章也不全属于今天之文学范畴。 所以,面对古今文学观念的错位现象,我们若想发现古人之真实想法,还是需要从原文文本中寻找答案。
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明确提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1]493,可见“思”与“神”并非完全等同,而思、神和物三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思”就是神与物相互交融的过程。 那么,何为“神”呢? 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 然 凝 虑, 思 接 千 载; 悄 焉 动 容, 视 通 万里。”[1]493可见,“神”是完全自由的,可以上天入地,穿越时空。 它并非精神的全部,而是其中最纯粹自由的接近神灵的精华,可谓“精魂”,可独与天地相往来。 与之相反并且相对的便是“物”,这个“物”原本是精神之外的具体的外物,有色有声,可视可听。 但正因为它可视可听,故能“沿耳目”通过“思”这根红线与“居胸臆”之“神”相连,这正是“思”之妙处。 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神”通过“志气”表现出来,“物”通过“辞令”得以展现,“志气”和“辞令”便成了为文的关键和枢机。 此之“志气”,与今意不同。 《体性》中提到:“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1]506可见,“志气”主要指情志与才气、文气。 而“辞令”,主要指谋篇与词藻。 《情采》有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538《征圣》中也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1]15可见,“志气”与“辞令”是为文之两大关键。 为此,我认为:“神思”在成文前是精神与外物相互感发和交融的过程,而在成文过程中主要具化为考虑如何表现“志气”与组织“辞令”。
二、“拙辞或孕于巧义……焕然乃珍”之辨
如何理解“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1]495。 早期学者一般认为这是指文章完成后要修改润色,此说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为代表。 后来,王元化否定此说,认为:“使庸事可以萌新意,使拙辞可以孕巧义,不是用修饰润色所能收功奏效的,它必须通过想象活动所起的作用。”[2]122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郭绍虞与王文生亦持此说。 李逸津则认为“杼轴献功”说讲的是修改文章,理由在于:“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应解释为“有时有巧妙的义理却用了拙劣的文辞来表达,有时有新颖的意思却用了平庸的事典来说明。”[3]在《文心雕龙译注》中,周振甫将之解释为“就情理说,有新颖的,有庸俗的,要删去庸事突出新意;就文辞说,有巧妙的,有拙劣的,要删去拙辞突出巧义。”[4]404
鉴于以上前辈学者的理解和分歧,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段话呢? 这里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刘勰在这里打了个比方,说“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麻经过杼轴加工后变为布,从材质上来说,布与麻并无不同。 但是,布的外观却“焕然乃珍”,从而价值高于原来的麻,这是杼轴的功劳。 可见“麻”用来比喻“拙辞”和“庸事”,但并不能把“布”喻为“巧义”和“新意”,因为从语意上来讲行不通,“拙辞或孕于巧义”相对应的就是“麻或孕于布”,但事实上麻并不是从布中产生。 我认为,“拙”并非“劣”,只是“笨拙、朴拙”,“拙”与“庸”皆有平常普通之意,就像不起眼的“麻”一样。 而“辞”,并非今天所说之词语,而是指“篇章、词句”;“事”亦非今天所说之事情、事例,而是指事义,即用事用典和义理。 在刘勰所处的南朝齐梁时代,骈文极为兴盛,连很多非文学性文体也受其影响,所以,骈文以及骈文的特点自然成为刘勰的关注对象,他的理论成果也是在以骈文为主的杂文学时代背景下产生。 萧统《文选序》:“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5]他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作为选文之标准,可见当时对于事义与辞藻是多么重视。 尤其要注意这里提到的“沈思”,这与《文心雕龙》的“神思”正相呼应,很明显,“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二者的意义相近,可以互释,都要表达“神思”对于在当时极为重视的事义和辞藻的重要作用。 不同之处在于,刘勰的这句话侧重在“神思”的“焕然”,他认为:原本普通平凡的辞藻和事义可以在“神思”的作用下获得新生,它们在神思所赋予的“巧义”和“新意”下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从而使得“拙辞”不拙,“庸事”不庸。 此种解释,似乎与前文的语意和文章脉络也相符合。 此段开头提到“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显然,这是下文的前提条件。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周振甫先生将之解释为“要是情思不一致而是非混杂,体制不当而变易多端”[4]399,我认为此解也有待商榷。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曾多次提及类似话语,比如《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1]67《章句》:“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1]570-571《附会》:“赞曰∶篇统间关,情数稠迭。”[1]652《风骨》:“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1]514以上诸篇,均谈到情理和文体之变化。 再联系《神思》篇的文章脉络来看,此段之前所谈为“神思”的特性与有助于“神思”的方法,比如“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1]493“博而能一”[1]495,等等,均为实际写作前的准备工作。但是,“神思”所包含的是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精神活动,在前文也提到过“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1]493所以,刘勰接下来所论述的便是实际创作过程中“神思”的性能,尤其是在情理与文体经常变化的条件下,“神思”之随机应变的创造性。
笔者认为:“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修改润色,也不仅仅是艺术想象,而应该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神思”对于篇章所起的各种作用的总和。 因为“辞”有篇句、词藻之意,所以要使“拙辞或孕于巧义”,“神思”所起的作用至少包括谋篇布局、组织语词、修饰词藻等等;又因为“事”包括用典和义理,所以要使“庸事或萌于新意”,“神思”所起的作用也至少包括从旧典中联想生发、进行有独创性的义理阐发,等等。 具体而言,则体现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其余篇章中。 正如《总术》所言:“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 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 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1]656这19 篇创作论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刘勰的创作理论体系。 而《神思》篇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神思”是作家创作中精神活动的总称,故而能渗透到其余各篇中,与之相互印证。
“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以“焕然乃珍”的“布”比喻有美好的文采和情理的文章,充分强调了文章的美感。 刘勰之前的王充在《论衡·量知》中就曾说:“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恒丝庸帛,何以异哉? 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 学士有文章之学,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6]从王充美学思想的整体倾向看,他还是力主美的简朴与实用的,但在这里,他却也注意到绚丽之美的存在,并且论述了这种美学形态与其所体现的权力、地位和礼仪的关系,这段话可算是“杼轴献功”说的先驱。 当然,与刘勰相比,王充似乎具有正统的儒家美学思想。 上文涉及到萧统的《文选序》曾说:“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是当时作家的重要技能,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对文章形式美的重视。 值得指出的是,对为文之美的追求并不仅限于诗赋等文学,刘勰等人对于当时其他实用性文体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们所针对的是当时的“泛文学”。 这种追求文章美感的观念,与今日之“纯文学”观念很接近,从而使二者有相交融之处。 文章的“焕然乃珍”,来自于“杼轴”之功。 《淮南子·说林训》上说:“黼黻之美,在于杼轴。”[7]这个“杼轴”即为“神思”,刘勰在《书记》中曾说:“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1]456“杼轴”所体现的便是“为文之用心”。 刘勰在《序志》中也曾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1]725可以说,“神思”与“文心”相呼应,而“辞采”与“雕龙”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最重视的两个方面,它们集中体现了文之锦绣。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中曾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8]鲁迅这里所说的“意想”,即为有意构思、冥想,与“神思”之意相通。 由此可见,《文心雕龙·神思》也彰显着出了刘勰的一种“向内转”的倾向,即由对“文”实用价值的追求转向对“文”之自身内在美感的关注。
三、“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之辨
在“杼轴献功,焕然乃珍”之后,刘勰又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1]495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引用《注订》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者,言文笔忌滥,适可而止。 趣味宜永,耐人寻思,方称妙品也。”[9]这里所强调的是“文笔忌滥,适可而止。”王元化《释〈神思篇〉杼轴献功》指出:“作家往往在作品中对于某些应该让读者知道的东西略而不写,或写而不尽,用极节省的笔法去点一点,暗示一下,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吝惜笔墨,而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想象活动。 这种在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现象,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2]120王元化认为刘勰在这里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想象,才故意搁笔,留下空白。 张少康认为:“我国古代的文艺家主张文学作品应当能体现出‘言外之意’、‘文外之旨’,即利用言语所能够表达、可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部分,去暗示和象征语言所不能表达、难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部分,尽可能地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10]
这段话虽然包含有以上各家所指出的种种深意,但它其实更可视为是刘勰的自谦之词。 联系上下之语境来分析,在“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之前,刘勰先后论述了“神思”在创作之前和创作过程中的特点,他在谈到创作前的“神思”时提出了要保持“虚静”的心态和“博而能一”等几点可实践的训练方法,这都是刘勰所能提供给为文者的可借鉴的方法,也有实际操作性。 但是之后在刘勰谈到具体创作过程中的“神思”时,他只是笼统地以“杼轴献功”打了个比方,并未提出具体的方法,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于实际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刘勰在其后的创作论中有一些分门别类的表述与解决方法;另一方面,正如刘勰在下文所说“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1]可见,这与伊尹不能说明烹调美味的技巧,轮扁不能说明砍轮精确的方法一样,那达到最高境界的方法是无法言传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亲身体会其中的精妙所在。 因此,这句话也是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的补充。 刘勰认为,如何使“神思”做到“杼轴献功,焕然乃珍”的方法或途径是无法告人的,因为那其中复杂多变、微妙精深。 沈约在《答陆厥书》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11]沈约虽然以精通韵律著称于世,但是他也无法说出其中的精粗之别。 陆机《文赋》也曾提到“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 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12]42同样有感于实际创作中的精妙是无法言说的,可谓“妙不可言”。 可见,“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 是刘勰在逐步深入谈到创作的更高境界时,因其中的精义奥妙过于复杂高深,故而不能向作者们提供之前那些较为直接和实际的方法,只有靠作者们自己去体会领悟了。
如果说这段话要表达的是,作家们为了追求言外之意而有意为读者留下空白这种情况,那么就与上下文意不搭界——至精而后谁来阐其妙呢? 至变而后谁来通其数呢? 让读者吗? 但刘勰的论述着眼点在于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的“神思”,并非读者的接受过程,他所关注的是承接上文而来的“神思”之训练培养的方法。 若说这段话是谈与玄学有关的言意之辨的话,未免离题万里了,因为全篇所讲的是“神思”的特点和训练方法,若真涉及到言意关系,那也是在前文中提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1]494,并且刘勰之所以在那里谈到言、思、意之关系,也是为了阐发“神思”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493-494的特点所带来的难题,即言与意的特性相冲突,刘勰还在其后提出了解决方法,即“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1]494其实在刘勰的其他篇章也有类似的话语,可姑且称之为谦辞。 比如《序志》:“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 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1]727《声律》:“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1]553它们都谈到为文的精妙变化之处实难完全表达清楚,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作者已是尽力而为了。此外《时序》中也曾说:“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1]675虽然在这里,刘勰可能主要是为了避嫌而搁笔,但是这段话和以上几段话都处于各自篇章结尾处,所起的作用都是补充说明。 所以,我以为,“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是同样的道理和作用。 在陆机《文赋》中也有类似的话:“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12]18这与刘勰要表达的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即各种技能在达到炉火纯青时的“纤旨”“曲致”确难向门外汉说清楚。若能说清楚,那么人人都将拥有高超的技能了,这也是不现实的。 况且,即便把其中的精义都说出来了,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人也难以理解,“夏虫不可语冰”便是这个道理。 此外,作为一名文章家,在其理论之作的末尾写上一段补充并自谦的话,这也是很常见的,即使在今天亦如此。
《神思》篇的疑点难点还有不少,本文只是力求立足于《文心雕龙·神思》之作品本身,结合当时文学背景,联系《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以及相近时代的作家作品,尝试去辨析学界《神思》篇研究中的几处疑义,以求贴近刘勰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