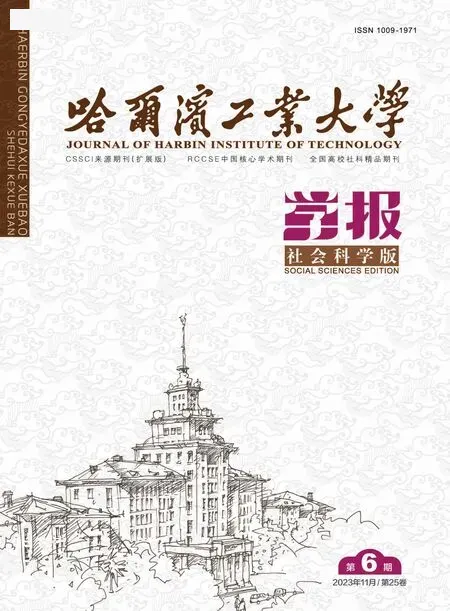对自然的“认同”及其困境
——兼论进化论思想的生态哲学意义
杨 文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运动兴起于20 世纪70年代,它以生态危机为线索,“探问人类事务的方方面面——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以及终极的:哲学和宗教。”[1]这一深入底层观念的追问发端于如下信念:“我们如何对待生态取决我们对‘人—自然’之关系所持的观念。”[2]在此视角下,学者们注意到近现代的二元论哲学是生态危机的“精神帮凶”,它在形而上学层面决绝地划分了人与自然,从而诱导了人类面对自然的冷漠态度。
对此,深生态学的创始人奈斯(Arne Naess)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名为“认同”(identification)的生态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展示了人类主体与自然对象相互交融的可能性和实现情形,从而弥合了二元论所生造的人—自然之鸿沟。 本文将考察“认同”之方法的基本要点及其理论困境,并引入进化论及其哲学阐释进行回应。 进化论所引发的生命哲学变革更新了人们对人—环境关系和人与其他物种之关系的理解,它为以“认同”为代表的诸项生态哲学理想提供了科学支持。 这一理论联姻也同时预示了生态哲学与实证科学合作并行的宏大前景。
一、人与自然的分离与“认同”
历史上的许多古代宗教与原始信念都表现出了生态友好的特点,它们主张普遍的生机论:“生命对他(人类)来说无所不在,并且都是活生生的……灵魂弥漫于整个存在领域。”[3]83这种生机论时常将周围环境中具代表性的对象拟人化,并无疑将限制人类的开采与利用。 印第安人将天与地认作宇宙性的父与母,这种认知导致他们不大可能对自然进行强力剥削:“你要我耕剖土地、我应该手持尖刀撕裂我母亲的胸膛吗? 你要我挖取石头。 我应该在她皮肤之下寻找骨骼吗? 你要我割草……但是,我怎敢剪除我母亲的发辫?”[4]①这类观念在我国的传统中同样存在,《述异记》等古代文献中所传的神话认为江河山岳均为盘古的身体所化,而《太平经》不仅提出了“天父地母”学说,认为“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还直接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反对人们大兴土木。 参见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415 页。
与之相对,近代的机械论观念则是“生态可疑”的,根据笛卡尔的理论,全部实体区域分为广延与心灵:“世界”从根本上说是无限可分的广延(几何)微粒,思想实体或曰心灵则是非广延的,它不按世间的力学—机械学规则活动。 笛卡尔的决绝之处不仅在于做出此一划分,更在于认定只有人才是心灵的保有者,就连和人有表面相似性的高级动物也被规定为一台“自动机”。 人因内在地包含“我思”这一超机械论因素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动者——主体。 与前述原始自然观不同的是,这种二元论诱使人类对自然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个没有价值与内在性,目的与心灵的宇宙是不足顾惜的。 世界性的诸般对象都可被合理地当作达成人类目的的工具,帮助实现人类的价值。 对工具的粗暴不是真实的粗暴,就像摔碎砖头算不得残忍一样。
由此可以明白,为何当代环境哲学家们近乎不约而同地将批判性目光指向了西方的“二元论”传统。 在这一传统中,“实在分裂为自我与世界,内部存在与外部存在,心智与自然。 这种分离受到宗教教条的长期支持,为后二元论的继承者准备了地盘。”[3]87人被变本加厉地逐出了自然(或者不妨说,是自然被逐出了主动性领域),他面对着一个就其本性来说死寂且无聊的广延世界,在无限的空间中不可遏制地感到孤独。 他因对心灵这一能动实体的内在保有而与自然中的任何对象间都有无可跨越的等级鸿沟。
迪姆(Christian Diehm)指出:“许多深生态学家都与奈斯一致,认为环境危机的一个根源是人在西方被逐出了自然。”[5]80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一与自然的相异以二元论的形式被铭刻进了近代精神。 无怪乎在一些学者看来,二元论已被环境主义者们认作头号公敌[6]。 追问至此,我们可以概括性地列出一个有关生态问题的逐层深入的递进线索:环境破坏的当代现实指示了现代人对自然的蛮横态度:人无情地利用并剥削自然,在自然面前挺立自身,不可一世。 这一态度或行动姿态背后是基础性的世界图景:人与自然(包括全部动植物在内)分处在根本上不同的存在领域里,且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自己更加高贵,自然则既无目的也无内在价值。
深度追问呼唤一种具有同样深度的行动,这一“行动”不再是发展创新性的环境技术,也不是单纯制定环境法律规范,而是在当前时代探寻新的思想可能性以对人与自然进行观念上的再布置。 用奈斯的话说,人们应当认识到:“环境的本体论和实在论先于环境的伦理学。”[7]93如同一名遭遇严重创伤的病人,不能仅靠缝合皮肤得到救治,名为深生态学家的医生们必须检查形而上学层面的受损情况。
为了重塑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关联,奈斯系统地阐释了“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学说与名为“认同”(identification)的方法论。 “生态自我”的理念认为,人类依本性就倾向于扩大“自身”的范围。 在这一进程中,自我不断地通过认同自然对象而得到深化与扩展,奈斯将此称为生态意义上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7]81-82。 “认同”意味着在他物中看见自己,其实现方式是多样的,它时常表现为对非人对象的同情。 以奈斯自己的经历为例:当他在一次实验中看见跳蚤落入酸性溶剂中慢慢死亡时,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痛苦和同感[8]83。 它也会表现为一种与外在事物的难以言说的“强烈关联”,如原著民与某一座山或河流,甚至某一块石头形成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让人认为,这些对象是“自我的一部分”。 报告这类感觉的居民们并没有学习过任何生态哲学,他们是自发地认同于(identify with)这些自然对象[7]87。这类情形被超验主义者们更加动人地表述了出来。 艾默生曾描述他在森林中的体验:“世上的生命潮流围绕着我穿越而过,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田野与丛树所引起的欢愉,暗示着人与植物之间的一种神秘关系。”[8]241
这样的田野与植物是难以被机械论式地还原的,这类强烈联系的发生也绝不是反映论所能含括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互动。 这种认同自然而然地引发了针对新共同体成员(自然物)的保护性伦理姿态,作为这一地带的居民,他想必一定会反对将它们交给现代工业进行开发,从而因些许经济利益消损掉这类不可描述的欢愉。 在奈斯看来,这一扩大认同的过程还标志着原先的人类自我的价值削弱[7]91,似乎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扩展”后,其原本的自我不再那么显眼了。
不难看出深生态学的理论诉求是消除人与自然间的区隔。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近代二元论的历史性胜利,那么直觉式的,个人情感式的修补进路就显得力量不足,它可以唤起神秘体验,深刻地改变个人世界观,但却无能于对抗二元论这一时代性的强力信念。 一种对自然观的历史性修复不能仅以发展个体直觉的方式进行,不然深生态学便有可能堕落为蒙昧主义。
深生态学家们当然不会忽视这一点,他们广泛地钻研了人类文化,从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吸取观点,企图寻找替代二元论的观念材料。这些体系包括但又不限于斯宾诺莎的整体论哲学,甘地的自然主义、印度教与佛教、道家思想、基督教生态神学等等。 但或许正是因此,深生态学难免给人造成文化复古的印象,学者们似乎无头苍蝇似的在古代文献中搜索“生态友好”这一辞条,凡是主张人与自然相同一的观点都可以拿来赞叹一番。 无怪乎布克金(Murry Bookchin)指责深生态学“将东方神秘主义传统粉饰以某种系统框架,而造成某类‘大杂烩’……混乱不堪,语无伦次,五花八门。”[8]27这种眼花缭乱的情形掩饰着一种思想上的无力,人们只好逃避与二元论进行真刀真枪的作战。 而如果二元论被认为是完美符合于近代科学的基本精神的,深生态学便无可辩解地是一种“反科学”思潮。
为了反驳这类批评,同时探究生态哲学所具有的可能形态,我们希望一方面能够坚持这一环境主义思潮的基本洞见,相信人与生态、自然、有机体等等是一个内在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观念,无论它来自直觉还是何种古代宗教,应当与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及其精神不存在本质性冲突。
许多学者对生态学这门较新的科学寄予了厚望,因为它本就是研究“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关系的科学。”[9]这一定义被一种基本洞见支持:有机体(包括人)与环境(生物环境与非生物环境)存在密切关联。 它存在于环境中,与环境相互作用。 但即使如此,生态哲学家们却无法从这一具体科学中直接获益,因为究竟何为“在—环境—中—存在”还未在哲学上被澄清。 二元论或者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同样接纳人与环境的关联:人的身体需要来自于外部世界的营养;人与其他动物共享一个环境;物种在自然中为食物与领地相互竞争……在此,没人能看出这些生态学见解有何种形而上学的对应位置,它无关二元或一元的哲学态度。 可以说,仅仅指出人与自然间存在“互动”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互动现象作为科学成就,并不穿透实证研究的大幕。 正因如此,奈斯对生态学与深生态学之关系做了相当谨慎的评论,生态学知识仅能够“暗示,激励,强化深生态运动的视角”[10]98。
如果将目光对准形而上学层次,似乎量子力学以及哥本哈根学派对物理学成就的形而上学解释便可被引为同道。①将量子力学引入生态哲学讨论的尝试在中外学者的论述中均有出现,可参见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3-311 页;陈炎等《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1-43 页。这一实在观挑战了机械论体系的一个预先划分:被观测的客体和观测它们的人。 作为研究/观测者的人可以对(物理)对象进行仔细的描述、测量、分析。 被观测者,即物理对象的真相原则上独立于观测者及仪器工具。 与之相对,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要求人们容忍确认位置与确认动量之间的冲突。 “因此,在原子物理学中,科学家无法作为独立的客观观察者,而是被卷入自己所观察的世界中,以至于他影响着被观察对象的性质。”[11]这一形而上学结果由一流的科学家所提出并确认,它相当程度地颠覆了认知者与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性,主与客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交融之势。
但量子力学带来的世界观变革究竟能为生态哲学提供多少资源却还是成问题的。 如果当前的理论任务是重塑人与自然间可能存在的深刻联系,我们便不可能满足于仅在原子物理学的层次上办理认证手续。 可以设想,当有人指出自己与自然界对象(无论是溪流、动物或是其他)存在亲密性甚至于将其认作自我的一部分时,他恐怕绝不会承认,这一亲密性源于自己在一种只有专业物理学家才能真正理解的粒子层面上参与了该对象的位置或动量确定,无论这种相关性有多么奇妙与深刻,人们也无法在其中发现草木山水等自然对象的踪影。 可见量子层级的交互性并不是生态哲学议题中人们所期望的关联。 量子力学及其结论的奇异性能够启发人们重新思索世界,但它恐怕并不具有直接性的生态价值。
二、本体论的交融:进化论视角下的人与环境
至此为止的困境隐约地在呼唤一种生命哲学,它应能够在形而上学层次上更新人们对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理解,勾勒出符合于现代科学的,人与环境或人与其他动物的复杂关联。 同时它也不能“走的太远”,以至于在寻找关联之时将人或自然还原成为纯粹的物理学对象,使得诸般生命现象尽皆错失。
在此线索中,进化论作为当代生物学的基石理论之一有着重大意义,海德格尔的犹太弟子,生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所作的《达尔文主义的哲学面向》(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Darwinism)一文则提供了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他在此文中结合哲学史对进化论思想进行了颇有深度的阐释,论证了一种人与自然的与任何神秘体验无涉的深度交融。
进化论的出发点具有完全的近代风格,它的建立只需要一个由自然规律决定的、没有内在目的、无需上帝过多干预的世界。 生命在这个世界里无目的地繁殖,进行残酷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有利于提升繁殖力的性状顺着基因遗传而渐进式地保存下来,失败者相反只能接受灭绝消亡的厄运。 初看起来,建立在进化论上的生命观难以支持何种生态哲学观念:这一世界太过残酷,而人类作为生物圈的竞争胜利者,更是天经地义地可对其余有机体实行强权,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斗争如此,生存亦如此。 上述思义确有道理,但达尔文主义与生态哲学之间存在的复杂张力,却绝不是一种“残酷自然”的观念就可概括的。
对进化论进行合理的哲学阐释将为深生态学信念提供两种支持。 第一,根据进化论的物种发展规则,生命体不可被脱离环境而理解,它与环境处在一种存在论层次上的“内在关联”(后文将解释此一概念)中,而这种关联使得人应当对自然有一种知识性的或曰理性的认同。 第二,这些分析“不仅仅表明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宣布了一种人与其他生物间的基本连续性。”[5]74通过这种连续性的建立,笛卡尔式的将人作为思维拥有者从全部自然界中独立出来的形而上学便不再成立了。 用达尔文本人的话来说:“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距虽然巨大,但却是程度而非种类上的。”[5]79
首先论述第一种支持。 进化论的提出是对物种不变观前所未有的打击,而如果物种及其性状的形成源于在具体环境中的生存斗争,那么一种微妙转变就悄然发生了。 由于“有机体被视为首先由其生存的处境决定,生命于是就要根据有机体—环境的互动而非一种天然本性的自动操演得到理解。”[12]46简单来说,生命体们在具体环境中相互斗争,而能够增加繁殖适度的性状取得优势,留存下来。 这一对性状的选择并非根源于物种的某种内在本性。 做出选择的“主体”是完全无意识的“处境”:周围环境提出的“要求”决定了谁才是“适者”。
一项生物学领域的经典研究可以例证这一阐释。 19 世纪早期,英国的尺蛾中深色蛾子的比例越来越高,而这样强烈的性状改变无法用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即小种群中等位基因的运气性改变来解释。 生物学家哈丹(J.B.S Haldane)指出,这一变化源于工业污染在城市里造成的逐渐黑暗的背景:黑化的蛾子与这种较深的背景色更为接近,因此它被捕食者如鸟类发现的概率比浅色蛾子更低(浅色的蛾子在逐渐加深的背景色上则越来越凸显)[13]。 深色蛾子(准确的说是“深色”这一性状)是这次生存竞争的优胜者,它因此胜利获得了繁衍下去的奖励。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性状变迁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该物种的内在目的,仿佛深色就是比浅色更加高级,尺蛾依某种“本性”应当逐渐变成深色。 单纯对生物体进行无论多么深刻的分析也无法解释深色性状的胜出,只因这一胜利源于对这一生命体来说完全偶然的、污染加重的城市环境。 假使若干年后,某城市的居民为了迎合时尚,开始以浅色油漆涂刷外墙,甚至连树干也不愿放过,那么消亡的命运就轮转到深色尺蛾了。
约纳斯认为“有机体与环境一起形成了一个系统。”[12]46现在我们应当对这一系统之系统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它不仅代表有机体需要在环境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在外部空间运动、摄食等等。 生命体实质上被环境从内部调控着。 环境不是简单的营养性的外部空间,如同桌子承载杯子一样承载生命,反过来说,生命也绝非像球装在袋子里那样位置性地在环境“之内”。 环境事实上是生命成其所是的动力根源,与生物们在本体论的深度中互动着。 物种及其性状如约纳斯所说,是“由其生存处境决定”的,而决定的原理就是进化规则。 除去环境,生命及其形态变迁是不可理解的。①这种对环境的重视在生物学哲学领域内并非约纳斯所独有,法国哲学家康吉莱姆同样对环境与生命的联系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参见姚思燮《论康吉莱姆对环境概念的哲学思考》,载《法国哲学研究》(第四辑)2021 年。
学界似乎还未注意到这一理论成果的生态哲学潜力。 事实上,它能够为深生态学宣言提供最为直接的理性支持。 1973 年,奈斯以纲要的方式列举了深生态学运动的几大特征,其中第一项就是拒绝简单的人—环境关系(人与环境如主客对峙)而代之以整体性的“内在关联”。 此术语的含义是:“A 与B 的关系构成双方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若无A 与B 的关联,A 与B 就不再是原先的对象了。”[10]95这一概念的提出挑战了对于关联的流俗领会,即认为关联总是两个现成对象之间的某种要素,必须先有现成对象,然后此二者间再建立起联系。 这类关联在日常生活中甚是常见,如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杯子在桌子上,球装在袋子里。
而在引入进化论及其哲学阐释后,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外在的关联并不能表征生命与环境,球不装在袋子里也依然是球,但除去与环境的关联,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物便不再能成其自身。 于是我们可以说,人类与自然的本质性关联绝非个别哲学家的奇思妙想,诸种浪漫直觉与体验,可以说是对这一客观原理的再创造和高级拓展。 在进化论的目镜下,即使不借助任何古代智慧或者浪漫情节,孤立的主体,一种保守在自身不变本质中的主体本就不曾存在过。 人与自然生态的“亲密”发生在生命的存在论领域中。
三、从隔离到连续:进化论视角下的人与动物
上述试图指明人与环境间存在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关联,此二者之间无法划出形而上学的分界线。 但需注意的是,生命—环境间本质交融的确证,并不能打破思维—广延这一更加顽固的二元隔离。 如前文所述,人类独有着思维这一实体,因此他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单纯机械/力学结构绝然地相异。 在这种笛卡尔式的世界里,“认同”显然是一种理性上的无知。
而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动态观点却唤醒了这一迷梦。 人与更加低级的生物间存在着发展上的连续,这种连续不仅将人放回了自然,同时“强调了人与其他非人存在者的亲缘。”[5]87无论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有何种优势,他的出现本就是自然的产物:由较低级的猿类动物进化而来。 人的一切器官与卓越能力,可以在进化的树枝形图谱上渐进地被追索,如同智人在一类常被展示的图片中,从古猿的形象分步骤逐渐站立了起来。 所谓“人属于自然”这一宽泛的论断,现在具体化为:人历史性地“来源于”自然。
这一人类理论与西方传统的创世观念存在不小的冲突,在创世纪故事中,“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 这一伊甸园中的事件范例式地表征了一种想法:人及其内在拥有的灵魂有一种自然外的来源,它是创造历史上的单独事件(神单独对人进行了吹气赋灵)。 但当进化论被引入讨论时,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对这段经文进行“寓意解经”了。 人类引以为豪的心灵或理性产生于完全的自然事件中,作为生存的利器,它与长颈鹿的脖子,鹰的利爪,虎的跳跃等等独特器官或能力一样,因能够提升物种的繁殖适度(帮助摄食、捕猎、逃离天敌等),从而在漫长的生存斗争历史中逐渐演化完善,最终胜利留存。 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因为鹰有自然界中最锐利的爪,它便在形而上学级别超越了其余一切生物。
从具体的进化线索上说,人类意识应当由最为简单的刺激—反应系统发展而来,“在时常需要竞争稀有资源的环境中,复制因子①在此,“复制因子”即是生物的不同性状。 它有着不断复制自身的“目的”。 为了实现它,复制因子必须拥有并发展某种策略,比如跑的快、盔甲的防护性好、拥有保护色等等。(replicator)如果拥有更为成熟的控制系统,就能够控制更多样化的行动反应,实现更多目标,它们就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14]神经系统的演化使得它从最简单的反射装置逐渐变成了高度复杂化的集成式中央处理系统(神经中枢—大脑)。 这一系统能够在采集环境信息后进行全局式的处理,使拥有它的物种对复杂环境进行分析,制定行动方略,从而在严酷的自然竞争中生存下来。 如此一来,人类对意识与思维的独有便无法维持了,进化论对意识形成的说明近乎不可扭转地颠覆了笛卡尔式的人与动物的间隔:作为脑的功能,意识及其能力不是一种特殊实体,而是一个其边界不甚清晰的谱系,逐渐完善于能进行神经反射的低级动物到拥有卓越理智的人类之间。
这一进化分析的实例可以帮助理解约纳斯的哲学思考。 在他看来,笛卡尔式的物质(广延)与心灵的二分是启蒙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一种策略,它将那些无法被广延化的东西(我思、观念等)单独框定(而非否定)了起来。 如此一来,剩下的世界便都以广延为其本性,从而可被精确测量与计算(数学化),而各领域的数学化当然是近现代科学研究的枢纽工程。 总结来说,“让‘物’独立,这是一种彻底性的,将外部实在从非广延和不可测量之物中本体论式地区隔出来的最佳手段”[12]54。 而“物”之独立的另一面正是“思”的独立:心灵实体或曰我思是由人所独独具有的,于是人便顺理成章地被约纳斯称作“二元论的堡垒”[12]57。
无论这种隔离在科学实用性上值不值得坚持,它的真理性都已倾覆,在进化论的视角下,人有一个完全自然的来源。 这一同源性的确立“废除了笛卡尔给予人的,相对于其余存在者的特殊地位。”[12]57无怪乎约纳斯评价道:“进化论比任何形而上学批评的尝试都更有效地摧毁了笛卡尔的工作。”[12]57既然各物种间存在着发展的谱系,人相对于其他动物没有起源上的专有地位,那么他怎么可能独独地抱有某种专属实体(心灵)?唯一准确的说法是:人类心灵的诸种功能明显强于其他动物,仅此而已。
人的地位之废除引出两条后续进路,首先是机械论的拓展之路(完全广延化):既然人没有特殊性,那么适合于动物的机械论形而上学也适用于人。 拉美特利对此评论道:“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吗? 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点,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15]但相反的道路也是可能的:既然人没有特殊性,那么适合于人的内在性、价值等等也适合于动物以及更广大的自然成员。 从生态哲学的角度看,第二条道路毫无疑问更值得选择:“在哀叹人因其动物血统导致的形而上学地位的降低所带来的不光彩时,被忽视的事情是,作为硬币的另一面,生命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被重新赋予了尊严。”[12]57
通过这一系列精彩的运演,进化论向人们展示出了其在生物学之外的理论价值。 迪姆评价道:“对人与非人生命之间连续性的理解对达尔文主义世界观来说是基础性的,于是进化生物学代表了西方思想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它能够促进在奈斯看来对于发展非人类中心论至关重要的那种与自然的亲缘性认同。”[5]86它让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万千生命重新感到亲近,虽然人类的主体性看似遭到了贬抑,但当他走出自身的孤独生命时,却能够向着无限恢弘的生命世界扩展自身,参赞神圣的自然造化。
结 语
如果说诸种生态哲学思潮期望对人与自然进行一种观念上的“再布置”,那么进化论便正是一种与之同行的自然科学理论。 它同样致力于回答生命与环境的互动、人与其他物种的关联等问题,在人与自然间构筑了牢不可破的亲缘。 这种追问的平行性是其他具体科学难以替代的,思想在此境域中产生了跨学科的激荡。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这种理论联姻促使我们进而思索生态哲学的当代任务。 如果生态哲学想要在现实中起效,真切地呼唤人们投入行动,就应当注重自身与现代科学世界观的适配。 以本文开头引述过的印第安自然观为例,这种泛灵式的观念当然具有生态意味,但这类观念在今日却难以拥有信奉者。 一名中学生恐怕难以在学习现代科学的同时,真切地相信某棵树木里藏着一个有意识的灵魂或将土地认作某位神明的“胸膛”,进而以防止神明疼痛为论据呼吁人们停止过度开发。 这种实效性或曰当代性尺度将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科学与古代智慧的合作,避免让生态取向的哲学工作成为人文学圈的自娱自乐。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科学是机械技术,工业生产等人类活动的理论前提,它也的确在不知觉间成为了环境破坏的推手。 但认定现代科学及其理念一定是生态的敌人却是一项严重偏见。 已有学者指出现代科学未必等同于对自然的操纵、预测等等。 相反,科学发现甚至可以通过祛除宇宙目的论而削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力量[16]。 方才的进化论分析则正是对这一削弱的例示。 挖掘现代科学的生态潜能,让它与人文智慧在生态话题中汇聚是完全可行的,这一前景值得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