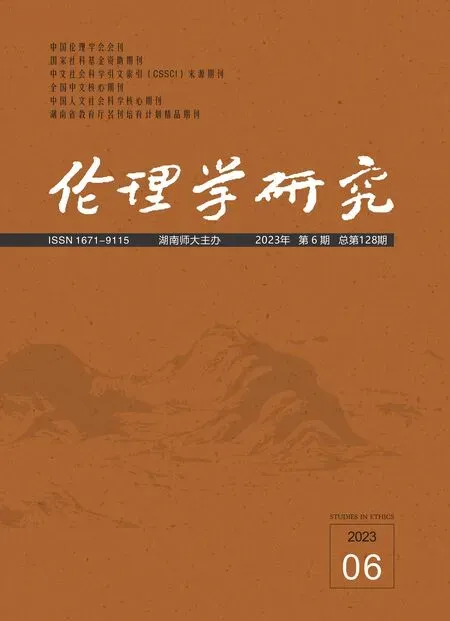梁启超新民伦理思想及其价值研究
徐亚州
梁启超可谓中国现代“伦理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与阐释者,在中国伦理学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也被诸多学者称为“思想家中的思想家”。1902 年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一词①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77 页。在中国古典文籍中“伦理”一词出现的时间较早。例如,《礼记·乐记》有言:“乐者,通伦理者也。”参见《礼记》,胡平生、张萌译注,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716 页。西汉的贾谊亦有言:“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参见贾谊:《新书》,方向东译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74 页。与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一词相比,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伦理”一词侧重于君臣(忠)、父子(孝)、夫妇(忍)、兄弟(悌)、朋友(善)之间的人伦关系与行为准则。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旧伦理”侧重于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泰西“新伦理”则侧重于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539 页。梁启超使用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一词出现的时间较早,在1897 年的《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中已经出现了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意义的“伦理”一词。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87 页。,此后,梁启超的《新民说》更是集中表达了其富厚的伦理智慧与道德哲思,切实开启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虽然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早已出现“道德”“伦理”等相关话语,但它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学科术语。梁启超在新民伦理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对中国近代社会风尚的提升以及中国近代道德观念的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现代伦理话语的推进以及中国现代伦理形态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因之,在伦理的理论与伦理的历史之互鉴沟通的基础上,系统探究梁启超新民伦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智慧,既有助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发展建构。
一、“道德革命”及其价值旨趣
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于1897 年在国内陆续出版发行,“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随即在中国近代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也促进了其他西方进化论著作的翻译和传播。西方进化论思想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发展观和世界观,为中国近代思想家开启了新的思维视域和理论视角。中国近代思想家将进化论思想引入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连锁反应。如黄进兴所言:“一旦他开启了优胜劣败的按钮,中国的道德意识立即变得流动不居,难以收拾了。”[1](102)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率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新国民品质的思考。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述具体的新民品格、条目之前,即以《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文阐释了新民的可行性问题。从新民的可行性来看,达尔文进化论给中国近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规范、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的革新与重建。此后,中国近代思想家全面开启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审视与反思,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140)。
从新民的应然性上看,传统“臣民”式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需要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和重塑,才能适应中国近代社会朝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需求。按照梁启超的逻辑,如果想要国家安定富强就必须先革新公民道德,而革新公民道德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革新的观念和方式。梁启超在撰写发表《新民说》期间,于1902 年刊发了《释革》一文,对“革命”的观念和方式进行了特别解说。在梁启超那里,“革命”有着多种理解和类型,只有采取正确的观点和态度,选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方式,才能达成理想的革命效果。在中国古典文籍中,关于“革”的事迹早有记载,“革”与“命”二字的连用也早已出现。例如,《尚书》中已有言:“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3](620)《周易》中亦有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4](226)按照梁启超的理解,这些事迹尚不足以称为“革命”,更多为王朝易姓式的更迭。梁启超认为真正的“革命”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Reform”式的革命和“Revolution”式的革命[5](92):“Reform”式的革命如1832 年英国的议会改革;“Revolution”式的革命如1789 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梁启超所谓“Reform”式的革命就是在保持整体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和改良,“Revolution”式的革命则有整体推翻旧制度、重建新世界之意。
对于中国近代国民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改造和重塑,梁启超实际上采取了因时制宜的态度与策略,即采取“Reform”式的革命抑或“Revolution”式的革命,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和内容来决定①勒文森认为梁启超思想中包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他尊重传统又欲变革传统的含糊的思维方式。参见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54—55页。张灏认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是复杂和多样化的,他的选择和他表现出来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65—166 页。实际上,这种逻辑矛盾更多停留在外在层面,梁启超始终希望能够发挥中国传统伦理的优势实现中国近代国民道德的革新,这种伦理路向在其整个伦理思想中未曾根本变动,特别是在其伦理思想的后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梁启超那里,道德有“德之外形”和“德之精神”的区分[6](541-542)。梁启超指出,由于文化、社会和环境不同,适用于诸种群体的道德条目也会不同,同时,不同群体适用的道德条目可能形式上截然相反,但其背后的道德精神却是相通的。梁启超所谓的这个相通的精神就是“利群”,即各种道德条目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整个群体的公益和福祉。如梁启超所言:“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则一也。”[6](541)对于外在的道德条目,梁启超主要采取了“Revolution”式的道德革命。梁启超认为,外在的道德条目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而不断调整和变化,才能维护群体的团结和促进群体的发展。对于相通的道德精神,梁启超明显采取了“Reform”式的道德革命。按照梁启超的逻辑,达尔文进化论不能应用于道德精神问题,道德的根本内涵永恒不变。这也说解了梁启超在新民伦理的后期特别强调中国传统“私德”的原因,因为传统“私德”同样可以达成利群、固群、善群的目的①按照杨国荣的论述,儒家价值体系虽然形成于前现代化,但却包含着适应近代化(现代化)的因素。参见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04 页。。梁启超在客观层面上接受了西方思想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的实践意义,而在情感层面上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文化自信。
二、“新民伦理”的价值内涵
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相关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度推广,梁启超并未局限于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检视与反思,而是全面展开了关于新民伦理的实践和探索。梁启超关于新民伦理的探索主要反映在《新民说》中,《新民说》一共20 节,陆续刊发于《新民丛报》第1 号至第72 号。从《新民说》整体的形式架构看,梁启超始终关切的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新民”)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的问题,为近代社会碎片化之“自我”至臻于“德行之人”提供了有益启示。在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中,关切的价值观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国家认同类”“个人自觉类”“社会合群类”。国家认同类的品格主要强调国家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念,个人自觉类的品格主要强调个人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念,社会合群类的品格主要强调社会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念(包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作关系)。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从“国家”“个人”“社会”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了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的异同问题,全面构设了契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民人格。
第一,国家认同类的品格主要强调国家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涉及的部分主要有《国家思想》《尚武》《政治能力》《民气》等章节。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开篇就论述了“国家思想”问题,也分析了国家伦理层面的品格在其新民伦理中的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比分析了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的差异,注意到“旧伦理”尤为缺乏国家伦理层面的相关品格。虽然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国家”的相关术语,但这些“国家”概念更多停留在部落或氏族的层面。传统儒家的士人君子则普遍将“平天下”作为最终的价值追诉和政治理想②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那样,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 页。这种天下观念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中国近代依然存有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某种否定态度。例如,在康有为所探求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就包含着天下大同的理想,带有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致其大乐,殆无由也。”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七集,姜义华、张荣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6 页。又如章太炎所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参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484 页。,以致中国近代的国家观念中依然带有社会等级和宗法身份的意蕴。由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冲突在中国近代社会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性。在梁启超那里,“国家”作为最大的团体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实体,从“部族”发展演变为“国家”则是文明进步的重要界标。他主张建设一个以富强、民主、文明为根基的现代国家,既注重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关注公民德性的培养以及社会风尚的维护。这种现代民族国家观使梁启超跳出了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进路,开启了中国近代伦理形态的发展建构。
第二,个人自觉类的品格主要强调个人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涉及的部分主要有《自由》《自尊》《自治》《毅力》《私德》等章节。中国传统伦理往往强调“无心”“无意”之行为才是真正的德行,所谓“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7](28)。相对而言,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较为关切行为者“意愿”“选择”之行为,所谓德性就意味着做选择(προαρεσι),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它(选择)显然与德性有最紧密的联系,并且比行为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8](64-65)梁启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的这种差异,并将此种意识推进到新民人格的构设之中。梁启超早在推介康德的伦理思想时,就特别强调了“道德之本原”问题。按照梁式的阐释,“吾欲为善人,欲为恶人,皆由我所自择”[5](137)。在《新民说》开篇阐释“新民”之义时,梁启超强调要主动选择那些更为优秀、卓越的民族来学习,以弥补我们自身所欠缺的品质和能力。在梁启超那里,行为者要先有“新民”这个选择然后再去作出行为,而非先作出了“新民”行为才去匹配或确定成为“新民”。行为者先有“新民”这个选择意味着行为是理智的和自愿的,而不是出于外力的胁迫抑或传统的惯力。在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中,出于“自觉”“自愿”之行为已经成为区分传统“臣民”与现代“国民”的重要标志。
第三,社会合群类的品格主要强调社会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涉及的部分主要有《公德》《权利》《进步》《合群》《义务》等章节。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伦理往往更加侧重个体对宗族、朝廷、天下的政治性道德责任,而怠忽了对社会公共性道德的重视和培养。虽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公正无私”“克己去私”的价值理念,但是这种“贵公”“尚公”的理念更多停留在价值评判层面,而非现实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与西方文化中“public”与“private”[包括东亚文化圈中“オホヤケ”(ohoyake)与“ワタクシ”(watakusi)]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公”与“私”往往指涉价值评判领域的善恶取向①黄克武认为公私问题可以划分为两个领域,即“实然”领域与“应然”领域。参见黄克武、张哲嘉:《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版,第59 页。,表示社会划分领域的“公”与“私”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公”与“私”观念带有“公领域”与“私领域”的意涵,但是与西方现代语境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意蕴却是截然不同的②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既需要制度性的保障,也需要相关民主观念的前提预设。如许纪霖所述,古代中国实际上并无形成类似现代公共领域的可能。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 年第2 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会和成公众的领域,但是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进而在基本上私人化而依然具有公共相关性的领域中对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参见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he MIT Press,1991,p.27。。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6](545)。一方面,梁启超所言及的“群体”包括两个层面,即政治性共同体和社会性共同体;另一方面,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不仅强调了国家共同体相关的道德规范(政治公德),还涉及了社会公共生活相关的道德观念。梁启超注意到了东西方“公私”问题的差异性,体现了将公共道德作为新民伦理的重要关切③例如,1907 年,《东方杂志》第4 卷第7 期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文章(《公私辩》),可以反映中国近代思想家(包括梁启超)关于“公”与“私”以及两者关系的态度和看法。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文稿对于研究梁启超公私观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陈弱水认为中国的“公”不但经常与领域无关,也不代表行为,而是指心态。参见陈光兴、孙歌、刘雅芳:《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0 年版,第78—79 页。陈乔见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公私之辨存在两次转向,即宋明理学的道德哲学转向和明末至清末的权利哲学转向。参见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与西方文化中实然领域的“public”与“private”问题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公”与“私”的概念范畴具有多重复杂的面向。。
三、“伦理转向”的价值趋赴
与传统儒家先哲所追寻的“圣人”理想人格不同,梁启超的新民伦理旨在探求一种能够契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且可以服务于世界文明的“新民”自由人格。对于西方伦理学,在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中大量援引抑或借鉴了边沁等人的功利论伦理学以及康德等人的义务论伦理学①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从边沁等人的功利论伦理学以及康德等人的义务论伦理学中获得了诸多有益启示,但是梁启超同样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伦理学所存有的理论局限。梁启超对于功利论和义务论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这种观点和态度在梁启超的文本中多有体现。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623 页;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8 页;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梁启超明确地将马克思视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主张运用唯物史观揭示道德的本质和发展问题②在《新民说》写作之初,梁启超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更是中国最早使用“社会主义”这个中文词汇的思想家,可谓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例如,在1902 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说道,“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Marx)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Nietzsche)之个人主义”。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7 页。。梁启超对西方伦理理论始终保持着理智与审慎的态度,就其新民伦理的精神意蕴而言依然带有儒家伦理的色彩。正如梁启超所言:“(西方伦理理论)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也则不可。”[6](643)梁启超的新民伦理立足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实践智慧,疏通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学之间的文明互鉴。从梁启超新民伦理的底层逻辑看,其在有意推进中国伦理学朝向两个方面的发展,即由“行为”到“行为者”的转向以及由“义务论”到“德性论”的回归③江畅提出中国伦理学经历了四次转向,即从坚守传统转向就教于西方,后转向就教于苏联,再转向就教于西方,最后又回头就教于中国传统。参见江畅:《中国伦理学现代转换的百年历史审思》,《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2期。梁启超的伦理转向带有双重性和先见性,就其外在形式架构而言其求教于西方,而就其内在精神意蕴而言则就教于传统。黄进兴认为清末民初的新道德有三项特质,即有意识的向善、祛除形上学以及“权利”基底。参见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167 页。确切地说,梁启超新民伦理的形式架构是中西调和与融会贯通的结果,然而就其精神意蕴而言则带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价值色彩。正如陈来所言,《论私德》及其影响下的《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参见陈来:《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梁启超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路向尤为关注,特别是在欧洲游历归来之后对儒家的内圣思想更是给予了较多关切。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六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32 页。。
1.由行为到行为者
梁启超在有意推进中国伦理学由“行为”向“行为者”的转向。梁启超在构设新民伦理的初始,将主要精力聚焦在国民应该作出怎样的具体行为的问题方面,为此,在《新民说》的开篇就特别论述了“公德”问题。随着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结构出现的全新变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德行问题也逐渐突显。由“家国同构”向“家国分离”的演进,传统儒家的规矩礼仪和处事准则在现代政治性共同体和社会性共同体中已难以施行。梁启超特别强调借鉴泰西“新伦理”中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以期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和发展。与梁启超所预期的不同,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实践并未走向他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西方式现代化,这使其开始重新思索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建立起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现代伦理道德体系。梁启超努力跳出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开始重回中国传统哲学中探求智识性资源,以期针对性地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实践问题,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符合本土特点的伦理支撑。与西方规范伦理学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始终关切的是“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追求的是行为者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君子”“贤人”“圣人”成为自我不断超越的阶梯和动力。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梁启超尤为重视宋明理学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阳明心学中的智识资源和实践智慧①如贺麟所言:“他(梁启超)全部思想的主要骨干,仍为陆王。”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8 页。。从实践层面上看,梁启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完成了阳明心学的创造性转化,使日本国民整体的道德素养和国家精神得到了全面提升。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应该加强对阳明心学的挖掘和应用,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国民德性的培养和整全人格的塑造,从而为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有利的伦理环境。从理论层面上看,梁启超认为王阳明“良知”的智识资源,能够较好解决西方伦理学“德”“行”两分的问题。赖尔在《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提出了两种知识的区分,即知道之知(knowing-that)和知道如何之知(knowing-how)②“knowing-that”和“knowing-how”亦可译为“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参见Gilbert Ryle,The Concept of Mind,Routledge,2009,pp.14-15。。但是,对王阳明的“良知”而言,赖尔的这两种知识都难以概括和解说③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东方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260—262 页。。在王阳明的语境中“良知”不仅同时具有“知道”和“知道如何”两种特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道德实践驱动性。相对于狭义的伦理概念,阳明心学通过心性身行的合一实现了整全的人格,可以较好回应道德上的知而不行问题。同样,在梁启超那里,“新民”不仅需要实现“公德”与“私德”的统一,而且要完成“德性”与“德行”的相通。针对中国近代普遍出现的“假道学”“伪君子”的社会现象,这种对内心觉知和思想意念的强调必然表现为道德践履的新民理念,强化了个体的道德自觉和责任意识,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学朝向现代化的发展。
2.由义务论到德性论
梁启超在有意推进中国伦理学由“义务论”向“德性论”的回归。梁启超在写作《新民说》的早期,对西方规范伦理学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较为关注“应该”“正当”与“责任”等义务论概念。梁启超希望借助西方规范伦理学理论弥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缺失,助力中国近代社会国民道德的普遍提升。在梁启超推行新民伦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风尚并未向其所预期的那样推进,反而出现了举国嚣嚣靡靡的状况。梁启超开始思索由“义务论”向“德性论”的回归④如梁启超所言:“就德性论,那层解缚的工夫,却更费力了。德性不坚定,做人先自做不成,还讲什么思想。”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77 页。,即从开始时对“行为规则”的强调到后期对“德性品质”的关切。在《公德》篇中梁启超尤为强调公民履行义务和规则的重要性,而在《私德》篇中其理论关切已主要聚焦在道德主体的德性品质方面。应该说明的是,梁启超早期对西方规范伦理学理论的推介实为一种应激性策略,更多的是为了迅速适应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梁启超从“公德”的强调到“私德”的关切并非理论的推倒重建,“私德”的基础性意义在《公德》篇中就有体现。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伦理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始终抱有乐观态度,只是这种观点和态度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梁启超的新民伦理思想并非由“义务论”向“德性论”的转向,而是向“德性论”的回归抑或彰显。
欧洲游历归来之后⑤欧洲之行归来后(于1920 年3 月5 日抵达上海),梁启超的几部重要著作相继成书[《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 年)、《中国文化史》(1925 年)等],亦能反映出梁启超伦理思想精神旨趣的回归。,梁启超伦理旨趣更加明显地回归中国传统伦理学,开始反思西方规范伦理学通过程序标准去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理论局限⑥学界普遍认为1958 年安斯库姆的《现代道德哲学》全面开启了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与审视。参见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Modern Moral Philosophy”,Philosophy,1958,Vol.33,No.124,pp.1-19。实际上,1902 年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已经具有了对西方规范伦理学理论的反思意义。如梁启超所言:“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梁启超在这里所言及的“泰西之学”不仅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而且也包括康德、黑格尔等近现代学者。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643—644 页。。梁启超所努力建构的伦理形态并非立足于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和边沁式的功利论伦理学,这种意识在梁启超的伦理形态建构中得到不断强化。梁启超的新民伦理思想涵括了大量的德性品质的相关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的新民伦理实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如果将“德性伦理学”视为一种动态发展的伦理理论而非静态固化的历史形态,梁启超的新民伦理或可称为一种广义的“德性伦理学”。一方面,梁启超的新民伦理可以较好回应当代德性伦理学难以回应的问题。当代德性伦理学始终伴随着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批评①托纳在《德性伦理与利己主义》一文试图回应德性伦理学关于利己主义的指责。参见Christopher Toner,“Virtue Ethics and Egoism”,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s,Edited by Lorraine Besser-Jones and Michael Slote,Routledge,2015,pp.345-357。,这在梁启超新民伦理中可以得到较好回应。梁启超新民伦理中的“新民”并非仅仅自身要成为“新民”,同时也要积极帮助他人成为“新民”。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6](530)另一方面,梁启超新民伦理具有与当代德性伦理学不同的理论进路。西方规范伦理学理论存有“美德”与“规则”的分离路向,这点在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中不成问题。如陈来所言:“德性伦理问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表现,不是规则和美德的冲突。”[9](301)在梁启超那里,所关切的是“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心行不二”“德行合一”亦可谓新民伦理的基本立场。
四、梁启超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从“道德革命”到“新民伦理”,再至“伦理转向”,中国伦理学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路径,踏上了中国式现代化伦理精神的必由之路。如今中国伦理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在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领域都实现了重要的推进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体现在经济、科技、生态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方面,而且要求我们广泛开展伦理理论的前沿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应当积极担起新时代的伦理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形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0](536)作为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伦理文明,更应当坚定伦理自信、兼收并蓄、奋发有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国现代伦理形态的发展建构应当立基于中国传统优秀的伦理文化资源,摒弃封闭、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坚持开放、共赢、创新的建构理念,兼收并蓄中外伦理学的优秀理论和实践成果②哈贝马斯曾特别论述了道德原则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参见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Polity Press,2007,p.204。,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伦理观念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相对于西方伦理学的历史衍化和发展进程,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发展推进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路向和实践智慧,可以为世界伦理学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作出积极贡献。在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义务论伦理学、功利论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鼎立的局面,三者表现出了各自独特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取向。义务论伦理学、功利论伦理学在对“行为”的关切方面有着共同旨趣,而德性伦理学则将更多精力聚焦在“行为者”方面③西方伦理学家对于“德性伦理学”的特质有着不同的说解,但是普遍认为“德性伦理学”应当聚焦于“行为者”方面。例如,赫斯特豪斯列出了德性伦理学的四个特质,其中第一个特质就是“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参见Rosalind Hursthouse,On Virtue Eth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6。同样,斯洛特认为德性伦理学必须更多地强调对行动者与其内在动机和品格特质的伦理评价。参见Michael Slote,From Morality to Virtu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9。,关于“行为”和“行为者”之间的争论持续至今。作为中国传统伦理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家伦理,不仅与功利论伦理学主要关切行为结果不同,而且与义务论伦理学侧重强调行为规则相异。在西方现代伦理学的这场鼎立局面中,儒家伦理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似乎与德性伦理学达成了某种“理论共识”。但是,这种理论共识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和德性伦理学之间的等同。一方面,这种理论共识并不聚焦在“行为者”方面,或者说,至少不仅仅体现在“行为者”这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德性伦理学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架构,更多为一种处在动态发展中的伦理形态。儒家伦理跳出了西方现代伦理学关于“行为”和“行为者”的二分争论,将心性身行统一在完满人格之中,展现出了一种更加富厚性的伦理形态。
概而言之,我们无意于论证梁启超的新民伦理应该归属于德性伦理学,更多意在说解梁启超的伦理转向对于中国现代伦理形态发展建构的有益启示。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转向中国现代伦理进程中的集中缩影,而且在世界伦理文明形态探讨中也具备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相对于具体的“结果”“规则”“德性”,梁启超的新民伦理更为关切一个人应有的整全人格问题,其所言及的诸多条目皆有“厚概念”(thick concept,其将评价性描述与非评价性描述相联结,具有行动的指导性——引者注)的意义①“厚概念”主要指具有“世界导向性”(world-guided)和“行为引导性”(action-guiding)的伦理概念,这些概念术语既涉及评价性描述,同时涉及非评价性描述,例如懦怯、残暴、勇敢、感激等。关于“厚概念”的相关术语学术界已多有述及,包括黑尔(R.M.Hare)、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安斯库姆(G.E.M.Anscombe)、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等。参 见R.M.Hare,The Language of Mora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Basic Books,2017;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Routledge,2011;等等。按照威廉斯的论述,“厚概念”与“薄概念”(thin concept)并非对立的关系,但是两种概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相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西方道德哲学对“薄概念”的关注超过了对“厚概念”的关注。,这也是梁启超为何将大量现代价值、理念都统归于新民德目的原因所在。梁启超的新民伦理将“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通过对中国“旧伦理”和泰西“新伦理”进行深刻反思和理性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旨在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和挑战,给世界范围内的伦理研究和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建构应当积极拓展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和外延,努力跳出西方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架构,进而充分体现伦理精神的中国风格和中国品质。如今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新论域,梁启超的致思路向依然可以发挥积极性贡献。道德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发展没有止境,中国传统伦理智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应擘画未来、赓续新辉煌。正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4](304)